2017-03-16 作为动词的文本

接收,是一个动词,拆封,是一个动词,翻开,是一个动词,寻找而找到自己的文本,则是最后一个动词。动词而动作,组成了关于文本的一个集束,在一个和平常一样机械工作的日子,一本陌生的刊物的到来,却终于将这一集束变成了可以永远珍藏的名词,就像那句话一样:“名词是在这个世界之后创造出来的,旨在指称世界的事物。”
而在这个陌生事物被指称之前,动词总是被创造出来,然后是“一切可能发生的行为和传递”。我说的“可能”完全是一种不确定的状态,甚至是一种不自信的感觉:它何时会被人发现,何时被编辑进刊物,何时能公开发表,何时会真正被自己阅读?可能的状态从2016年10月27日开始,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我就是这样进入了被动词包围的世界,而所有的动词度都集合成了一个动作:等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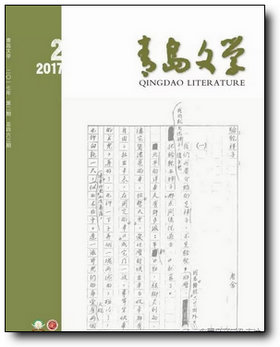 |
 |
最先是从“或。者”的留言里打开这扇动词的门,“你好,我是文学期刊编辑,请问这篇文章是否有意发表?”在关于《福楼拜的鹦鹉》的书评下面,一种诚恳、谨慎、礼貌的语气,留言者是陌生的“zuozuo”。作为回应,我告知了QQ号码,然后互加了朋友,才知道他是《青岛文学》的文学评论编辑,他说,最近杂志要进行栏目的改版,力图推出一些学术性的随笔,看到我的这篇书评,打算刊用发表。
我没有细问他是从什么渠道知道我的书评,或者是从网络搜索而来,或者是在豆瓣邂逅,也或者只是误闯到我的博客,反正,第一个动词是发现。当然,被发现对于我来说,也的确是一种被动语态,从来没有想着去投稿,也从来不期望在纸质刊物上发表,但是,被发现变成发现,于我来说,也是一种走出去的过程,文章当然可以发表,而且我也向他推荐了我其他的书评,它们一直以来安静地睡在我的“千克读品”的页面里,在少有读者光顾的角落里,只有我以“第四人称”的方式和它们对话,而现在,当那扇门被打开的时候,它们应该被另一些人看见。我甚至还向“zuozuo”推荐了我的那些影评,它们也像书评一样沉睡在只有我经过的那个世界里。
于是,那个等待的动词开始了,一直到今年1月9日,“zuozuo”在QQ上告诉我:“贵文《哈扎尔辞典》将要刊在我刊2月号学术随笔头题。”而第一次打开那扇门的《福楼拜的鹦鹉》书评可能要到下半年发表,书评和书评,文本和文本,对于我来说,并没有什么区别,所以即使被改变了计划,还是有一种欣然的感觉。但是他说的“将要”对于我来说,依然是一种不确定,将要是一种将来时,也是一种可能状态——直到2月13日,“zuozuo”才明确地告诉我:“哈扎尔辞典发第二期了,今天给您寄刊物。”发表在第二期,而且将收到杂志,这无论如何是不会改变计划了,但是等待还在继续,因为只有真正将杂志拿到手里,真正看到自己的名字和文章,我才能把自己当成一个可以看见的作者,也才能把自己当成认真阅读的读者。
在一个月过去之后的今天,终于收到了印有“青岛文学”字样的邮品,《青岛文学》对于我来说是陌生的,创刊于1959年,曾用名《海鸥》,青岛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zuozuo”说这是一本省级文学刊物。拆开,打开,翻阅,这是16开本的杂志,这是ISSN:1003-9791的刊物,而这更是印着自己名字和书评的文本:9000余字的文章就这样安放在第74-80页,等待它的另一批读者,它是安静的,却也是在系列的动词归于沉寂之后,走向一种名词状态。
其实,对于我来说,当翻开那一页看见自己的名字的时候,也是陌生的,就像当初拿到《文学与人生》时一样,“仿佛是一个不认识的人,说着和自己一样的话而已。”这种陌生感一直存在于写作之后的状态里,似乎也是对于作者身份的一种剥离,那些“很认真”的书评,只有进入到写作状态时,它才是熟悉的,才是自我的,这是一种“书写的正典”,而当完成这一种文,以最后确定的方式放置在自己的位置上,它就完全属于它自己,不管是在博客里的数字化,还是被发现的电子化,被发表的刊物化,都是作者之后的动词了,所以不管是我,还是“zuozuo”,甚至从刊物上阅读的那些读者,一定和作者无关了,我们都是读者,我们都在唤醒动词,我们都在等待文本。
事物被指称了,动词的意义已经结束了“可能发生的行为和传递”,于是我以名词的方式把它放进了文本的仪式里,它是永恒,它是唯一,它是典籍,它是历史,就像《哈扎尔辞典》里的那段刻写的碑铭:
在此躺着的这位读者
永远也不会
打开这本书,
因为他已长眠于此。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21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