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03-16《从城堡偷糖》:我爱人们在漂泊中沉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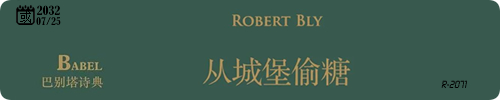
那头驴子说道,“只要抓住我的鬃毛,你就能提起你的嘴唇离我毛茸茸的耳朵再近点。”
——《吃词语的蜜》
不是说,是听,不是罗伯特·勃莱在说,而是我在听,一样在“四月的跳荡里”,一样发生在春天身上,仿佛是作为一头驴子听见勃莱在耳边讲话,而且几乎不停地在说:靠近,凑靠近,再靠近,听见他说出如蜜一样的词语,听见他说到滑入的海洋,听见他说起战争、身体、灵魂和死亡,以及和父亲有关的记忆,“我有那么多话要说!”他一开始就这样说道。
说和听构成了一种“四月的跳荡”,其实一本书只是一本书,一个说者只是一个说者,一个听者也只是一个听者,用驴子的比喻只不过是在这“四月的跳荡里”发现了一种重复的事:我曾经——一年前就已经读过了勃莱的诗歌,就听到了他对一头驴子的耳朵讲话。那时的一本诗集叫《对驴儿诉说》,而现在则变成了《从城堡偷糖》,无论是“对驴儿诉说”还是“从城堡偷糖”,书名都构筑了一种极富具象性、戏剧性的行为,勃莱似乎一直在行动,但是作为读者或者听者似乎忽略了这种行动本身:读过仿佛还是陌生的,听过仿佛第一次听说,是不是诗歌没有真正抓住鬃毛?没有提起嘴唇离毛茸茸的耳朵再近点?是不是诗歌每次都是一种新的存在?
很奇怪的体验,也许是忽略了诗歌其中的意蕴,或者不同的译者带来了全新的阅读感受,或者读过本身就是一种缺失——直到读到“我一直在对一头驴子的耳朵讲话”才想起《对驴儿诉说》,但是这分明还是1999年的诗集,距离勃莱真正出版的《对一头驴子的耳朵讲话》还有十二年,勃莱自己甚至还要以一种回溯的方式“对驴儿诉说”。一年前读的诗集《对驴儿诉说》由赵嘉竑翻译,它是勃莱两本诗集的合体:出版于2005年的《我被判的刑罚是一千年的快乐》和2011年的诗集《对一头驴子的耳朵讲话》,而陈东飚的一本则几乎收录了勃莱所有诗集的代表作,从1950-1955的《早期诗篇》一直到2012至2013的《新诗》,时间跨度是两个世纪近60年。两部诗集是不同的,勃莱和勃莱也是不同的,在驴耳边讲的话当然也是不一样的,这是和时间有关的普遍意识,就像勃莱在《悼巴勃罗·聂鲁达》中所写的那样:“无人放置花朵/在水的/坟墓之上,/因为它不在/这里,/它/已逝去。”
但是分明听到了在耳边说出的那些话,仿佛一遍又一遍,不如以某种回溯的方式再次回到勃莱如流水一般的时间之中,寻找永恒却流逝的“水的坟墓”——从已经被阅读但仿佛是第一次阅读的两册诗集开始。一个特别明显的标记就是勃莱使用了大量关于“量”的表达,诗集《我被判的刑罚是一千年的快乐》里的“一千年”构成了一种时间,而“快乐”则是这个一千年的总情绪:快乐是《有那么多的柏拉图》中的微妙,“我们的使命是成为一条湿润的舌/微妙的念头由此滑入世界。”是《束紧肚带》中的速度:“抓紧了。马匹正向夜晚疾驰。”是《黎明前听锡塔琴》中的轻与重:“有时候石头全无分量,而云彩沉重。”当然最重要的是《从城堡偷糖》,“仅仅偷一粒糖就是一份快乐!”通过设计图进入城堡,在城堡里发现死去的秘密,“我不介意你说我会很快死去。/即使在很快这个词的声音里,我也听见/开始每一个快乐句子的你这个词。”所以当法官宣判对窃贼的惩罚,这一年也是快乐的。为什么是一千年?《对一头驴子的耳朵诉说》里有更多的一千:“我们每言,‘我信上帝,’意思/都是上帝早已抛弃了我们一千次。”这是《藏在一只鞋里的渡鸦》的一千,这是我们死亡的一千次,也是祈祷被拒绝的一千次,所以上帝抛弃了我们一千次;《让我们的小船漂浮下去》里是“我们的哀伤而在一千个星系里被崇敬”,《向往杂技演员》里是“但我相信有一千个异教牧师/会在明天到来给风行洗礼”,《保持沉默》中的战争“这事已经持续了好几千年!”……除了“一千”,还有“一百”,《尼尔玛拉的音乐》里是“被倾倒出去洒在土地上”的一百碗水,《这么多时间》里是我们留在哀痛里再多一百年,《向往杂技演员》里写到当我们把双手放在地上,“井水就甘甜了一百英里”。
一千次被抛弃,一千次死亡,一千次被拒绝,一千个星系,一千个异教牧师;一百碗水,一百年哀痛,一百英里……勃莱用数字构筑的是一个繁复的世界?勃莱的数字叙事是一种增殖?当一千和一百成为对驴儿诉说的内容,再近点是不是全部能够被听见?并非是一种数字的重复,而是体现某种细小,“屋顶的细小钉子躺在地上,为屋顶而疼痛。/我们脚上某块小骨头正向往着天堂。(《屋顶的钉子》)”这是一千个细小的疼痛,这是一千次细小的向往,这是一千次细小的快乐,它们所构成的是一种整体的存在:化零为一:一头驴,一次惩罚,一处天堂,以及一部诗集,“我发现的那种/打开的一首诗的方式原是取/自他走进一处田野的方式。(《我父亲四十岁时》)”这是繁多、增殖和重复中的同一性,而这种同一性指向的是勃莱诗歌中对黑暗、寂静、死亡、灵魂、身体、意志、战争的同一种态度——诗集写作的时间跨度那么大,但是此种的情绪却很少流溢在纷繁的变化之外,就像水之流逝,流逝本身也构成了不被流逝的同一性。
| 编号:S55·2250211·2234 |
“我们到头来并未保持完整。”从时间之河回到诗集中的第一首诗歌,《一个黯黑草丛里的家》是一个起点,而这个起点作为勃莱诗歌之河的源头,似乎已经注解了他一生诗歌的同一性主题:正是我们从来不曾完整,正是我们失去了太多,当我们连根拔起才是真正的开始,“并在海里游泳,/不是总在干土地上行走,/以及,跳着舞,在树林里找到一个救星,/一个黯黑草丛里的家,/和死亡中的营养。”这便是作为源头而具备了所有之物的家:海洋之水,黯黑,死亡和跳舞:他在《等待夜晚来临》中写诗,写一首黑暗的诗,“我想早在子宫里我就接收到了/对黑暗天空的渴望。”那是黑暗中的水导向的死亡,“活着的我们像一只光润漆黑的水甲虫,/滑过静寂的水面方向任由/我们选择,而没过多久/就被突然从下方吞噬。(《夜晚》)”却在黑暗中享受,“假如我能下探,接近泥土,/我能拾取几抔黑暗!/一种始终都在的黑暗,我们从未留意过。(《午后降雪》)”甚至在这里找到了记忆,“在水下,从我儿时起,/我就梦见过奇怪而黑暗的宝藏,/不是黄金或怪石,而是真的/礼物,在明尼苏达的苍白湖泊之下。”
勃莱写作了《深夜友人来访时》《惊诧于傍晚》《晚间驾车进城寄一封信》,夜晚似乎适合他干很多事,夜晚是属于他的时间,而关于夜晚的诗歌本身就具有了极强的叙事性,比如《与一友人彻夜畅饮后,黎明时我们乘一艘船出去看谁能写出最好的诗》。夜晚感受黑暗,黑暗中感受快乐,这是对白天和热闹的隔绝,勃莱所写下的就是《棚屋里的冬季遁世诗》,“我醒时,新雪已经落下,/我独自一人,却还有个谁跟我在一起,/喝着咖啡,望着外面的雪。”和朋友交谈就是和自己对话,和黑暗共处就是和自我共处,而这和自我的对话和共处构成了勃莱“雪域中的寂静”,正是在黑暗的寂静中才打开了自己同一性的世界:“有一种孤寂就像黑泥!/坐在暗中歌唱,/我说不准这份喜悦/是来自身体,还是灵魂,还是一个第三方!”
身体、灵魂以及“第三方”,对于勃莱来说,就是在同一性中进入和世界的对话之中,《牙齿母亲终于赤裸》这一辑诗歌写于上世纪70年代,反战是诗集的主题,“这是汉密尔顿的胜利。/这是一个中央集权银行的优势。”海军空军基地,B-52战斗机、海军陆战营,以及越南、民主体制、总统,无不指向那场战争,但是这场战争带来的是谎言,“这些谎言意味着我们有一种渴望要撒谎。”是死亡,“现在我们遇到你从死者口中取来的垃圾,/现在我们坐在垂死的人身边,握住他们的手,几乎没有时间再见。”更是信仰的迷失,“我知道他们正用铁链把《圣经》绑在椅子上。/书籍不想再跟我们待在同一间屋内。/新约正在逃亡……扮成女人……她们在天黑后溜走。”而最后的结局是:“在另一个大洋中——牙齿母亲,终于赤裸。”1974年的诗集《雷耶斯角诗篇》是关于旅行的诗章,而这更是“战争结束”的叙事,“明天是/我的新娘要来的日子。/那时战争已经结束,差不多。”但是战争结束之后的旅行,也是孤独的,因为,“世界已经开了一个洞。”
世界已经开了一个洞,世界也不再是以前的世界,时间之流其实已经发生了改变,但是,“我爱人们在漂泊中/沉睡”,沉睡看起来是一种遗忘,但是却是一种经历过后的深入,“我爱雪;我移动时需要隐私。/我独自一人;乘烹锅漂行/在海上,整夜我都是独自一人。(《1926年12月23日》)”回到一个人的世界,是再次体验黑暗,是再次感受寂静,是再次和自己对话,再次在身体、灵魂和“第三方”的世界里寻找同一性的世界。《这副身体是由樟脑和歌斐木打造》诗集写到了身体,歌斐木是《圣经·旧约·创世记》中制造诺亚方舟的木材,当经历了这一切,还有可以拯救的诺亚方舟?还有可以打造的歌斐木?勃莱书写的“身体叙事”里只有一种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那就是爱,身体是黄瓜叶,是凝固与旋转的能量,是原生动物的共同体,但是,“这身体爱我们,并载我们回家离开我们的耘锄。”而我们也爱着身体,“我们爱这身体如同我们爱我们初逢引领我们离开这世界的人的那一天,如同我们爱我们某日清晨,在分秒刹那间,凭一时冲动送出,而我们依然每天看见的礼物,如同我柄爱那张人脸,在做爱后焕然一新,比一车干草更充满快乐。(《我们爱这身体》)”
当勃莱叙说着爱,其实他在一种缺失中寻找,对于爱情,他说:“我爱你用我内心末完成的事物。”对于身体,他说:“我们无法一直与我们无法命名的事物才自爱……”对于生活,他说:“现在我越来越渴望我无法逃离的事物。”而对于诗歌,他说:“词语的声音/有时承载的是我们没有的东西。”未完成的事物,无法命名的事物,无法逃离的事物,没有的东西,这一切构成了就是否定的缺失,但是勃莱以扬弃的方式寻找那个空出来的位置,它们是词语本身,“因此我们就是蜂群;蜜是我们的语言。”是灵魂,“死后灵魂回返到吸饮奶/与蜜在它简朴的家中。断梁/重又接起日出之门,而群蜂鸣唱/于酸肉之中。(《时间在死后倒流》)”当然,更能体现勃莱对未完成、无法命名事物扬弃的,则是对生活本身的思考,这就体现在他对父亲那段关系的书写中。“我父亲八十六岁/你八十/六岁了,还在我们/交谈时突然/倒头入睡。”在父亲这样的年纪,在即将“入睡”的时候,勃莱却问道:“我可不可以说你/虚度了你的一生?”
从父亲四岁时体内的巨大渴望写起,“不充分地/披着羽毛,已变得/寒冷而愤怒。”做事只是凭着自己喜欢,并且在喜欢中“一直活下去”,当经历了那么多,体内那种寒冷而愤怒的东西是不是也构成了勃莱无法命名的存在?从生病住院,到“探望我的父亲”,从“在殡仪馆”到“你死后一星期”,勃莱记录了父亲走向生命终点的过程,没有大悲,却有着无法对话的隔阂和无奈,“你体内的那一位/执意要活着/是那只苍老的鹰/世界为之而/变暗。”当死亡来到,应该有的对话都变成了缺失,“当我站在那儿身边/是你在你长长的/棺材里面,我明白我们/拥有的时间比/我们能用的更多。(《在殡仪馆》)”去世一个月里梦见了父亲,“安居/在一个铁匠的仓库里,/一桶桶螺栓和钉子/从地板到屋顶。”还带来了一个象牙罐给我,当我收下,意味着“一场危机已经到来”,但是父亲变成了一具干瘪的尸体,绳子还绑在脖子上。当我醒来,对妻子喊着:“他不是/那么死的!没有绳子!/全错了!”而妻子却说:“在/你的梦里他是那么死的。”
勃莱记叙了父亲的死,在并不呈现为大悲的诗歌里,却处处感受到一种隔阂,一个偏执的父亲?一个坚持着的儿子?从来没有真正对话的父子关系?总是变成危机的生活?也许只有死亡到来才是把这一切都推向终点,“若死亡/来临呢,若全都结束呢!”生和死就分开了沙子和海洋,分开了天与地。和父亲之间的关系在《早晨诗篇》中似乎也能看到复杂的情绪,勃莱提到了“一个悲伤的童年”,说到曾经找到电话亭打电话给父亲,“我们谈谈吧。”但或许终究没有谈,而等到过去了很多年,故事并没有真正走向终点,时间之流仿佛在流逝中注解了更多的内容,很多未完成的事需要完成,很多无法命名的事物需要命名,很多无法逃离的事物当然也不必逃避——跨过了《我被判的刑罚是一千年的快乐》和《对一头驴子的耳朵讲话》之后,收录的《新诗》仿佛再一次听到了勃莱在内心深处的声音,“天还黑的时候,我父亲起身,穿上/他的工装裤,穿上他倔强的生活,/倔强地将它珍藏——它内在/于他就像鸽子的啼鸣与生俱来(《我父亲在黎明》)”倔强如初,却是一份浓浓的回忆,而对于这个变化的世界,勃莱依然在书写着一种同一性的感情,那是爱,“我们厌倦了抱怨生与死。/即使老水手也保留着他们对风的爱。(《对风的爱》”那是回归,“多少个世纪我始终是无人,颠沛/流离,暴风雨中的一只野鸟,然而/那么久我—直都坐在摩西的身边。(《听蒙特威尔第》)”那也是快乐,“有时候失败和愚蠢是好的。/假如哈菲兹不曾愚蠢,他就不会拥有/赤条条走在路上的快乐!(《就是不要担心》)”当然,只有“提起你的嘴唇离我毛茸茸的耳朵再近点”才能听见。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53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