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03-16《历史及其图像》:让往昔复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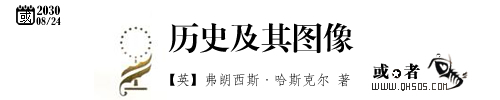
赫伊津哈认为,中世纪的衰落,其核心问题是想象力贫乏,其标志是要求“为所有的观念赋形。每个想法都谋求图像表达,但同时也在图像中凝固、僵化”。
——《第十五章 赫伊津哈与弗莱芒文艺复兴》
图像在表达,图像也被凝固和僵化,当图像的表达变成一种想象力贫乏的表现,艺术也就臣服在观念之下,甚至是在观念中心主义下失去了艺术的魅力。赫伊津哈无疑准确地指出了观念表达和艺术创作之间的区别,他所解答的是“中世纪的衰落”这个历史问题,但是他所呼唤的却是艺术的想象力——但是吊诡的是,赫伊津哈是荷兰的一名历史学家,弗朗西斯·哈斯克尔将他看做是一个“令我震撼的人”,也是从他作为一名历史学家的身份出发的,于是问题就变成了:如果中世纪的艺术不缺乏想象力,那些创作出来并不凝固和僵化的图像是不是会成为研究中世纪的一个重要维度?
赫伊津哈的历史学家身份是讨论的出发点,这本《中世纪的衰落》最早出版于1919年,五年后的英文译本定名为《中世纪的衰落》,对于中世纪历史衰落的研究就是赫伊津哈的主要成就,得出想象力贫乏的结论,也是在历史视野中完成的:他所依据的不是艳丽的节日盛装或二流手抄本的插图,而是基于对“单纯而优雅的凡·艾克兄弟的自然主义”,因为艾克兄弟在15世纪以他们为代表的弗莱芒艺术中引入了“写实主义”,在赫伊津哈看来,弗莱芒艺术的写实主义不是一个新社会的诞生,而是“一个迟暮文明的回光返照”,这种回光返照可以看做是对中世纪的一次复兴,而当赫伊津哈将他们的自然主义和写实主义放在“中世纪的衰落”这本书里,他其实就是在回答本书的中心议题:因为缺少像艾克兄弟及其追随者的创作方法,所以中世纪在缺乏想象力中衰败了。
那么,艾克的自然主义或者写实主义是对历史的一次阐释?至少在哈斯克尔看来是这样的,他认为赫伊津哈的贡献就在于对艾克兄弟及其同时代人的艺术有一个真切的了解,“通过观察它与时代整体生活的联系而把握其意义”,这是一种历史学家的视野;早在1905年,赫伊津哈在格罗宁根大学就职演讲中就选用了“历史思考中的审美元素”这一题目,他通过自己最近几年的经历,提出了社会学意义的问题:“历史学家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关注个体,又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关注群体或更广泛的社会力量呢?是伟人的行动决定了历史进程,还是伟人本身受制于自己所处的环境和形势?”而当1943年71岁的赫伊津哈从德国统治下的荷兰强制拘留所释放,他还回忆到了40年前的布鲁塞尔展览,正是那次展览开启了他作为中世纪历史学家的职业生涯,是他“最有意义的一次经历”。
赫伊津哈是历史学家,研究中世纪的历史学家,将一生都风险在历史研究中的历史学家,那么当他认为想象力贫乏导致了图像的凝固和僵化,艾克兄弟写实主义对文明的返照回答了中世纪衰落的原因,他的历史研究这一维度为什么是“艺术”的阐释?“历史思考中的审美元素”是让艺术指引历史?实际上,赫伊津哈对中世纪衰落的研究,对写实主义的引入,对历史的思考,所强调的不是历史发生的本身,而是一种“历史感”,“历史感最好用幻象,或者(稍好一点)用唤起图像来加以描述。”历史感不是历史,不是历史研究的正确方法,更不是“对往昔阐释”的方法论,它是架设在历史和艺术之间的一座桥梁,但是在这本副标题为“艺术及对往昔的阐释”中,哈斯克尔犯了一个根本性错误:将艺术阐释变成了历史研究的最要方法,将历史感具有的想象力还原为真实历史的再现动力。
艺术和历史当然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这种关系表现在很多方面,一方面艺术创作的确是历史的产物,没有一个不生活在自己的时代超越历史的纯粹艺术创作者,包括艺术拓展开来的文化乃至更为宏大的文明,都刻上了历史的痕迹,也就是说,不管是实物的存在还是精神遗产,都是历史的产物,都是存在于历史维度的社会的产物;另一方面,从现代研究处于历史阶段的古代、近代,也需要依靠艺术作品来阐释,这是对历史的发掘——在这两种关系里,艺术始终是一种再现,甚至在很大程度上以视觉化的方式呈现出来,它已经不在真实的历史层面,所以当通过这些艺术品来研究历史,本身就带有很大的危险性:它甚至是一种反历史的存在,那么,“艺术及对往昔的阐释”几乎就成了一个伪命题,剩下的也只有赫伊津哈所说的“历史感”,即使历史感存在,它也早就在想象力作用下变成了艺术的一部分——而不是历史的一部分。
历史产生了具有历史感的艺术,艺术是历史感的“幻象”,这才是艺术和历史之间真正的关系,而哈斯克尔却一直沿着从艺术中发现历史、阐释历史并还原历史这一思路,将艺术纳入历史研究范畴。在《导言》中,哈斯克尔其实就指出了这一历史研究存在的风险,一方面,他认为艺术作品并不缺少历史价值,他想扭转人们一直以来对艺术品的不正确态度:或者敬畏,或者贪婪,或者怀旧,或者好奇,或者熟视无睹,但是他们都认为富有历史意味的图像缺乏艺术性,但实际上,他认为,从历史中产生的艺术作品本身就具有历史价值;另一方面,很多时候视觉证据的流传过程极不确定,如果太偏重于视觉的历史研究,“其本身也有潜在的危险性”。强调艺术作品的历史价值,警惕太偏重于视觉的历史研究会有危险性,于是他折中地提出了一个概念:对历史想象,“这项研究,主题是图像对历史想象的影响,我的首要目标是说明那些可资利用的图像的本质,以及相关历史学家所做的探索——正是这些图像触发了他们的想象力。”当图像触及了历史学家的想象力,不正是赫伊津哈所说的“历史感”?
“图像的发现”是第一部分的内容,是谁发现了图像?哈斯克尔无疑又站在历史学家的位置上,他将彼得拉克这位历史学家看做是发现的第一人:是他第一次采用了“新的人文学科研究方法”,也是他作为历史学家运用新方法而作出了决定贡献,“在此书的写作过程中,在我的周围,要求在历史学家和艺术史家之间建立新型合作关系的呼声却不绝于耳。”彼得拉克如何成为第一人的?在一次阅读罗马晚期帝王传记时,彼得拉克看到了一段对小戈尔狄亚努斯的描述,说他是个面容英俊的美男子,于是彼得拉克在《罗马帝王纪》的抄本空白处写道:“那他肯定雇用了一个蹩脚的雕刻家。”看起来这句评论微不足道,但是在哈斯克尔看来,却是史学思想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在这里,彼特拉克不仅将图像与文献材料等量齐观,而且还看出了两者间的差异。”
| 编号:Y11·2231106·2022 |
一种是文献资料的文字描述,一种是图像的呈现——彼得拉克就是参考了一枚刻有小戈尔狄亚努斯半身像并有题铭的钱币,那么,真正的小戈尔狄亚努斯如文献的描述所称是面容英俊的美男子?还是被蹩脚的雕刻家在钱币上所画的那个半身像?彼得拉克发现了图像和文字的差异,他所提出的问题站在历史学家的角度来说,则是一个谁是真正历史上存在的小戈尔狄亚努斯的形象?或者说,谁更接近真实历史?彼得拉克的意义其实不再于看到了两者的区别,更是将钱币图像纳入到了历史研究之中。也许正是这一“事件”被哈斯克尔看做是艺术阐述历史的起点,所以他从此就从历史的维度构建起了艺术的阐述史,并将艺术品看成了对于历史研究的重要实物。
“许多来自不同领域的作者几乎众口一词,他们强调说:研究钱币,最主要的原因是它们对历史学家有价值。”不仅仅是头像,还有里面的铭文,都成为了历史研究的一部分,埃内亚·维科写道:“我们甚至会怀疑罗马历史学家所描述的伟大事件是否确有其事。”政治家塞巴斯蒂安诺·埃里佐说,历史知识在所有人类成就中最不可或缺,对于王侯和政治家而言尤其如此。之后是肖像画的出现,它是“最常见、最重要,通常也是唯一的形象化历史证据”,雅各布·斯特拉达对特定罗马头像进行了系统鉴定,巴伐利亚公爵布莱希特五世建立了古物陈列室,将文献和视觉材料合二为一,具有了文化史的意义;奥尔西尼将题铭、钱币、雕像、胸像和其他图像融为一体,以揭示古代名人的真实面貌;除了钱币、肖像画之外,还有镶嵌画、湿壁画等,它们成为历史研究中最重要的原始材料,梅泽类在他的《法国史》序言第一页他就宣称,留下伟人的声名是历史的真正目的,而“肖像和叙事几乎就是唯一的手段”。而图像材料和历史最直接的结合就是一些“实录”的出现,在16和17世纪的时候,人们对书面历史存在普遍的怀疑,于是他们认为图像材料更能够“实事求是”描述历史事件。
不管是钱币、肖像画还是镶嵌画、湿壁画,这些都是作为材料二出现的,它们当然是历史研究的对象,或者说它们还不是真正的艺术品,但是在“图像的发现”之后,哈斯克尔的“图像的运用”则完全从视觉化的材料变成了艺术品,当艺术和历史相遇,艺术对历史的阐述就成为了一个伪命题,相反,历史成为艺术创作的一个题材,它构成的是艺术本身的历史。蒙福孔在《法兰西王国古迹》中解释了中世纪叙事性图画,这本书“比以往更充分地意识到了可靠的图像在讲述民族历史(中世纪及其后的历史,还有相关的古代历史)的书籍中作为插图时所起到的作用”;拉·科尔纳·德·圣帕拉伊采用一种更“哲学化”的研究方法,投向了艺术和浪漫的骑士文学,使得虚构的历史叙事同样具有了价值;穆拉托里8卷本的《论意大利古物》更是深刻认识到了视觉艺术的潜在意义,他对中世纪建筑、雕塑和绘画的研究完全是一种文化史的研究——文化史不是关于历史的文化,而是文化的历史,其主体便是文化;马费伊从古物研究转向历史学,而他历史学研究的古物却完全是艺术品,它们是维罗纳的雕塑和铭文,“对学术研究而言,最为有益之事就是全面研究古代视觉遗存,并查看与此相关的最重要的版画。多年之前,我曾全身心投入这项工作,搜集了大量材料,脑子里想的就是这个目标。但我从未一试身手。因为我想还是先完成对古代文字材料的研究吧,毕竟我已经开始起步,且取得了很多进展。”
|
| 哈斯克尔:艺术是历史的“幻象” |
从古物材料到艺术品,这是一种转向,这种转向并不是在历史维度的,而是在艺术维度、文化维度,伏尔泰认为法律、艺术和科学更具有哲学价值的时候,艺术已经超越了作为军事技术、政府效能、各类乐善好施之举、种种嘉德懿行等的补充,把艺术变成了“一般意义上的文明衡量标准”,而随着罗兰完成《古代史》,文化史也终于诞生,“对艺术和科学的研究使我(的论述)远远超乎了我的想象。”文化史作为历史研究的一部分,它的本体不是历史,而是文化,这是一个最为关键的转折,在这个转向中,历史研究其实变成了文化史和艺术史的研究。一方面,艺术和文化是从社会中产生的,艺术也成为了社会表征的艺术,温克尔曼提出的观点是:“希腊艺术之所以伟大,是由社会、政治、宗教、气候和其他因素的合力所致,它们在古代希腊是如此特殊,因此也是独一无二,除非现在的世界有一个根本转变,否则这些条件永远不可能复现。”社会表征的艺术在黑格尔那里就被看成是一种“世界精神”,文明展示了自我体现了自我,艺术形式就表现了它的本质,“埃及文明,这个充满矛盾、令人费解的文明,首先是以其象征性纪念碑而知名,它由众多形式和众多图像组成,我们发现,精神从中感受到了自我约束,因而只能用一种感性的方式来表达自我。”
具有象征意义的“法兰西古迹博物馆”便是这种社会表征在艺术上的最大表现,法兰西革命具有的破坏性和它的建设性一样,是史无前例的,一方面这种破坏是对当时文化的毁灭,也是对历史的抹杀,所以“法兰西古迹博物馆”最多的遗存是那些曾存在于礼拜堂和大教堂内部的陵墓;另一方面,破坏本身也构成了历史的一部分,它是都那段历史最生动的注解。所以建立了法兰西古迹博物馆的勒努瓦被哈斯克尔认为是历史上拯救濒危遗产贡献最大的人,勒努瓦的成就,是同时代人们提出“画家、雕刻家、建筑师、装饰家到博物馆去研究艺术史及军人和平民百姓服装”的践行者,同时也成为“用一双敏锐的眼睛追寻法国古史”的严肃的历史学家。
按照米什莱的说法,历史学家的首要任务就是“让往昔复活”,勒努瓦是这样一位历史学家,米什莱更是付诸了行动,但是在更大的意义上来说,他们的历史研究就是站在艺术的位置书写历史,就是在艺术中找到了历史感,甚至就是构筑了艺术史。“让往昔复活”在米什莱那里完全是艺术化的展现,它等同于“让我想起了童年往事”,米什莱在22岁的时候就开始撰写童年往事,那座法兰西古迹博物馆就是留在他记忆中的“童年往事”,之后他专注于视觉艺术的研究,并且阐述想象力在艺术创作中的重要作用,“往昔社会的真实结构,以及不同民族的特有性格,都可以通过这些社会或民族遗留的艺术得到呈现,你可以直接目睹这一切,也可通过充满想象的沉思加以阐释。”他认为古迹在呼吸,教的尖顶在思考,耳堂在玄思冥想,哈斯克尔认为米什莱最大的贡献是对文艺复兴的“发明”,在米什莱看来,文艺复兴所复兴的并不只是艺术与学术,还见证了“世界的发现和人的发现”。
如果说米什莱“让往昔复活”,是在艺术中发现想象力的巨大作用,那么约翰·罗斯金、雅各布·布克哈特和希波利特·泰纳则充分阐述了“风格的历史意义”,尤其是具有鲜明特色的哥特大教堂,它们都提现了一种社会风格,而具有这种风格的艺术当然成为了对历史的一种阐述,罗斯金对“威尼斯之石头”的调查总结出风格和观念上的显著变化应该归因于时代而非个人选择;布克哈特说:“艺术不是历史的度量标准;其发展和衰落并不能为一个时代或民族提供绝对可靠的正面或反面证据,但它永远是充满才情的民族最有活力的特质之一。”而泰纳则从阿尔巴尼别墅中唤起属于它的古代社会生活——罗斯金、布克哈特和泰纳提出的风格,也不是为历史学提供一种方法论,他们更是将具有历史性和社会性的风格看成是艺术的一种表现,或者说,风格所体现的是一种艺术史观,“(一个时代)最为隐秘的理想和观念也许只有通过艺术手段才能传诸后世,这种手段最可信,因为它并非刻意造作。”布克哈特如是说。
其实对于艺术和历史的关系,阐述得最好的是“作为预言的艺术”这章,哈斯克尔甚至完全摆脱了“历史研究”,完全转向于艺术对历史的构建——不是回溯的“历史”,而是通向未来的历史——在这个意义上讲,“未来”是艺术的未来,艺术,也成为了“作为预言的艺术”。1635年凡·代克受命创作一幅绘画,要从三个不同角度展示查理一世的头像,代克完成了处在权力巅峰的查理一世的绘画,但是当这幅画被送到罗马交到正准备为查理一世制作大理石胸像的贝尔尼尼,贝尔尼尼看了画像说:“他预言了一些凶险和不幸之事,这位杰出君主的面相已经透露了这些苗头。”这是预言,预言当然最后成真了,但是艺术为何具有预言意义?为何直接通向了未来?哈斯克尔对这一问题完全是从艺术研究的角度来谈的,一个观点是,政治、道德、社会和宗教中即将发生的变化可以通过艺术呈现出征兆,这是因为艺术先天具有直觉上的优越性;这种直觉上的优越性不是艺术本身具有的,它无疑取决于艺术家,甚至在艺术天才上表现出来,创作了《贺拉斯三兄弟的宣誓》《布鲁图斯》的维特认为天才“总是能预言革命”;当然这种天才论更重要也更实质的意义是艺术家具有的创造性思维和想象力;而在社会变革时代,所谓的创造性思维和想象力,甚至就是对整个社会的反叛,是通过构建未来和现实断裂。
这种断裂就是阿波利奈尔所称的“战斗”,就是贾科莫创作的“速度”,就是马列维奇消除了逻辑的《第四维中的彩色团块》,就是路德维希·米德内尔融合了表现主义、立体主义、未来主义的“启示录风景”,就是康定斯基在战争爆发前创作的“有爆炸感和弹道痕迹的画作”,他们激发着无穷的想象,他们彻底将现在埋葬,他们颠覆了图像的再现,所以,他们开创了和历史相反的那条路:被预言的未来,而这或许就是艺术史中最惊艳的一笔,但是它从来不是历史研究的一部分,“让往昔复活”永远是在艺术的争斗中在未来复活,““巨大的战争风暴已经露出齿牙,用它那幽冥之手拖动着我的画笔,留下了残忍的身影……”康斯坦丁在1919年这样说道。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6467]
顾后:湘湖探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