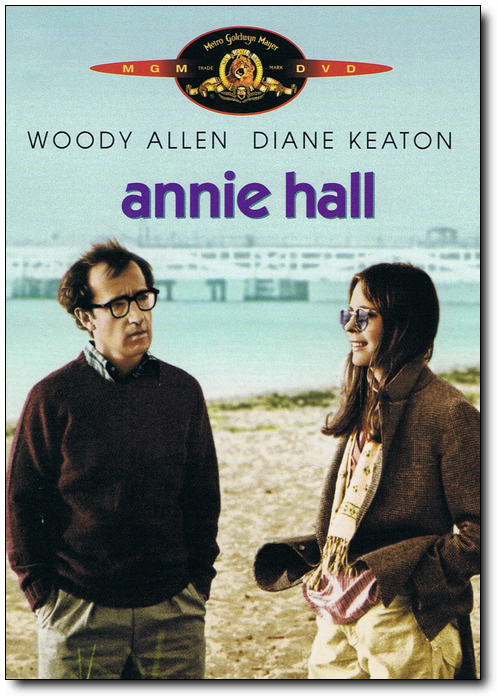2017-05-24 《安妮·霍尔》:被间离的知识分子

导演:伍迪·艾伦,编剧:伍迪·艾伦,主演:伍迪·艾伦,自编自导自演的故事贴满了“伍迪·艾伦”的标签,但是为什么不以自己的名字命名一部电影?甚至也不是以自说自话的角色埃尔维·辛格命名?去除了电影幕后的编导和台前的主角名字,当安妮·霍尔成为电影名字的时候,是不是也是一种“间离”的策略?她是一个来自威斯康辛州的乡下丑小鸭,她是被埃尔维·辛格发掘了唱歌潜力的做梦者,她是和他在床上完成了肉体亲密和依赖的女孩,但是最后却以分手的方式离开纽约,离开他,离开1975年,离开优雅,离开笑话,甚至离开关于所有死亡的书,而离开不是消失,她的名字无处可逃,被命名在《安妮·霍尔》的符号里,就像一个无形的门,把她放在了无法从他的世界里逃逸的符号。
不是谁是主角的问题,离开而不消失,分手而被命名,安妮·霍尔的符号化意义在埃尔维·辛格那里完全变成了符号,就像他说的命中注定要和一个开口说出“La-de-da”的女孩相遇,如启示录一般打开了门,却也如死亡的预约一样关闭了门——在飞行几千公里从纽约到洛杉矶,辛格坐在街头问安妮的最后一个问题是:“我在考虑我们该结婚了。”而安妮的问答是:“早了。”早了其实是不了,干脆,简短,充满了否定的力量,在洛杉矶,她的生活是结识朋友,录制唱片,参加社交活动,这是一种肯定的状态,而肯定的反面是否定,否定纽约,否定他,否定结婚,以及否定和爱有关的关系:“我们只是朋友。”
拒绝肯定,做出否定,被命名、被放在书名号里的安妮就真的成了符号,当安妮告别之后,开车沮丧地准备离去的辛格终于以一种诡异的方式撞到了前后左右所有的车,那一幕仿佛就是回到了布鲁克林的童年时代,回到了父亲开的那个碰碰车俱乐部,不断地撞击,不断地破坏,汽车和碰碰车一样,在应该成长的现实里变成了危害,于是被警察发现,于是被羁押,于是自己也像一个符号安放在书名号里。这是一种“返回”,辛格在开出碰碰车之前就说过,我的想象力太过发达,以致总是分不清幻想和现实,幻想中的自己,现实中的自己,幻想中的他人,现实中的他人,当分不清的时候,是不是把所有的人都符号化了,是不是把所有的车子都当成了碰碰车,是不是把所有真实的东西都当成了符号?
|
| 导演: 伍迪·艾伦 |
 |
作为纽约的一个喜剧明星,辛格在舞台上大讲政治笑话,开篇的那个老笑话,辛格指向的是所谓的生活危机:“有两位老妇人去卡茨基尔山旅游。其中一个说:哎,这地方的食物可真够糟糕的!另一个说:可不是嘛,给的份量又那么少。”这是辛格对生活的看法:尽管充满了寂寞、痛苦、悲惨、和不幸,但又觉得一切都逝去得太快。笑话不是为了笑,在辛格那里恰恰是为了不笑,不笑而笑,这是他的生活状态,也是一个纽约知识分子所面对的现实困境。两次失败的婚姻,像一个小丑一样逗笑别人,沉溺于和死亡有关的书籍,以及和是犹太人相关的出生,在辛格的世界里,否定笼罩了一切,但是在否定的状态下,他活着就像是在讲一个笑话,或者,他本身就变成了一个否定的笑话。
|
|
| 《安妮·霍尔》电影海报 |
当一部电影开场了两分钟,他无法容忍自己以迟到的方式进去观影,于是舍弃全部而选择新电影;他从来不在公共场所洗澡,因为在他看来被别人看见自己的身体是一种亵渎;小时候被母亲带我去看《白雪公主》,所有人都爱上了白雪公主,而他却对刻毒的皇后一见倾心……母亲曾经一语中的地谈到了他的否定状态:“他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所以在辛格的世界里,所讨厌的,所嘲笑的,所否定的,是一种面对现实的无奈,这是知识分子的幼稚病,看上去透着知识的分子的傲慢和咄咄逼人,却总是找不到突围的出口,于是在笑话的世界里,在失败的婚姻里,在自娱自乐的否定中,藐视着一切,却又让自己变成被被人藐视的人。在和安妮分手之前,狂妄症他跟踪安妮和“有一腿”的教授,当他质问安妮:“那混蛋教《西方男人的当代危机》,这都是什么垃圾课程啊?”而安妮告诉他:“是《俄国文学中的存在主义主题》好不好?你说的真靠谱啊!”辛格却归纳为一种:“有什么区别吗?反正都是一些精神上的自渎。”
或者也是自我生活的一种象征,讲笑话的喜剧明星却看了15年的心理医生,失败了两次婚姻却在寻找另一种幸福生活,《俄国文学中的存在主义主题》变身为《西方男人的当代危机》,并非是一种混淆,而是一种自我遮蔽自我否定的精神胜利法。所以在和安妮的爱情生活里,这样一种知识分子的症候便从骨子里进行了自我解构。从网球场上相识,然后约会,然后上床,然后同居,对于辛格来说,安妮的出现使得他可以名副其实成为一个知识分子,这个从“La-de-da”开口的女孩,有着最纯真的幻想,在某种意义上也像是辛格“返回”童年生活的一次证明,在学校里6岁的他就曾在全班同学面前亲吻一个女孩,这是他对女性感兴趣的开始,这个起点在两次失败的婚姻中几乎已经被遗忘了,而当安妮到来之后,那带着格莱美·霍尔式领带的清新风格吸引了辛格,于是他给他讲希尔薇娅·普拉斯的诗歌,推荐《美国现代诗歌》和《小说入门》,劝她去读成人学校,当然,也称赞他在杂音遍布的酒吧里唱起的“仿佛旧时和你在一起”是最动听的——甚至他们最后一次吵架,安妮脱口而出的也是知识分子的文本:托马斯·曼的《死于威尼斯》。
看上去,这一场恋爱充满了知识分子的肯定语态,而其实,在辛格骨子里的这种笑话生存方式使他无法从否定中脱身而出,而一心幻想成为歌星的安妮似乎也在这样的爱情故事里看到了符号化的虚构,她的网球技术不错但是开车技术奇烂,她需要借助大麻来提高性致,她会用非常弱智的借口来挽回辛格的爱,甚至醋意之中还会再提辛格和艾莉森的那段讨论奥斯瓦尔德射击角度的婚姻,还会在辛格和另外的女孩体验“卡夫卡性爱”中打电话回来打蜘蛛——而回来的辛格甚至拿起了《全国评论》这本知识分子的杂志去卫生间击打那两只巨大的蜘蛛。
一个是为肯定而否定,一个是为否定而肯定,一个是寻找,一个是突围,无论如何,这样的爱情存在过、体验过,最终却是灰飞烟灭,就像辛格对着2000一盎司的海洛因,突然一个喷嚏,毒品飞扬,归于尘土。所以在分手的时候,辛格对安妮说:“爱情就像一条鲨鱼,它必须不停地往前游,否则就会死掉。”不停地往前游是一种自我肯定,在行动中找到自我定位,但是最后的结果却是否定的死掉,所以为什么辛格说希尔薇娅·普拉斯诗歌里的优雅在1975年已经消亡了,所以为什么辛格说爱是“Love”太弱了,而应该是更强的“Lurve”“Luff”,为什么辛格会患上所谓的“慢性洛杉矶恶心症”——当安妮离开纽约,离开辛格,离开爱情,而继续在自己所谓的演唱事业中前行的时候,他们其实是回到了彼此的存在状态中——安妮不停地向前游,而辛格却在嘲笑他人和自嘲的世界慢慢死去。
非理性的、疯狂的、荒谬的男女关系正在解体,两个人就是在隔离的现实和幻想中,而其实,贴着“伍迪·艾伦”标签的电影,被命名为安妮·霍尔的电影,在某种程度上却在实践着戏剧的“间离”效果,辛格在和安妮看一场棒球比赛时就提到了“间离的模式”,他对着镜头说:“”讨厌棒球比赛,讨厌知识分子。”然后又转过头去,似乎把观众又撇在了一边,亲吻安妮就像回到了剧情里,回到了和观众互动无关的虚构中。辛格似乎热衷于这样一种身在其中又自由脱离的表达:六岁时亲吻了小女孩,教室里却坐着已经长大的辛格,作为旁观者他让每一个孩子畅谈未来;当和安妮错过了开场已经两分钟的电影而重新排队购票的时候,他们后面的男人喋喋不休地说着费里尼的电影,不耐烦的辛格走出队伍,面对镜头,而后面大谈阔论的男人也走近镜头,甚至两人走到旁边,从广告牌后面拉出他们正在谈论的麦克鲁恩,三个人一起开始评价其作品的优劣……
抽身而出,他们在叙事里,又在叙事外,当两个人进入剧院的时候,却成为了观众,他们站在一旁看自己的表演,评析到位与否,以及存在的问题;而对于安妮和辛格这两个在若即若离的爱情里的人来说,“间离模式”也成为反映他们内心世界的一种处理方式,两个人刚认识约会的时候,口头上谈论着艺术,但是内心的活动却变成了另一行字幕:“她可真是个白痴。”“他是个混蛋”;在夜晚同床共枕的时候,用大麻来提升性趣的安妮终于被辛格否定了,然后辛格打开了充满色情幻想的灯,但是两个人在一张床上却各怀鬼胎,甚至安妮的影子从床上起来,以旁观的方式看着他们;当两人的感情出现问题,画面被分隔成左右两幅,辛格在右侧向着心理医生述说着自己的烦恼,而左侧的安妮也倾诉着自己和辛格不和谐的关系;在他们飞往洛杉矶试唱而回来的时候,坐在一起的他们又彼此怀有心事,其实对他们来说,内心却有一个共同的关键词:分手。
“我们面对现实吧。”终于开口,在不断间离的效果中,无论是安妮还是辛格,其实都在否定的肯定状态中安于现实,又在肯定的否定状态中寻找自己的位置,一方面是融入,一方面是逃避,一方面是互动,一方面是抛弃,就如最后他们分开时说的:“听着,所有有关死亡的书都是你的,所有有关诗歌的书都是我的。”这是一种对立,这是一种分隔。可是,死亡和诗歌真的就是如此水火不容?如果拿在手里的那本书是《关于死亡的诗歌》呢?当安妮最终离去的时候,辛格创作了新的舞台剧,一个男人,一个女人,男人问女人,我在考虑我们该结婚了,女的却说,早了,然后各自起身,离开——这是安妮和辛格分手的写照?可是,当现实被搬上舞台的时候,是不是另一种幻想的开始?那女的终于回过头来,“我想和你在一起。”然后又说了一句:“我爱你。”于是男的过来拥抱,他和女人一起进入隔离之后的爱情喜悦中。
舞台表演而已,台上的爱情而已,观众又在哪里?其实在没有间离效果的舞台上,真正的观众只有一个:埃尔维·辛格,“她是多么好的一个人。”他说,他是爱情的作者,他是爱情的观众,他却不在现实里,那个多好的她一定只在书名号里,一定是被命名而成为一个符号:安妮·霍尔,“完全是非理性的、疯狂的、荒谬的鸡蛋”。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5802]
思前: 《洛奇》:割开眼皮让我看见
顾后: 《杜撰集》:传说神有九十九个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