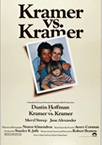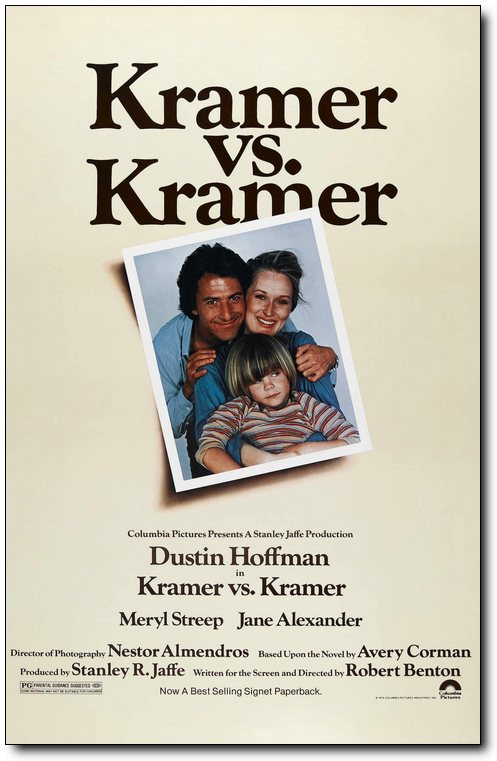2017-05-26 《克莱默夫妇》:Kramer vs. Kramer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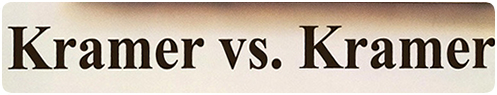
“我发现这里才是他的家,我非常爱他,但是我不带他走……”她是曾经的克莱默夫人,她赢得了比利的监护权,她可以把孩子带离这个家,但是在曾经的丈夫面前,她却用了一种否定的方式要把孩子留在这里。当乔安娜走进电梯,当电梯门关上,对于曾经的克莱默夫妇来说,像是一种隔离,但是这否定的想法却又仿佛把之前对于孩子监护权的争夺之战变成了另一种融合,他从楼上孩子身边下来,她从楼下走到孩子身边,在上和下的不同方向,里和外的不同空间里,他们却以另外一种方式共同回到了孩子的世界里。
无言,遗憾,隔离,在离婚而带来必须择其一的现实面前,他们看起来都是无助的,甚至这样一种家庭伦理故事必然会以受伤而终结,但是最后以积极的方式共同面对问题,又似乎为这个困境带来了一点暖意。电梯门关上那一刻,心门却被打开了,而就在18个月前,一样的电梯门被关上,一样走向无奈的分离,一样是留着泪告别,但那是一种坚决的离开,一种必须做出的决定:“我要离开你。”在事业有了起色、正想分享成功喜悦、甚至还没回过神来的泰德面前,乔安娜说了三遍这样的决定,然后留下了钥匙、银行卡,告诉了存款和已经缴纳的收电费,然后走进电梯,然后关上门,“我不再爱你了”是这对夫妻婚姻关系走向终结的宣告。
从电梯门打开走向终结,到电梯门再次打开走向新的开始,这似乎并不是简单的呼应,而其实在这场“克莱默对克莱默”的对立中,不管是乔安娜决然地离开,还是她18个月来的自我寻找,不管是泰德的自我反省,还是和孩子比利在爱的世界里融为一体,其实对于他们来说,对立的不是他们自己,甚至寻找的也不是自己,而是以比利为中心的一次发现,发现那种宽容,发现那种理解,以及发现都无法离开的家庭的爱,所以,电影名Kramer vs. Kramer,完全可以表述成:Kramer vs. Kramers——单数的是父亲、母亲或者孩子,复数的是一家人,一个人的现实总是难以解决一家人的矛盾,但是一个人的价值有时候需要一家人的爱来证明。
单数的故事,在复数的世界里,究竟如何打开,如何发生?这其实是克莱默夫妇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两个人从相恋到结婚,似乎都变成了一种省略的背景,也就是说,在这场最终走到一起的婚姻里,不容怀疑他们一定是带着满满的爱,带着对未来生活的憧憬和希望而走到一起的。就像在法庭上,乔安娜陈述时说,结婚前两年,很快乐,也有工作。但是当这一切都可以忽略的时候,他们的生活里出现了矛盾,出现了问题,也出现了孩子比利。从乔安娜“我要离开你”的决然态度中可以看出,在结婚之后,她没有了工作而成为一个全职太太,也从此开始了两个人的隔阂,泰德在公司里忙碌工作,对于这个家照顾很少,当然也没有更深地体会乔安娜作为一个女人的情感需要,甚至没有安心听她说话,也就是说,在乔安娜离开之前,泰德无论是作为一个丈夫,还是一个父亲,对于这一个集体世界来说,是缺席的。所以在五年的婚姻生活中,乔安娜似乎只留下了不快乐的感受,“我几乎没有了自信,所以必须离开。”
|
| 导演: 罗伯特·本顿 |
 |
而其实,不管是曾经泰德忙于工作的疏忽,还是现在乔安娜为了寻找自我,在他们不同的缺席阶段,伤害最大的是孩子比利。“要多大勇气才能离开孩子?”这是泰德的疑问,妻子和母亲突然离开,对于这个集体世界来说,无疑会陷入一种混乱。泰德成了家庭主妇,比利成了首席助手,似乎各自是有了新的定位,但是在没有秩序的生活中,他们的世界一片狼藉:鸡蛋敲破的时候杯子里都是鸡蛋壳;将吐司放在里面的时候忘了加牛奶;在走神的时候吐司却烤焦了;急忙去拿平底锅的时候,却烫了手……父亲和孩子,当没有乔安娜的一天到来的时候,他们其实无法走进有着母亲影子的生活,或者说,这个集体世界的一切秩序都是母亲所设置的,都带有她的标签,不管是泰德还是比利,仿佛都变成了过客。
|
|
| 《克莱默夫妇》电影海报 |
这也是问题暴露的方式,而对于比利来说,这种困难越发凸显,在超市里购物,比利只记得母亲的购物习惯,那些物品也都打上了乔安娜的印记;在回答最喜欢的球队时,比利说是波士顿队,“因为妈妈是波士顿人。”而在送比利去学校的时候,泰德也是匆匆在学校门口丢下他,然后自己去搭计程车。种种问题凸显出来,泰德在混乱中才感觉到自己曾经在这个家庭中的缺席,他更像是孩子世界里的陌生人。所以当乔安娜离开之后,他需要的是重新找回自己的位置,重新走进这个集体世界。
把乔安娜相关的照片、贺卡、纪念物,甚至缝纫机都收进了盒子里,按照自己的方式开始和比利相处,泰德看上去是开始了“去乔安娜化”的努力,实际上是在新的生活中重新定位自己,重新弥补过去缺席的父爱。他不再急匆匆送孩子到学校,而是在路上和孩子聊学校里的事;因为比利被别的同学欺负,老师来电话,泰德便离开一次公司的重要报告;因为比利生病发烧,他耽误了大西洋航空公司的截稿日,致使公司付出巨额赔偿。而那一天在公园里玩耍时,比例从高处摔下来脸部着地,泰德疯狂地抱起孩子,穿过车来车往的街道,高喊着“急诊室在哪?”当医生对比利进行治疗要他离开手术室的时候,泰德却说:“我是他父亲!我要去陪他!”坚决要在疼痛的比利身边,成为他有力的臂膀。
而泰德回归家庭,总是和公司的所谓公事发生矛盾甚至冲突,一开始以为自己可以处理好两者的矛盾,但是当泰德在家庭生活中重新寻找自己位置的时候,却只能牺牲公司的利益,错过重要报告,错过作品截稿日,甚至那一大堆的材料在比利的果汁中化为乌有,最后的命运:泰德被解雇了。那时乔安娜正好提出要孩子的监护权,泰德又坚决不同意,而失去了工作的他无疑在这场争夺战中失去了优势和机会,所以他为了比利,在24小时之内找到了工作,虽然和以前的工作相比少了很多收入,但是在泰德看来,却是保住了和比利在一起的机会。
一个父亲回来了,一种爱也回来了,“爸爸,我爱你。”比利说,“比利,爸爸也爱你。”泰德这样告诉比利。泰德找到了自己的归属位置,进入了这个集体世界,而在分开18个月之后,离家出走的乔安娜也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在一起的时候我不知道自己是谁。”曾经她也是迷失了自己,而离开之后她找到了工作,成了一名服装设计师,也找到了自己的归属位置。但是当两个人都看见了自己的时候,却必须面对一个问题:比利到底时归谁?
从个人主义式的发掘到现实主义的难题,无论对于泰德还是乔安娜,都比分开之后18个月的生活更为残酷。当两个人终于站在法庭上打起了夺子的官司的时候,似乎先前的一切努力正在失去意义。两个人都爱着比利,两个人也都从自身寻找问题,乔安娜说自己没有耐心,不自信,“不是你,是我的错,你娶错了人。”而泰德也承认,从前的自己太忙于工作,疏忽了乔安娜的感受,“我想让妈妈成为某种人,变成我想要的那种太太。可她不是,我以为我开心她就会开心,但她没有。不是你的错,是我。”但是当这场官司真正打起来的时候,为了争夺这唯一的孩子,他们虽然没有相互指责,但是关键的理由只有一个:我更适合孩子。
对簿公堂,是Kramer vs. Kramers的战争,甚至各自的律师为了当事人打赢这场官司,想尽了一切办法,有的甚至击中要害,但是在这场争夺孩子的“战争”中,其实对立的不是夫妻双方,而应该是自我和家庭之间,也就是说Kramer vs. Kramers。在离婚之前,泰德为了自己的事业,忽视了家庭,这是他的失职,而在乔安娜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又离开了这个家,而且这一离别就是18个月,无论如何,对于正在成长中的孩子来说,他们都是不合格的,都是自私的。而当泰德开始承担起作为父亲也作为母亲的职责时,他回归了家庭,但是乔安娜提出要比利的理由,仅仅是“他爱我,而且他更要我。”这是一种基于母爱的判断,对于孩子来说,在那个阶段。似乎母爱的作用更大,而且乔安娜一直和比利在一起生活了5年,所以在法庭上,乔安娜说的一句话是:“18个月怎么能和5年半相比?”将一种对孩子的爱时间化和数字化,也无非是站在自我角度的自私想法,5年半是她和比利在一起的日子,但是那时候泰德虽然忙于工作,但还是有着父爱,也就是说,乔安娜在5年半的时间里没有起到父亲的角色作用;而在她离开的18个月时间里,泰德在逐渐磨合中承担起了父亲和母亲这种角色,也就是说,如果真正量化来比较,泰德的爱甚至比乔安娜更多。
所以他们真正面对的问题是:怎么对比利最合适?无论是泰德还是乔安娜,他们对于孩子充满了爱,也自信能够照顾孩子,但是其实他们离婚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孩子,也就是说,比利在这个矛盾中只是一个果,而不是因,让他来承担失去父亲或者母亲的后果,都是不公平的,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泰德找到位置,还是乔安娜寻找自我,比利发挥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力。他的存在,他的生活,他的困惑,他的遭遇,都为泰德和乔安娜寻找到更好地表达机会,泰德发现了自我,是通过比利实现的;而乔安娜回来要回孩子,也是因为她无法忍受失去孩子的生活。
“别让臭虫咬你。”这是当初乔安娜离开时对比利说的话:而这句话在后来的日子竟变成了比利对泰德说的话,这种无形的转换其实让泰德和乔安娜为代表的成人世界处在一种尴尬中,无论如何,在婚姻这个一生中最重要的关系上他们都失败了,但是在家庭上,在对比利的爱上,他们却又都唤醒了自我,当泰德输掉了官司,“如果我上诉呢?”当律师说:“这回你得付出孩子的代价,我必须传唤孩子作证”时,泰德还是放弃了上诉的权利,因为他,不能伤害自己的孩子。
所以在这个伦理的难题中,当任何一种选择都可能对孩子造成伤害的时候,他们或者必须选择一种折中的方式,所以在按照法律程序比利要离开,按照亲情要求比利必须留在这里的时候,那扇电梯门关上了,上和下,里和外,这是一种隔离,但是这已经言和的隔离更像是融合,他们离婚,他们分开,但是心却以另一种方式回来了,回到自己应该付出爱的家里,回到Kramers的复数世界里。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52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