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10-29 犹如雨的盲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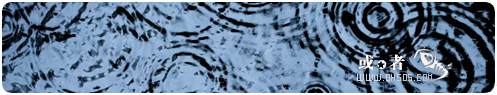
现在可以把手指放到扳机上。不,最好压低枪口顶住颧骨,直到感到疼痛,觉得空铁管里面藏有子弹。
——卡尔维诺《通向蜘蛛巢的小路》
必须是紧张的场景,甚至有点冲突到一种黑暗的降临,一把冰冷的枪,一种身体折磨出现的疼痛,以及一种和困境在一起的压抑——本来是一种可能不存在的想象,甚至没有一颗子弹,但是当触及到皮肤,便“感到铁器的冰凉了”。
引用,是把自己安放在另一个作者设置好的故事里,即使去除掉了所有背景和细节,去除了故事的多种走向,但是在一个通向蜘蛛巢的小路上,交错的感觉却无法挥去。就是被这一种引用带入到了小说的虚构世界里,于是开枪或者不开枪都在其次了,只有那一种冰凉的感觉,伴随着身体的疼痛,却传遍全身,甚至把所有写下的文字都弄得血迹斑斑。
大约是自己缺少了被带入场景的能力,所以在引用的句子里,自己才能微微醒来,才能制造出一点紧张的气氛。生活一直是这样,按照它既定的路线前行,从早晨到晚上,从晴天到雨天,从春季到秋季,一无是处毫无意外,到后来甚至连打量所有新鲜的一天也有点机械了,于是弄出点冰凉,弄出点疼痛,弄出点紧张,像一部小说,必须在大路朝天中走向蜘蛛巢的小路。
如果不是引用,我完全应该自己去书写一个故事,一段情绪,甚至自己制造如迷宫一般的情节,但是似乎有些疲态了,一两个句子还在本子上,像一句诗,读起来有一点味道。那似乎是某个雨天行走在不知名的路上,偶然想起的,并非是茫然,在陌生的场景中,我似乎更容易找到情绪表达的出口,关于下落的雨,关于向上的树,关于沉沉的大地,关于很轻的记忆。但是只有一两句诗,很偶然地找到了意境,但无法表达完整的意思,最后也只是残留在那里,无法成为一个整体的一篇文。
仿佛就这样烂在那里了。那一个掀起点高潮的节点已经过去,而且很平滑地滑向了不确定的未来,像是一下子掏空了一般,也懒得却寻找什么,更不会去发现什么,只是随遇而安地存在着。这是一种空泛的状态,一切都在渐行渐远,时间是有的,但是在被充满了时间的日子里,倒是手足无措了,所以那下雨的日子,那几句诗就像是别出存在,当雨终于不见,当晴天开始,情境就像死去了,不仅是找不回那种感觉,连几句话看上去也找不到阅读的兴趣。
所以又回到了曾经的茫然,没有计划,没有预设,没有通往蜘蛛巢的小路的那种冰凉感觉,犹如雨的盲点,在时间里终究没有了那一种表情,甚至下就下吧,在安然坠落的过程中何处有溅起的水滴,何处有树叶飘风时的逆向动力,又何处有必须陈述于口的诗句?尤其是这个秋高气爽的晴天,热不热,冷不冷,一道清脆的阳光撒落下来,再也没有可以迷茫的理由。在心里还落着雨?还有雨的盲点?还有恣意的坠落?
其实,通往蜘蛛巢的小路是自己走上去的,“他把枪放在哪里?给谁了?”这样的疑问更可以看成是接近另一种疼痛的理由,身体在自己身上,疼痛在那里出现,没有诗句,没有雨的降落,也无法离开必然到来的颓然,所以,在一个个晴天里,“阳光紧贴着冰冷的墙壁垂直往下照,一直照到小巷尽头,一些拱形建筑使得深蓝色天空看上去像是被分成一段一段的。”自动分离开来,一段一段地存在,像诗句必然的命运一样,无法成为一个整体的一篇文。所以电话那头,总带着来埋怨的口气,所以电话这头,总是把借口当理由,所以电话那头的疼痛,总是传不到电话这头,所以电话这头的生活,总是不被电话那头理解。
身体的疼痛已成为必然?生活的不安已成为常态?走出去,又返回来,秋天似乎又加深了一寸,长袖开始遮蔽裸露的皮肤,一切的过渡总是无声无息,而以为身体已经具有了秋天的模样,它却在另一个时间里挣扎,“这是冬天的一天,也是仲夏的一天;这是静止的时间和一个还有时间的时间:”冒号之后是时间的时间的疼痛,“一个时间给一个不再有过路人的世界;一个时间给一个从未有过表情的脸”,而另一张脸呢?最后都变成了记忆,变成了虚构,变成了一把枪抵达身体而感觉到的冰凉——尽管那铁管里没有一颗子弹,如果可能,随时可以打中那张没有表情的脸,打中那个没有感觉的身体。
那先前的雨,终究像长袖一般,遮蔽了裸露的时间,而这不是庇护,而是麻木,雨的盲点像雨本身一样砸下来,但是身体早就没有了疼痛感,我们把它叫做“堕落”——比坠落更自然地从高处抵达深坑的地方。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1761]
顾后: 作为他者的金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