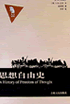2022-10-29《思想自由史》:必得开放言论自由

但要稳固地建设思想自由的学理,尚须有逼害的理论和实际的长期经验,后来基督教所取的压迫政策及其种种结果就驱使理性为这个问题而奋斗,使理理智自由终得辩明了。
——《第二章 理性自由时代》
“思想自由史”被写成了“自由思想史”,算是对文本的第一次误读,似乎潜意识里“自由思想”比“思想自由”更符合语法,或者被自由修饰的思想史比被思想限定的自由史更重要——一本在书柜里搁置了许多年的书,一本只有薄薄133页的书,从来没有进入过必读的书目中,那一段从购买到阅读的漫长历史是不是也是对自由和思想的忽略?
伯里似乎也没有对“思想自由史”和“自由思想史”有过明确的区分,但是行文中,“思想自由”组合成固定的词组,指向的是另一个更狭义的自由:言论自由,“所以思想自由,从它的任何价值的意义看来,是包含着言论自由的。”从言论自由来看思想自由,从思想自由来构建思想自由史,伯里其实很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而基于言论自由之上的思想自由,在历史的场合中它所必须面对的则是教条,则是权威,也正是教条和权威可能存在的“逼害”,使得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最核心的精神便是:理性,以理性反对权威,以理性争取自由,理性的构建历史便成为了思想自由的历史,伯里就是以这样的逻辑开始了思想自由史的论述。
其实,伯里对于自由、对于理性的阐述,放置在西方的历史中,这似乎是一种狭隘,甚至在他看来,因为思想自由是建立在言论自由基础之上的,所以自由还必须是一种公开的思想表达,如果只是限制在人的内心世界中,只有经验和想象,那么这种私自思想的天赋自由也是没有任何价值的。立足于西方历史,论述于公共思想,思想自由便只是一种狭义上的概念定义,再加上它主要的表现是言论自由,它所反抗的是教条和权威——这主要也是表现为基督教的权威,所以伯里的这部思想自由史只是在很狭窄的通道上,133页的论述也基本上是以历史素材为要点,缺少对概念、思想的深度阐述,伯里自己在《序言》中也承认,这只不过是一个很简略的导言,“未能尽量论述”。
古希腊和罗马时代是伯里思想自由史的起点,而这个时代在他看来却是“理性自由”的时代,也就是说,历史似乎并不是螺旋式上升的发展过程,而是从自由到不自由再重新获得自由的曲线型过程。古希腊和罗马时代为什么是理性自由的时代,因为那时候是言论自由的,“我们最深沉的感谢是因为他们是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创造者。”他认为小亚细亚的爱奥尼亚是自由思考的发源地,欧洲的科学史和哲学史都起始于爱奥尼亚:其开拓者是色诺芬,他攻击的是荷马,而攻击荷马意味着攻击权威,因为荷马是在神话上最权威的代表,“他将为人类所犯而大家公认为不名誉的行为归于神负责”,色诺芬批评荷马,推翻荷马的权威,就是言论自由的表现,就是思想自由的行动。
而在科学意义上,德谟克利特和赫拉克利特的学说,就是用理性观察宇宙的代表,他们破除了常识中不合理性的观念,成为了当时的唯物论者。当然,伯里在论述“逼害”中产生的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时,必须提及的一个代表人物则是苏格拉底,喝酒诡辩派不同的是,他是教育者中最伟大者,不仅他提倡自由讨论,而且在被判决后拥护言论自由——在伯里看来,苏格拉底的标志性意义在于:一,他坚持个人对任何权威或法庭的强迫就范采取拒绝的态度;二,他坚持“自由言论的公共价值”,认为这是最高的善,“我是你们的刺激性的批评者,以劝说和谴责坚执不移地来告诫你们,又反复检验你们的意见,希冀你们明了你们所认为你们已知道的事物,你们实毫然不知,能够日日讨论从我听得的诸问题,就是为人最高的善,未用这种讨论检证过的生活是无价值的生活。”从这两点来看,苏格拉底之所以成为自由的代表,就在于他面对的是“逼害”的世界,“逼害”的世界必然引出两个问题:谁来逼害?怎么逼害?而这两个问题也必引出关于自由的意义:自由是对逼害的反抗,就是对权威的反抗,逼害指向的是虐行和危险思想的流传,自由便是对之的维护,所以伯里认为,“但要稳固地建设思想自由的学理,尚须有逼害的理论和实际的长期经验,后来基督教所取的压迫政策及其种种结果就驱使理性为这个问题而奋斗,使理理智自由终得辩明了。”
| 编号:B62·2070516·0745 |
中世纪便是理性被禁锢的时代,便是逼害扼杀自由的时代:奥古斯丁作为最受尊敬、最高权威的教父,他制定了逼害的公则,那就是圣书中耶稣基督所用的“强迫他们进来”的那句话;十三世纪的教皇英诺森让西欧的基督教势力达到了极点,对异教徒的扫除成为了逼害的主要行为;宗教裁判所遍布西欧个基督教国家,“全欧洲大陆的法庭有一个链子连系着。”它们是逼害的机构;基督教会用于法庭诉讼的程序便成为逼害的法律依据,它破坏的是欧洲大陆的刑事法律体系——中世纪的种种逼害,其源头正是基督教被采用,就是宽容主义被扼杀,“这重大的决议就使一千年中理性受着束缚,思想被奴役,而知识无进步。”漫长的中世纪,逼害导致了理性、思想和知识的发展,一直到十三世纪的意大利,“由轻信和愚稚所织成而蒙蔽着人们的灵魂使不能了解自身和他们对于宇宙的关系的雾幕开始揭开了。”这便是人文主义开始的文艺复兴时代,从文艺的复兴开始,文化成为反对正统信仰的理智革命,渐渐的理性被解放,知识被恢复,同时在政治上也促进了思想自由的出现。
实际上,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其转变最重要的则是宗教意义上的,欧洲教会势力的失坠、神圣罗马帝国的衰落,都是宗教权威影响失势的象征,强有力君主的产生,近代国家的发展,使得教会政策发生了改变,在这样的背景下,于是开始了宗教改革。在伯里看来,认为宗教改革建设了信教自由和个人判断权,其实是错误的,宗教改革的最大意义不是提供了信教的自由,而是形成了某种新的政治和社会状况,是政治和社会的进步才有自由的成功——那就是宽容主义,“同时政治环境的势力逼迫着各政府不专维护一种教条,而也宽容其他的基督教派;为着俗世的利益,排他的救渡说也打破了。信教自由实是达到完全的思想自由的一重要步骤。”
逼害来源于基督教,信教自由来源于宗教改革,思想自由史其实就是一部宗教改革史,它的矛盾之产生和解决都是在宗教意义上的,而本质上,从逼害到自由,就是不宽容和宽容的区别,所以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所呼吁和促进的就是宽容主义,所反对和反抗的就是不宽容主义。其中的领袖则是伏尔泰,他对卡拉研案判决的最终改变就是对“不义逼害案”的积极辩论,他的成功归结为理性的胜利,“在巴黎的宗教狂妄行动,虽有势力,但总受理性的支配。”之后的法国革命建设了信教的自由,而在德国宽容的产生来自于普鲁士的政治利益的动机。欧洲各国从宗教改革的宽容主义建立起了自由制度,而这些自由制度最后促进了十七世纪与十八世纪的唯理论的发生,伯里认为,唯理论的进步分成两个时期,一个时期是思想家对矛盾、悖理、荒诞和教条道德等方面的攻击,逐渐萌发了科学精神,洛克、霍布斯、斯宾诺莎都通过理性发现真理;第二个时期则是在十九世纪,各方面科学的发现,直接冲击了草昧时代的思想,推翻了那些权威,那些自由思想家和唯物论者成为了斗士。
科学的发展不仅产生了唯理论,也使得唯理论从发生到进步建立了它的一元论与实证哲学。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万有引力和血液循环的发现、黑格尔的进化哲学、斯宾塞和孔德的科学宇宙观,为唯理论进步时代的到来创造了条件,而《人类的世系》之出版,更是以“一种新的非独断的基督教”的方式开始了宣说,莱斯利·斯蒂芬认为,“教义中没有哪一项不能被驳倒,不仅如此,即使在布道中,倘布道者希望赢得正统的名声,希望他的行为被视为一种明智地谋求主教职位的努力,那也没有哪一项教义不能被驳倒。”基督教不再只是宽容的基督教,在科学精神中,它甚至被视为另一种异端,罗斯金、莫里斯和拉斐尔画家,都成为了反基督教的艺术家,而一元论、实证哲学和孔德宗教相结合就是“完全以科学为基础而排斥神学、神秘主义和玄学的人生观”。
从基督教的逼害到宗教改革之后的宽容,再到科学精神对神学的排斥,思想自由史看起来更多是思想家对宗教反抗、改造的历史,宗教在历史进程中扮演了多元的角色。但是回到从言论自由到思想自由的自由主义,伯里最后提出的观点是:自由不是根据抽象的基础,不是根据独立社会的原则,“却完全根据于功利观念”。为什么自由是一种对于功利观念的实践?伯里认为,言论自由的目的是促进知识的进步,“要得社会习惯制度和方法能适应新需要和新环境,自然必得有辩驳,批评社会习惯、制度和方法以及发表最违俗的思想的完全自由,固不必顾虑是否触犯着流行的思想。”思想自由是社会进步的最高条件,也就意味着它不属于寻常利益的范围里,而属于我们称为“正道”的更高利益,也就是说,这是“人人应该认可的一种权利”,这就是一种功利,它是日常的、合理的、正当的、基本的权利,“现在在最文明、最进步国家里,言论自由已被公认是一种根本原则了。实际上,我们可以说,它已被视为判定文明的标准了。”
思想自由是言论自由,言论自由是理性反抗权威的结果,是功利的自由,是文明的标志,当然更是历史走向未来的公则:“在今日,关于思想自由是人类进步的公则的话,当无遗漏地统统揭示给青年们。”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37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