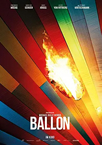2020-10-29《气球》:升空和坠落的自由传奇

从热气球上掉落的彼特和甘特做出了投降状,看到的却是来自巴伐利亚的伐木工人,于是他们高喊:“我们成功了”;加强了边境巡逻并动用了直升机的中校看见信号弹在夜空中亮起,无奈地说了一句:“白忙了一场。”隔着铁丝网,一边是成功的喜悦,一边是失败的无奈,当两种命运成为这个夜晚的写照,这出夹杂着太多运气的“惊天大逃亡”终于从一个囚禁之地去往了自由王国,而根据1979年“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也变成了一出来源于现实又超越现实的传奇。
导演米夏埃尔·赫尔比希把这个真实事件改编成传奇的目的是明显的,1976年9月16日,来自东德的两个家庭共八个人,用他们自制的热气球跨越了边境线,飞越了铁丝网,飞行18公里,用28分钟的时间实现了“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逃亡”。为什么伟大?因为他们冒着被逮捕、被枪杀的危险,毅然选择了逃亡,甚至还留着年迈的母亲,甚至还有亲人在东德,而且,热气球并不能保证百分之百去往西德,在充满了各种变数的行动中,在随时可能被发现的危险中,在孤注一掷的逃亡里,成功只是小概率事件,但是他们却将这一切变成了现实,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偶然而成为必然的背后,是对于自由的向往。
越是将这种危险性表现出来,就越能展现对自由向往的不可阻挡性,所以米夏埃尔·赫尔比希制造了太多的冲突。首先在宏观叙事中,他一开始就打出了字幕,“1976年至1988年间,38000名东德人企图逃亡西德而失败,至少有462人在边界丧命,他们被烙上了叛国贼的标签……”数字是历史的一部分,它是客观的,但是不免有些枯燥,于是米夏埃尔·赫尔比希用一个视觉强烈的镜头来说明失败者的命运:黑夜中有人试图翻越铁丝网,但是被巡逻的士兵发现,于是枪声响起,越境者中弹,他倒在东德边境这一侧,连死都无法实现跨越的他,最后呈现的是一张血肉模糊的脸——死去的462人或许都像他一样,在被烙上了叛国贼罪名之后,死无葬身之地,而且还会连累家人和朋友。
宏观的数据和微观的惨状之外,米夏埃尔·赫尔比希用从当事人的惊险逃亡中制造冲突,两个家庭花费了两年时间筹划这一次逃亡,当万事俱备,意外出现了:负责缝制热气球的甘特说,这个气球不能承载八个人,所以他决定让彼特一家坐上气球去往西德。彼得决定当天晚上就行动,大儿子法兰克似乎早就知道了这个计划,但是年幼的小儿子费奇对此一无所知,他甚至在白天的课堂上被学校老师要求唱起歌颂社会主义的歌曲,所以对于几乎被洗脑的费奇,一家人开始了启发,与其说是启发,不如说是欺骗,母亲朵乐丝告诉他晚上去露营,当费奇还有疑虑的时候,朵乐丝终于告诉他,我们是去西德,还答应他去了西德之后给他买脚踏车。当一家人开着车带着热气球来到边境树林的空地,费奇开始害怕,但是朵乐丝护住他,四个人终于上了热气球,气球开始慢慢上升,正当气球在大风的助力下穿越云层向西德方向进发的时候,由于高度太高,瓦斯管受冷,燃料未能充满燃烧,于是在升空14分钟之后,气球熄火,并慢慢坠落。
没有越过边界,对于彼特一家人来说,这并不只是简单的计划失败,对于他们来说面对的是比制作热气球更危险的局面,因为他们没有飞过铁丝网,他们重新回到了东德,他们的整个行动都可能被秘密警察发现,由此这场大冒险变得让人窒息:中校发现了热气球之后,开始了大搜捕,这场计划实施中的热气球布料、瓦斯管、蓝色瓦特堡车都会成为暴露行动的证据,甚至朵乐丝还不小心忘记了那张甲状腺的处方签,而处方签上有编号。除了这些可能的物证之外,彼特一家对面住的是秘密警察艾瑞克,艾瑞克和彼特是邻居,艾瑞克的女儿克拉拉和彼特的儿子法兰克则是情侣,在他们交往中很容易走漏风声。
| 导演: 米夏埃尔·赫尔比希 |
米夏埃尔·赫尔比希制造的悬念还不止这些,朵乐丝在第一次失败之后开始了犹豫,她内心似乎有了某种阴影,“我不想失去孩子。”她的第一愿望不是为了追求自由,而是为了不家破人亡,这个从理想主义到现实主义的转变,让整个家庭的逃亡计划变得扑朔迷离;而在计划失败之后,彼特一家也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他们总觉得一双双眼睛正盯着他们,无论是敲门打听国庆节准备国旗的政府人员,还是酒店大堂正在看报的陌生人,在他们看来仿佛都有秘密警察的影子,而他们试图寻找美国大使馆以求政治避难的计划也最后破产,那被放在经过女士包里的烟盒上写着求救信,最后也是没有了下文;最重要的是,甘特接到了征召令,他将在六周后入伍,如果这个计划想要继续实施,一定少不了甘特,而甘特父亲对他说“你有大好人生”的期盼,更是让甘特处在命运的十字路口。
在情况变得危急的时刻,米夏埃尔·赫尔比希并没有停止制造悬念,反而加大了悬疑力度:两家人决定再做一个热气球。于是他们又开始买布,只不过采取接替购买的方式躲过纳西耳目;他们开始在地下室里缝制热气球,为了不让邻居起疑,甘特和妻子佩特拉假装来彼特家聚会而喝醉酒的朋友,摇晃着开着摩托车走了;甘特的孩子在幼儿园老师问爸爸最近在干什么时,他竟然说在缝纫机上缝东西,幸亏在中校来学校探口风的时候,老师说他们家在赶制国庆的国旗,才化险为夷……裁制、缝纫、焊接,两家人冒着危险制作热气球,开始第二次大逃亡,而这一次几乎就是在秘密警察眼皮底下发生,当他们正逐步掌握情况慢慢接近真相时,起风的日子终于来到了,他们将热气球运到了树林的空地,然后点燃了瓦斯罐,但是法兰克却没有及时割破最后一根绳子,在热气球摇晃着升空并燃着了布料时,这个计划似乎又向着失败迈进,幸亏绳子最后被割断了,八个人也终于随着热气球升到了空中,但是因为顶部缺了布料,再加上上空气温骤降,热气球上的火焰又慢慢变小,最后甚至和第一次一样熄灭了。
火焰熄灭,气球下坠,在惊恐声中最后落入到黑暗中,这似乎又是第一次计划的翻版,但是当彼特和甘特从树林中走出,看到大路上的卡车和从车上下来的人时,他们以为自己难以逃离秘密警察的逮捕,但他们听到的却是:“这里是巴伐利亚。”他们才知道在28分钟的升空中,气球已经越过了边界,落在了他们想要到达的西德土地,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一个自由的世界,虽然狼狈,但是终归逃离了东德的追捕,终归远离了被逮捕被处决的命运,在“我们成功了”的欢呼声中,从此走向了自由。在种种危险的铺垫中,在命运被悬于未知世界的时候,米夏埃尔·赫尔比希似乎达到了制造传奇的目的,让这个在历史上发生的真实事件演变成了更富视觉冲击的传奇。但是,在这个影像化的过程中,当真实事件被赋予了太多传奇色彩,是不是反倒变成了一种虚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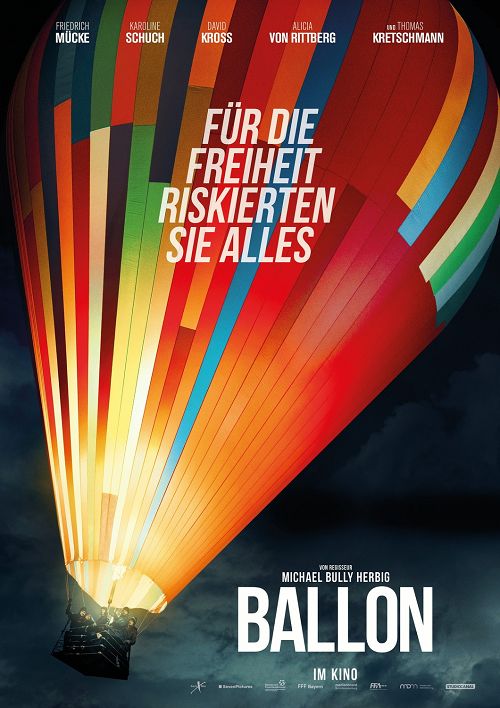
《气球》电影海报
很明显,米夏埃尔·赫尔比希设置了电影可以被阐释的中心,那就是两家人为什么冒着生命危险不惜一切代价想要追寻自由?就像中校对疏于值守的中尉说的那样:“我们做了什么,使他们要冒着重罪的危险?”这或者也是那个时代那个国家的疑问,这是这个惊天大逃亡计划得以一而再实施的原因,也是整部电影最基本的逻辑主线,但是米夏埃尔·赫尔比希显然没有设置好这个逻辑的起点。在电影中,有许多关于东德社会不自由甚至囚禁式的描写,比如朵乐丝曾经闪回了自己弟弟惨遭迫害的镜头,正因为此,她才想要一家人平安;在计划失败之后,彼特一家人走在街上总感觉有无数双眼睛在监视着他们;在搜查行动中,秘密警察也可以动用一切资源,从布料店到药房,都在查找他们的踪迹……但是这些并不能构成东德专制现实的真实写照,他们对身旁人的怀疑只是自己的敏感而已,而秘密警察对案件进行调查似乎也是在行使自己的权利。
而且,对于彼特和甘特两家人的逃亡理由,似乎也是不充分的,他们拥有稳定的工作,家境也算殷实,不管是生活还是孩子的教育,至少都没有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他们选择冒险似乎仅仅是行动本身,或者说,只是那个时代的一个样本而已,米夏埃尔·赫尔比希没有凸显他们的遭遇,当他只是在随机中选择这两家人成为“叛国者”,便缺失了说服力。而在表现这个逃亡计划时,又因为可以强化传奇性,反倒失了最基本的叙事逻辑。第一次计划失败,他们其实留下了太多证据,比如那辆蓝色的瓦特堡车,比如那些瓦斯罐,比如制作气球的大批布料,更成为直接破案线索的则是朵乐丝留下的那张带有编号的处方签,只要从药房里找到编号所对应的患者名字,这个案子就完全没有了悬疑,但是那些秘密警察在查找这些证据时,显得极为愚笨,直到他们制作完成了第二个热气球,并开始了第二次升空,中校才找到了那间秘密地下室——从第一个气球花费两年时间制作,到第二个气球只花费短短几天,这其中的传奇性完全变成了米夏埃尔·赫尔比希的人为设置。
而更为奇怪的是,当秘密警察发现了真相开始在边境大肆搜捕的时候,两家人竟也能躲开他们奇迹升空:中校带人闯入了制作热气球的地下室,发现了一切秘密,于是在确定的区域里布防设卡,而此时彼特因为要接佩特拉竟然开着那辆蓝色瓦特堡在路上行驶,他们甚至看见了前面设卡的警察,一个掉头竟然避开了他们;甘特开着摩托车去带忘了钥匙的法兰克,路上真的遭遇了正在盘查的警察,当警察要查看他的证件时,甘特知道自己一旦拿出证件就意味着被抓捕,就在这个时候警察发现了另外的线索,竟然离开了,使得甘特顺利和彼特汇合;在气球升空之后,还是遭遇了问题,甚至最后还是熄火掉落下来,在大家都认为这次再也难以逃脱时,命运却把他们带到了西德境内——这只是一次有关运气的偶然成功,在通往自由之路上,他们随时可能成为叛国贼,随时会被送入牢房,随时别结束生命。
胜利的偶然性,也许也是这场惊天大逃亡成为传奇的一个原因,也折射出自由之路的艰辛,从这个意义上强化了“我们做了什么,使他们要冒着重罪的危险?”的主题,但是在缺乏了逻辑的故事里,在抽离了现实的剧情里,一只气球的升空和坠落完全和物理学无关,它也变成了一种向往自由的传奇。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41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