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10-29 《阳光灿烂的日子》:像少年一样随波逐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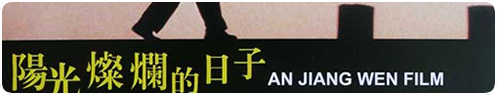
“北京,变得这么快,20年的功夫她已成为了一个现代化的城市,我几乎从中找不到任何记忆里的东西。事实上,这种变化已经破坏了我的记忆,使我分不清幻觉和真实。我的故事总是发生在夏天,炎热的气候使人们裸露得更多,也更难以掩饰心中的欲望。那时候好像永远是夏天,太阳总是有空出来伴随着我,阳光充足,太亮了,使眼前一阵阵发黑……”街上行驶的汽车,观望着已经改变的一切,总是夏天,总是炎热,却总是隔着遥远的距离,时间从现在拉回到记忆,是20年,而其实,从记忆拉回到现在,似乎也是20年。如果从一个不是夏天的午后开始回返,距离那“阳光灿烂的日子”刚好是20年,20年的学生时代,20年的青春岁月,一部电影的首映式在陌生的城市上演,而其实,在那20年前的记忆中,分明出现了不在电影中真实的夏雨、宁静,他们站在首映的舞台上,满面笑容,讲述着电影有关的故事。台上和台下,隔着几十排的座位,却似乎隔着一个时代,只是在那舞台上,并无炎热的阳光,并无虚构的欲望,那个夏天其实早就过去了,而电影里的世界却有限地复原了一种蓬勃却残缺的青春,于20年前的每一个少年来说,都已经分不清幻觉和真实。
|
| 导演: 姜文 |
 |
“等等!”在阳光灿烂的日子,一句“等等”寄托着被发现新的可能,预示着某种和现实无关的虚构,等等是20年后的回返,等等是20年前的片段,等等也是一个残缺时代最无奈的解释。残缺时代一定对应着现实的不完整,当米兰和我断绝往来,当刘忆苦当兵后被炮弹震傻,所有“等等”的结局都变成了一句话:“再后来,音讯全无。”是的,不完整的现实里,必须寻找某种能带入“前现实”的东西,而这种东西便是记忆。记忆里是革命,是激情,是“这座城市属于我们”的自由,是“这是谁干的”的笑谑,是撬开每一道锁的快意和刺激,封闭的世界被打开的时候,那锁舌跳出来的感觉就像是对世界的致命一击,可是,每一道锁,每一扇门的背后并不是一个全然开放的世界,并不是完好如初的现实,它杂夹着幻觉和真实,无法真正拼贴出一幅完整的图景。
记忆总是在最希望保存完整世界的时候打破,而残缺的记忆里或许根本没有那台老式苏联黑白电视机,没有历史老师讲述的《中俄尼布楚条约》和风中装满煤球的草帽,没有奶奶拉着小孩在过道上好奇而凝望的眼神,没有拿着望远镜看见那穿着泳装的少女照片,那么在记忆中到底留下的是什么?米兰出现在马小军的面前的时候,他对她说的第一句话是:“我好像哪里见过你?”好像见过的暗示最后变成了米兰眼中的某种不屑,小毛孩是她对于马小军的命名,可是这样不对称的关系还是依靠着残缺的记忆进行复原。所以对于马小军来说,米兰是一种象征,是一个期望展开的完整世界的投影。在那次冲洗头发之后,米兰客气地问他学习和生活,而马小军在收获了赠送的那支三色圆珠笔时,开始按照虚构的方式新建了一个“他者”,他把自己扮成一个与年龄极不相称的胆大妄为的强盗,给米兰讲述自己的传奇故事,而这样的故事最后又成为了幻觉,甚至几次在米兰家里睡着的记忆都变成了幻觉,“或者我根本没有在那里睡过。”可是这样的幻觉不真实,又如何跑到我脑子里呢?
 |
| 《阳光灿烂的日子》电影海报 |
“或者”和那个“等等”一样,是一种可能之后的不可能,也是不可能之后的可能,肯定和否定,就像幻觉和真实一样,已经分不清了,只是米兰性感的身体和锥子般的目光,总是让我进入到已经安排的记忆之中,尽管破碎,却能让我满足。送米兰去农场的那条林荫道上,米兰是坐在马小军的身后抱着他的腰,“那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一天,晨风的抚摸使我一阵阵起了鸡皮疙瘩,周身发麻。我还记得有股烧荒草的味道特别好闻,可是大夏天哪来的荒草呢,但无论怎样,记忆中那年夏天发生的事总是伴随着那么一股烧荒草的味道。”美好总是会掩盖记忆的脆弱性和易碎性,以致在那梦中反复出现的时候,就像回到了可以触摸的现实。但是当现实真的被击得粉碎的时候,记忆又以虚构的方式掩盖现实的破败。那在老莫餐厅过的生日里,硬币游戏的隐喻并不是最为刺激的,而在马小军生气带来的怒吼声中,他像一个自己塑造的英雄,手拿砸破的啤酒瓶朝刘忆苦猛扎过去,可是这样的记忆注定要在“等等”的画外音中变成一场幻觉中的闹剧,“我发誓要老老实实讲故事,可是说真话的愿望有多么强烈,受到的干扰就有多么大,我悲哀的发现根本就无法还原真实。记忆总是被我的情感改头换面,并随之捉弄我,背叛我,把我搞得头脑混乱,真伪不辨。我以真诚的愿望开始讲述的故事,经过巨大坚韧不拔的努力居然变成了谎言,有时候一种声音,或是一种味道可以把人带回真实的过去。”老老实实讲故事是不是马小军的初衷?为什么最后的真实都变成了谎言?但是,当我开始讲述另一个版本的生日,那欢笑,那和谐,那醉酒,一切都解构着暴力的版本,但是这个充满着欢声笑语的生日版本难道一定就是真实的?它是不是对于另一种真实的篡改?
是谎言代替了真实,还是现实隐瞒了虚构?那喝醉的雨夜,当马小军骑车赶过去而落入泥潭的时候,米兰从房子里走出来,马小军大喊一声“米兰,我喜欢你”,但是当米兰问他,你说什么的时候,他却回答:“车掉沟里了。”车掉沟里是现实,还是那句“米兰,我喜欢”是现实?其实并不是分不清幻觉和真实,而是当现实出现残缺的时候,便用记忆来修补,而当记忆出现的残缺,便用幻觉来修补。但是不管何种修补方式,对于少年马小军来说,那无法阻止的欲望总是以不合时宜的方式出现,所以记忆的残缺其实根本就是肉体欲望的残缺。
马小军的欲望毛孔张开,是在那隔着窗户玻璃看见女孩子们在跳芭蕾舞,这是一种懵懂的窥探,窗外和窗内,隔开了两个不同的世界,所以对于欲望的探寻始终是偷偷摸摸的,而这样的窥探是从肉体的局部开始的,那一双舞动的脚支撑起了少年全部的遐想,可是那被石头砸碎的玻璃预示着窥探最后的失败。而在书包扔上天空以蒙太奇的方式表现一种成长的时候,马小军的世界依然没有对于一双脚的窥探。打开那一道暗锁,鬼使神差地进入了陌生的房间,而在这个自由的房间里,马小军用墙上的望远镜窥探着外面的世界,胡老师上厕所的那一幕给他一种满足,而当他用望远镜扫描到蚊帐后面的墙上挂着那一张穿泳衣少女的照片时,内心被触动的感觉一下子打开了欲望的毛孔。经过多次捕捉和定位,那张照片逐渐清晰,并在自己的内心深处投射出欲望的影子。一张照片带来的是幻觉,一根头发带来的是想象,在这幻觉和想象中,马小军像一只热皮屋顶上的猫寻找真实的那个女孩出现。而当米兰真的出现在马小军面前的时候,就是那一双脚,从床底下看到换鞋子的脚,对于马晓军来说,激发出来的是更小童年的那种记忆,这种记忆一旦被复活,幻觉就会成倍成倍地增加。一双脚之后,在那个朝鲜代表团演出的门外,马小军又一次注意到出现在眼前的那双脚,而在那次从地上见火柴的时候,马小军又看见了熟悉的那双脚,最后跟着这双脚,终于从记忆之中打开了欲望的门,那一句“我好像见过你”,便把真实的米兰和想象着的米兰合二为一,而一双脚也似乎完成了欲望投身的意义,从局部肉体变成完整的身体。
但是这种转变对于马小军来说,并不是欲望的完全展现。在米兰面前,他是一个毛孩子,年龄和经历的差异在他们之间是不会产生所谓的爱情,即使暧昧,马小军也知道只是一种类似姐姐的懵懂保护,可是对于马小军来说,这样的保护实际上摧毁着他的英雄主义,“我最大的理想就是中苏开战,因为我坚信,在新的世界大战中,我军的铁拳定会把苏美两国的战争机器砸得粉碎,一名举世瞩目的战争英雄将由此诞生,那就是我。”这是马小军的英雄主义理想,从学校偷偷溜出之后,他在自己的家里打开父亲的抽屉,戴着老爸的军功章、军衔,在镜子前耀武扬威,这便是一种虚无的英雄主义。在被警察抓去被训斥了一顿之后,回到镜子面前,马小军又恢复了那种英雄气概:“我还明告诉你了,我明儿还去那拍,我就一个人去,你要不去逮我你是我孙子。我震东单震西单,我还震你们炮局呢!行行行,擦鼻涕滚蛋。滚不滚,你不愿意滚就在这儿多呆两天。”这无非对于警察训斥他的那一段话的模仿,或者在这样自我世界里,他才是一个英雄。而面对米兰,他也想着自己去保护女人,所以这样的英雄主义就变成了对于欲望的征服。在带米兰见那些大院里的兄弟的时候,他眼见着米兰和刘忆苦眉来眼去,便模拟“列宁在一九一八”的电影情节,表现一种英雄主义情结,而爬上那根大烟囱也就是这样表现的极致表达,最后奇迹般地跌落而没有受伤,看起来是英雄主义的极大胜利,但实际上是一种溃败,一种歇斯底里的疯狂爆发,所以和米兰的暧昧自然变成了一种无法满足的残缺,参加姥爷葬礼回来的时候,在马小军面前的还是那一双脚,只是这时的米兰似乎已经和刘忆苦更近地走到了一起,所以这时候的那双脚完全变成了对自己欲望的伤害,那一晚,马小军穿着不整的军服,抽着烟,看着米兰和刘忆苦跳着舞蹈,这是他内心英雄主义的溃败,也是欲望的彻底浇灭。所以当最后的冲动爆发的时候,马小军连滚带爬冲上楼梯,打开房门,把米兰压在身下,但是在挣扎和打闹中,最后脱身的竟然是马小军,而那一句带着哭泣和疯狂的“有劲”则构成了一个“强暴-反强暴”的对立关系,实际上,要征服米兰的马小军最后变成了被征服者,而一双脚的欲望也彻底泯灭了。
强暴和反强暴,征服和被征服,欲望的残缺,并非是米兰的反抗,而是某种无法逃避的时代病症。扔上书包而掉落书包,这是马小军成长的仪式,而那一句“我操”打开了少年的暴力和欲望世界,但是这样的欲望总是小心翼翼,这样的暴力总是带着病态,马小军窥探世界中的那个避孕套被当成了娱乐的气球,而最后因为被吹破而使母亲怀孕自己有了弟弟,这是一种被压抑的释放,却带着母亲歇斯底里的怒骂。而在《列宁在一九一八》的电影世界之外,是那在影院里播放的禁片,一部是在大院公开放映,一部只在室内供特殊的干部观看,而当马小军等人偷看这带着女性裸露镜头的电影时,象征权威的老军人站起来,受批判的电影,毒性很大,而真正有毒的或者是那些权威,而马小军对于权威的反抗早就在镜子面前模仿警察的骂声里体现出来,但是这样的反抗是自娱式的,而那个关于裸露镜头的电影依然构筑了马小军畸变的欲望世界,直至他在反强暴的米兰前面说出那句“有劲”,才使自己残缺的欲望得到了暂时的满足。
而实际上,残缺的记忆,残缺的欲望,给马小军带来的是虚幻的理想和虚幻的爱情,在“革命风雷激荡,战士胸有朝阳”的歌声里,在“欢迎欢迎,热烈欢迎”的欢迎仪式中,在“瓦西里”的呐喊声中,马小军其实在一种逃避中构筑属于自己的完整世界,但是这样的构筑却从类没有给他带来真实感,他一直游离在那个时代的边缘,总是夏天,总是阳光,只是这样的阳光灿烂的日子并不是健康,并不是和暖,却是一种强烈的照射,一种看不清真实世界的照耀,革命、英雄的70年代或者就是充满阳光的时代,但是给马小军这样的少年带来的只是一种精神的残缺,那里有大人的谩骂,有老师的怒喝,有警察的训斥,在他面前永远有秩序,有规则,即使能够打开那些锁,即使像英雄一样从烟囱里掉落而大难不死,但是现实依然隔开着自由,隔开着欲望,隔开着英雄,大院里的傻子在听到“古伦木”之后,总是回应着“欧巴”,“古伦木-欧巴”的话语体系曾经是智取威虎山的暗号,闪耀着革命英雄主义的光芒,但是却变成疯癫的话语体系,这种反英雄主义正是这个时代精神残缺的一种讽刺。
记忆的残缺,欲望的残缺和精神的残缺,在20年不断出现“等等”的叙述中,没有什么是完整的,当记忆破碎,当欲望泯灭,当精神沦落,青春的少年只能随波逐流,而在20年后再次回到现实的时候,真正完整的就只有那个架着木棍的傻子,一声“古伦木”之后依然还是那句“欧巴”,只是这已经不具备反英雄主义的隐喻,而成为无法逃避现实的一种真实写照,这座城市已经不属于我们,那个远去的时代也成为一个假象。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6143]
思前: 醒来的无意义
顾后: 《暗铺街》:其实我们都是海滩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