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1-01应该,回到现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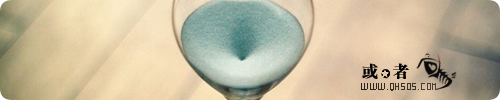
当那只黑鸟飞出了视线,
它标记下多个
圆圈之一的边缘。
——史蒂文斯《注视一只黑鸟的十三种方式》
1428,是2019年降下帷幕的时候,我在豆瓣上标记的“看过”电影的总数,尽管最后那部《美国狼人在伦敦》是2018年观影的片目,当它被纳入到2019年观影历史的时候,是不是意味着对某种逝去时间的追忆?对某种时间和经历的补充?
有些隐喻的不是偶然看见这部电影而放进了错位的时间列表里,而是那个作为整体的数字1428,如果转换成时间形式,它指向的是2008年发生的那次大地震地动山摇的那一刻,而一部名为《1428》的纪录片正是记录大地震之下的众生。但是当我在2020年的第一天重新开始标记看过的电影、阅读过的图书时,无论如何也找不到这一条目。它曾经出现在豆瓣中,出现在我的历史中,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当2015年我去贵州铜仁出差的时候,就是在那个陌生之地用手机观影了这一部纪录片,连同马尔克斯的《苦妓回忆录》,一起构成了我旅途中不多的阅读体验,而在写好影评之后,我也是从豆瓣上获取了这部纪录片相关的信息:导演: 杜海滨,类型: 纪录片,制片国家/地区: 中国大陆,语言: 汉语普通话,上映日期: 2009年,片长: 115分钟……
但是,当2015年并未很久远地离开,“1428”便真的成为了一个被抽离的事件,在豆瓣搜索,只是得到了一部43分钟的泰国短片的信息。不知道关于这部电影到底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经历了去年那场风波的豆瓣是不是遭遇了更大的压力,当一部电影被抽离当“1428”成为沉默的数字,也许现实里的确不能记录真相,杜海滨曾经说过,“灾难是一个特殊的背景,在这个不同寻常的背景下,人性的光明和阴暗被凸显的一览无遗。”似乎一语成谶,而在远离历史的时间里,一切都变成了数字谜题。
一种感想似乎是在偶然之中涌现出来的,当2020年正式启幕的第一天,开始重新标注电影和图书,是希望回到现场,即使是一种仪式,也需要用一种记录的方式证明曾经来过。或者是从1428部电影被补充标记的时候获得的感悟,从2011年加入豆瓣开始,似乎一直没有作为标记的工具在使用,只是当写好了自己还满意的评论,便在豆瓣上发布出来。所以,从2011年到2018年末,标记的电影和图书都只有100多部。从2018年豆瓣推出便捷式标记电影的程序开始,才一股脑儿将以前看过的大部分电影标记完成,而从2019年开始,正式遵守标记的规则,当一部电影看完、当一本书阅读完毕,会在第一时间在豆瓣上点击“看过”按钮,然后做出五星制的评分。
2019年的标记是完整的,但是作为整体来说,仅仅一年的标记当然无法反映我的阅读和观影历史,粗粗统计了一下,到2019年底,看过的电影在1700部左右,阅读过的图书则在1300部左右,所以为了体现自己多年的观影和阅读经历,决定在2020年开启之时进行集中补记——并非是为了得到一种数字,而是希望真正构建一种观者的历史,只有在“看过”和“读过”的意义上,我才是在历史的那个现场里,虽然在时间上补充标记一定会造成时间的错位,但是作为一种追忆,它或许有一种带入到记忆之中的在场感。于是,在对电影零星补充的同时,开始按照“千克读品”上的记录,一本一本进行搜索,同一本书名会有各种不同的版本,同一版本不同的出版次数也可能会有不同的封面,所以在很早以前的图书,基本上要从记忆深处去追寻片段的信息,还好,大部分图书能够按图索骥找到当年阅读的版本,于是,标注为“看过”,于是放进了书影音档案里。
从2008年以前的那些图书,到2008年之后每年阅读的书目,不厌其烦地搜索、确认、标记,当2018年最后一本《注视一只黑鸟的十三种方式》标记完成,豆瓣上显示看过的图书是1235册,基本符合我阅读的总数,连同1600部电影,构成了我作为观者整体的数字。但是,在标记过程中,也出现如“1428”年被抽离的那种感觉,我这一生阅读的第一本图书,按照我最大限度的回忆是那本《金箫玄剑》,而且此前也从网上搜到了相关的书影,但是在豆瓣上却搜不到相关信息,所以从起点开始的“1”就成了一种无,不免让人遗憾。或许是年代太过久远,文学价值也不高,所以没有人建立相关条目,但是有些书年代并不久远,也没有什么敏感内容,却也无法搜寻到,比如鲁羊的《在北京奔跑》,在豆瓣上也是空无,有《吃在北京》《混在北京》《爱在北京》,却没有“在北京奔跑”。
也许北京没有奔跑的人,也许奔跑的人不在北京,一种缺失,一种空无,似乎是对于“在”这个字的最大讽刺,所有的标记是为了一种在场感,所有补充的标记是为了追忆历史中在场的时间,无论如何,都是为了回到现场,而当文本本身就成为了一种缺省,所有的种种记录,都将成为无历史的历史,搁置在已经发生的时间里,看上去却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当文本制造了不在场的证明,当历史被抽离,或许给人的启示是:不是回到现场,而是当你真正在当下的时候保留现场、记录现场,所以每一天都应该进入现场,每一天都应该被标记,每一天也都是不可复制和不可追忆的现在。
可是,一种理想主义的在场总是会遭到现实的破坏:多年跨年夜形成的仪式是看一场电影,但是小五却否定了,于是在夜不出户中送走了必然要离开的2019年;新年第一天的仪式是在同一个场所为小五拍一张成长记录照,但是直到下午将他送到学校门口,才想起这件事,最后在只留下背影的下午,第一天在场的照片便永远不在……一只黑鸟飞过,一声叹息,永远在离开时想到回来,永远在未来想要回望现在,“你属于我,但只是在那永不磨灭的记忆里面,/而不是在以日为计的瞬息之中。”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2302]
思前:关闭一个出口的十九种方式
顾后:像枯枝掩盖枯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