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01-17《巴赫曼先生和他的学生》:历史不是一个循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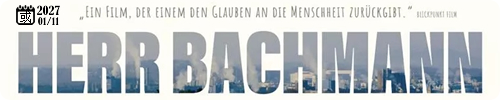
当孩子们一个一个和他拥抱而离开,当教室里只有空空的桌子和椅子,当一批学生结束学业开始新的征程,巴赫曼一个人坐在那里,对着空荡荡的教室,他的背影显得有些孤独,头上Hasan送给他的那顶帽子似乎也成为最后的象征。这是“巴赫曼先生和他的学生”这个统一体走向终结的时刻,对于即将退休的巴赫曼来说,这是不是也是一次充满仪式的告别?而他对孩子们说的“你们都是很棒的孩子,记得坚守你们的纯真”是不是也是他一生恪守的格言?
“巴赫曼先生和他的学生”,片名就是将巴赫曼和“他的学生”结合在一起,缺了谁似乎都可能变得不完整,但是这种结合是在什么意义上完成的?学校的一天从黑暗开始,这是属于学生的每一个清晨:他们在路边等待校车的到来,他们买来点心当早餐,他们坐上校车抵达学校,他们走进教室,“谁还没有来?”一个声音传来,学生们议论着,那个声音让孩子们走出去再走进来,在混乱和吵闹结束之后,学生们坐在自己的位置上,声音继续:“你们再睡一会儿吧。”于是孩子们靠在课桌椅上,等孩子醒来,这个声音便开始了精彩的讲课。
这是属于每个学生的普通一天,这是属于巴赫曼先生的普通一天,当“学生们”出现在清晨的校车上,进入亮着灯的教室,坐在自己的位置上,在另一边仅仅是对他们说话的声音传来,这是巴赫曼的声音,但是只有声音他的形象并没有出现,这像是一种“只闻其声”的缺席,然后在镜头的切换中,坐在讲台那边的巴赫曼才现身。先扬后抑,先声音后形象,无疑设置了某种悬念,这种悬念也正是为了让巴赫曼保留足够的神秘,但更重要的意义,是在这铺垫之后让“巴赫曼先生和他的学生”在一个也不少的情况下成为一个整体——为什么老师和学生,讲台之上和讲台之下,进入者和等待者要在每一天中成为一个整体?
这是德国施塔特阿伦多夫的一所学校,巴赫曼的学生来自巴西、土耳其、保加利亚、哈萨克斯坦等12个不同国家,这些12-14岁的孩子在第二故乡德国其实存在着一些隔阂,他们很多人还没有掌握德语,当然更没有完全融入这个多元的城市。一方面,作为移民的第二代,孩子们和整个城市存在着隔阂,语言之外,是文化,是习俗,是宗教。Ferhan总是戴着头巾,在这个班里,她是最孤独的,也是最容易忧伤的,而在沉默中,她也总是一个人躲在走廊的楼梯上悄悄抹泪——关于清真寺,关于古兰经,似乎她没有对话者;跟随父母从摩洛哥移民到意大利再从意大利到德国的Ayman,总是想念摩洛哥,因为哪儿有他的家人;一个女生说自己和父母从土耳其来到这里,但是还是想念土耳其的家,因为那儿有祖父祖母的墓地。孩子们想家,是因为没有融入这个城市,没有融入这里的文化,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父母为了立足,聚少离多,也很少顾及他们的感受,有的孩子父母已经离婚,有的父亲在外地工作常年不回家,所以在学校里,在教室里,孩子们容易变得孤僻,又可能引发偏激——一个教室就是微型的社会,甚至是施塔特阿伦多夫这个城市微缩的历史。
所以,巴赫曼必须承担起将他们融合在一起而成为“巴赫曼先生和他的学生”这一整体,虽然有校外街道、学校外出活动、参观施塔特阿伦多夫博物馆以及作为世界上最大独立铸铁厂商的弗里茨·温特铸铁厂的镜头,但是在217分钟的纪录片里,场景一直封闭在小小的教室里。在这个微缩型的社会里,每个孩子都是一部活生生的现实之书,他们都有自己的故事,都有自己的烦恼,当然也都有自己的追求和理想,当他们统一在教室里,统一在巴赫曼先生的课堂上,其实融合就开始了:教室虽然是封闭的,是单一的,但是教室里的摆设呈现出一种多元化倾向,座位并不固定,教室里除了课桌椅,还有一些器材;巴赫曼似乎总是坐在讲台那边,但是他几乎不站立起来“俯视”孩子们,而且他的课既有德语课,也有音乐课、数学课,庞杂的授课内容也呈现出某种多元性:当大家说起土耳其,说起家乡时,他问他们“家乡”在土耳其语中如何表达,但是很多人不知道怎么说,“你感觉土耳其是家乡,但是你不知道土耳其语的‘家乡’怎么说。家乡是很有趣的概念......我在德国出生长大,现在已经在德国生活35年了,我还是不觉得德国是家乡。去土耳其,我也没有回家的感觉。我属于哪里?是德国,还是土耳其?”
| 导演: 玛利亚·施佩特 |
家乡是一个固化的概念,这种固化似乎带来某种偏狭的观念,所以在课堂上,巴赫曼会让孩子们用不同的语言说“我爱你”。而且他还经常在音乐中融入更多元素,让大家更容易接受,“吉他是什么颜色的?”“沮丧是什么意思?”“桌子为什么不开心?”那个桌子和吉他的故事,完全是拟人化的故事,于是孩子们跟着唱起来,脸上显出微笑。巴赫曼让孩子们作画,制作手抄报,然后让他们上台用德语讲述自己编写的故事,故事讲完,他又让底下的孩子们点评故事,让德语基础好的同学指出某些错误——当然,如果有孩子捣乱,他也会让他们走出教室以作惩罚;在一些和社会有关的话题中,巴赫曼起到了一个引导者的作用,孩子们讨论男女之间以及婚姻相关的事,巴赫曼问男生什么是理想女性,男孩说不存在“好看又好相处的女性”,他认为女人是麻烦,会要求丈夫做各种事情,但是他的这个观点遭到了Stefi的不满,她反而认为男人才是麻烦,“在家只知道享受,把一切责任都丢给妻子。”学生们说出了自己的理由,而巴赫曼在认真听完之后,也告诉他们:“理想和现实总有落差,我们设想的理想伴侣,不可能出现在现实生活里。”而在学期结束前,巴赫曼唱了一首关于两个男孩的歌,他问他们如何看待这种同性之爱,Stefi认为这种感情很恶心,自己肯定不会这样的;戴着眼镜的女学生并不认为“恶心”,但是说自己没想过恋爱和结婚,她想到的是自己以后的工作——巴赫曼只是听学生们的观点,他不发表自己的想法,也正是这种“沉默”,可以让孩子们更好表达自我。
但是不管是向左的观点,还是爆发的矛盾和冲突,甚至在外出活动时两个男生打架,巴赫曼都是积极引导他们,在他看来,这些都是属于孩子们的特性,所谓的学习,并不是要成为一个完人,而是成为真正的自己。所以在学期结束时,学生开始走向不同的人生道路,巴赫曼告诉他们:“这些分数它只是暂时的,它并不是真正的你们。你们与它截然不同,分数根本无法代表你们,它只是某一瞬间的影像,记录了像数学英语这些微不足道的东西,更加重要的是,你们都是很棒的孩子和年轻人。”对他们的鼓励,是学生们告别走向新的征程的一种自我认识,更是将自己的理念融入到他们未来的生活中,无疑,这便是对封闭教室的某种突破,对隔阂现实的某种改变。

《巴赫曼先生和他的学生》电影海报
巴赫曼作为“学生们”之外的一种存在,起到了人生引导者的作用,实际上,“巴赫曼先生”在这个“和”自组成的统一体中,也是其中的一份子,他是将自己代入到他们之中,甚至“巴赫曼先生”也是从历史走向现实的一个征象。对于施塔特阿伦多夫来说,历史已经变成了那座博物馆,这座移民城市原名阿伦多夫,在1933年纳粹接管之后这里建成了两座大型炸药工厂,二战爆发之后,纳粹又把被占领国工人强迫输送到这里进行劳动,并为之建设了集中营。历史似乎已经走远,它成为了博物馆的档案和物件,但是当学生参观这座博物馆,当集中营的建筑成为废墟继续存在,历史并没有被湮没,它以另一种方式被唤醒,所以,施佩特阿伦多夫的历史就是一段移民的历史,当现实带着历史的遗留,它需要的是正视,需要的是融合,而巴赫曼无疑承担起这样历史使命的人物。
但是巴赫曼的历史使命并不是宏大意义的,他甚至也是个体意义上的突围,在和孩子们的交往过程中,属于巴赫曼自身的历史慢慢浮现出来:他的名字本来带有浓厚的波兰特色,但是在二战中德国让他们改名,于是被强行改名,“巴赫”的意思是“小溪”,“巴赫曼”就是“小溪人”的意思——改名的历史对于巴赫曼来说意味着暴力;在带领学生们参观石雕的时候,和另一个老师聊天,巴赫曼说起了自己选择当老师的原因,曾经他辍过学,曾经他做过歌手和雕塑家,甚至他曾经最讨厌教学,但是最后成为一名老师,巴赫曼说:“总要有人赚钱养家,所以我就是那个去工作的人。”妻子没有固定收入,孩子又需要生存,所以当老师对于巴赫曼来说就是维持生计的工作,就像那些学生的家长,在长期做工中也只是为了生存;学生们无意中问起他像他们那时的生活是否幸福,巴赫曼告诉他们,那时的父亲生活不如意,经常酗酒,母亲也染上了醉酒的恶习,那天两个人都喝醉了,而自己则去踢球了——巴赫曼似乎故意省略了“那天”的最后结局,他对孩子们说的是:“现在你们也知道了我的故事……”
巴赫曼的故事,巴赫曼的历史,巴赫曼的经历,似乎作为缺省的内容存在着,就像施塔特阿多尔夫的历史,在孩子们有限揭开的那一角,其实并不意味着带来伤痛,带来反思,带来阴影,相反,在“巴赫曼先生和他的学生”组成的世界里,一切都需要化解,都需要融入,都需要超越,因为历史不是一个循环,现实也不是建筑在历史之上永远的集中营,现实是“桌子不开心”有吉他在唱歌,是有人生病了但“捣蛋鬼提尔”会让他开心,它永远面向向外的世界,“让我们坦诚一点,把自己的想法讲出来。”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38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