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3-20《书信》:我的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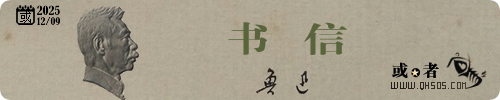
我也常常想到自杀,也常想杀人,然而都不实行,我大约不是一个勇士。
——致李秉中
被人憎恶,也憎恶自己,想到自杀,也想到杀人,有着对爱人更深的爱,也有着对仇人更深的恨,这是一个自我认识的鲁迅,这是一个在信纸上告诉别人的鲁迅,当鲁迅以这样的方式看见另一个鲁迅,他是不是用通信的方式重新认识了自我?同一个,另一个,这是1924年9月24日写给李秉中的一封信,当鲁迅在信中毫无保留地向对方敞开心扉,又以披肝沥胆的方式深刻剖析自己,这是鲁迅借着信件进行自我倾诉,还是对于青年提出了自己可能的人生观?
这一年,鲁迅在教育部任职,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学校任教和从事学术著述,七八月间还应邀去西北大学讲学,他是作为一个老师在给李秉中写信——当时的李秉中就是一个生活贫困的青年学生,曾多次求助于鲁迅,鲁迅也给予了帮助,而在这封信里,鲁迅以一个慈爱又坦诚的师长形象给李秉中回信,他循循善诱,他孜孜不倦,他身体力行,他告诉李秉中,“我诚然总算帮过几回忙”却又要被帮助者“可以毫不放在心里”;他说,“然而这些话并非要拒绝你来访问我”,“可以只管来”;他认为,“我所怕见的是谈不来的生客,熟识的不在内”,原因是不愿 “装出陪客的态度”……所以鲁迅在给李秉中的信里而已谈到了自己的态度,对于那些“谈不来的生客”他怕见,对于那些“愿我有钱,有名,有势,或则愿我陨灭、死亡”的人们则表示憎恶与蔑视——即如李秉中,他后来到国民党军队里当了官,与鲁迅走的是不同的道路,当他提出可在南京设法取消对鲁迅的通缉令时,理所当然地为鲁迅所拒绝。
但是,在这封信里,鲁迅更多的却在说着另一个鲁迅的苦闷。这一年,鲁迅经历了革命斗争的挫折,这一年,鲁迅在探求着新的斗争之路,尤其是两年前当《新青年》解体之后,他的内心就充满着复杂的矛盾,新文化营垒的内部分化,家庭的变故,都让他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和痛苦,一方面,鲁迅讽刺了那些论敌,他以“报答盛意”,“有以骗之”的方式和他们针锋相对,“我很憎恶我自己,因为有若干人,或则愿我有钱,有名,有势,或则愿我陨灭,死亡,而我偏偏无钱无名无势,又不灭不亡,对于各方面,都无以报答盛意,年纪已经如此,恐将遂以如此终。”但是另一方面,“常常想到自杀,也常想杀人”的想法就构成了一种矛盾,杀人是想杀掉那些“愿我灭亡的人”,而自杀则是对于自己内心黑暗的某种排斥,“我自己总觉得我的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我极憎恶他,想除去他,而不能。”即使是在战斗,也让自己看不见真正的光明,“我虽然竭力遮蔽着,总还恐怕传染给别人,我之所以对于和我往来较多的人有时不免觉到悲哀者以此。”
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毒气针对敌人,鬼气却黑暗了自己,所以这封写给李秉中的信就是鲁迅对于另一个鲁迅的深刻自省,但是一封信,一封只寄给他人的信,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单向度的交流:李秉中在写给鲁迅的信里说出了自己何种苦闷?探讨了何种问题?如何使得鲁迅能用这样冷静而深沉的方式袒露自己?这些问题或者不会有答案,一方面鲁迅的习惯,“对于平常的信,是随复随毁”,而由于处在白色恐怖之中,为免“累及别人”,他在1932年的“近三年”中“大烧毁了两次”朋友给他的信,李秉中写给鲁迅的信可能已经付之一炬,另一方面,鲁迅在写信时而已并非想要把自己的原告保存下来以示今后的读者,仿佛是“阅后即焚”式的书信往来,鲁迅只在特定的时间里表达着自己的愤怒和无奈,看见同一个和另一个鲁迅。
从1904年10月8日寄给曾参加创办浙江兴业银行并经营广昌隆绸缎号的蒋抑卮,到1936年10月18日逝世前一天落款为“草草顿首L拜”寄给致内山完造,这两封信构成了鲁迅32年的人生书简,而其实这是收录在其中的第一封信和最后一封信,《书信》就是在鲁迅逝世后收集整理的,书信数量也在整理中不断被发现:一九三七年第一次出版影印本的《鲁迅书简》时收录的书信共六十九封,一九四六年鲁迅全集出版社印行铅印本《鲁迅书简》收录的书信为八五五封和三则断片,一九五八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鲁迅全集》共收录书信三三四封,到一九七六年出版《鲁迅书信集》则收录了一三八一封书信,附录十八则;十八卷《鲁迅全集》则收录一三三三封书信,另有致外国人士一一二封,附录十二件——除鲁迅自编文集及《集外集拾遗》的书信外,迄今为止发现的鲁迅书信已全部收入。
一四五七封书信和附件构成了鲁迅一生被保留下来的“书简”,从这些书简中可以梳理鲁迅和朋友、家人和相关人员的通信情况,大致绘制出他的心路历程。书信是寄信人和收信人之间的交流工具,它是沿着一条单行线在两个方向间建立联系,所以在书信里可以交流可以告知,也可以倾诉,甚至可以成为一种发泄。在鲁迅的书简中,很大一部分便是鲁迅对于中国现实的看法,和他的杂文一样,他在信件中表达对当时中国社会、文坛、国民的一些批评,编号“041008”的信是1904年10月8日写给同去日本留学也一起回国的许寿裳的,他在信中说:“树人到仙台后,离中国主人翁颇遥,所恨尚有怪事奇闻由新闻纸以触我目。曼思故国,来日方长,载悲黑奴前车如是,弥益感喟。”和许寿裳保持着常年的通信习惯,收录的信件有38封,鲁迅就在书信往来中表达着对中国现实的看法:1910年11月15日的信中,他说:“中国今日冀以学术干世,难也。”同年12月21日的信中,他回忆了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教学中因发对学校监督“木瓜”夏震武而一起罢教、辞职的经历,“木瓜之役,倏忽匝岁,别亦良久,甚以为怀。”半个月后写给他的信中又感慨:“吾乡书肆,几于绝无古书,中国文章,其将殒落。”所以询问在北京的许寿裳,琉璃厂是不是有很多古籍;1917年俞复、陆费逵等人在上海设盛德坛扶乩,组织“灵学会”,次年一月又创办《灵学杂志》,宣传迷信,反对科学,针对此,鲁迅认为“沪上一班昏虫”又在捣鬼,于是给许寿裳的信中说:“人事不修,群趋鬼道,所谓国将亡听命于神者哉!”而在《新青年》开始刊载自己的拙作时鲁迅发现并没有多少人爱读这些文章时,1918年5月29日致许寿裳的信中说:“该杂志销路闻大不佳,而今之青年皆比我辈更为顽固,真是无法。”
他在1918年7月5日致钱玄同的信中表达对当时刘师培等计划复刊《国粹学报》和《国粹汇编》的讽刺:“然既将刊之、则听其刊之、且看其刊之、看其如何国法、如何粹法、如何发昏、如何放屁、如何做梦、如何探龙、亦一大快事也。”他在1920年5月4日致宋崇义的信中表达了对新思想不彻底的愤怒:“近来所谓新思潮者,在外国已是普遍之理,一入中国,便大吓人;提倡者思想不彻底,言行不一致,故每每发生流弊,而新思潮之本身,固不任其咎也。”1927年在致章廷谦的信中则对浙江“不能容纳人才”的一贯做法不满,“我常叹新官僚不比旧官僚好,旧者如破落户,新者如暴发户,倘若我们去当听差,一定是破落户子弟容易侍候,若遇暴发户子弟,则贱相未脱而遽大摆其架子,其蠢臭何可向迩哉。”
对中国现实的不满,就如鲁迅的另一篇杂文,体现了鲁迅一贯的批判和战斗精神,而在自我经历中,鲁迅对文坛的丑恶现象也进行了批评。1921年他在写给宫竹心的信中提醒他想要在文学上立足是“世上最苦的职业”,而上海和北京的杂志“没有批评眼,只讲名声”;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之后,鲁迅给宫竹心的信中就说:“鲁迅就是姓鲁名迅,不算甚奇。唐俟大约也是假名,和鲁迅相仿。”他在写给胡适不多的信中谈论了《水浒后传》的问题,“我之不赞成《水浒后传》,大约在于托古事而改变之,以浇自己块垒这一点,至于文章,固然也实有佳处,先生序上,已给与较大的估价了。”谈到了《海上花列传》的成就,“自从《海上繁华梦》出而《海上花》遂名声顿落,其实《繁华梦》之度量技术,去《海上花》远甚。”给钱玄同的信中认为《醒世姻缘》“就其大意而言之,则无非以报应因果之谈”,但是,“写社会家庭之事,描写则颇仔细矣,讥讽则亦或锋利矣,较之《平山冷燕》之流,盖诚乎其杰出者也,然而不佞未尝终卷也,然而殆由不佞粗心之故也哉,而非此书之罪也夫!”
这些对于作品的谈论或者是在学术研究的意义上,但是随着和论敌展开对战,鲁迅也在信中谈论那些和自己有关的文坛之事,他在1921年8月29日给周作人的信中说“我近来大看不起沫若田汉之流”,1926年12月8致韦素园的信中批判了高长虹,“至于长虹,则我看了他近出的《狂飙》,才深知道他很卑劣,不但挑拨,而且于我的话也都改头换面,不像一个男子所为。”他在写给章廷谦的信中痛斥“第四阶级文学家”:“第四阶级文学家对于我,大家拚命攻击。但我一点不痛,以其打不着致命伤也。以中国之大,而没有一个好手段者,可悲也夫。”他在1929年4月20致李霁野的信中大骂上海的所谓“革命文学”:“上海的出版界糟极了,许多人大嚷革命文学,而无一好作,大家仍大印吊膀子小说骗钱,这样下去,文艺只有堕落,所以绍介些别国的好著作,实是最要紧的事。”1930年9月20在致曹靖华的信中又对所谓的无产文学家提出了批评:“新的文人,都是一转眼间,忽而化为无产文学家的人,现又消沈下去,我看此辈于新文学大有害处,只有提出这一个名目来,使大家注意了之功,是不可没的。而别一方面,则乌烟瘴气的团体乘势而起,有的是意太利式,有的是法兰西派,但仍然毫无创作,他们的惟一的长处,是在暗示有力者,说某某的作品是收受卢布所致。”犀利如鲁迅,“我先前总以为文学者是用手和脑的,现在才知道有一些人,是用鼻子的了。”之后在给曹靖华的信中,他又指出了上海的文人多是狗,“一批一批的匿了名向普罗文学进攻。”
对不同文学流派的批判,实际上折射的是鲁迅对自我定位的调整,从北京到厦门,从厦门到广州,从广州到上海,鲁迅在几年时间里不停辗转,他发现中国文坛和学术界总是充斥着败坏的思想,他在1927年1月8日离开厦门大学后给韦素园的信中说:“总之这是一个不死不活的学校,大部分是许多坏人,在骗取陈嘉庚之钱而分之,学课如何,全所不顾。且盛行妾妇之道,‘学者’屈膝于银子面前之丑态,真是好看,然而难受。”4天之后写给翟永坤的信中再次对学校的学风提出了批评,“学校是一个秘密世界,外面谁也不明白内情。据我所觉得的,中枢是‘钱’,绕着这东西的是争夺,骗取,斗宠,献媚,叩头。没有希望的。近来因我的辞职,学生们发生了一个改良运动,但必无望,因为这样的运动,三年前已经失败过一次了。这学校是不能改良,也不能改坏。”而到了广州中山大学,似乎一切都没有改变,同年2月25致章廷谦的信中,他说:“中大定于三月二日开学,里面的情形,非常曲折,真是一言难尽,不说也罢。”仅仅两个月,给李霁野的信中就表达了要离开中大的想法:“我在此的教务,功课,已经够多的了,那可以再加上防暗箭,淘闲气。所以我决计于二三日内辞去一切职务,离开中大。”所以辗转而来,不管是厦门还是广州,环境并没有得到任何改变,由此鲁迅认为中国没有产生学者的土壤,“但是我们中国的所谓学者,大半是开倒车。”
而在对不同文学流派的批判中,鲁迅和文人之间的论战也从未停歇,1933年5月1日给施蛰存的信中说自己想要投稿,“此复,即请著安。”但是不久之后就和施蛰存发生了关于《庄子》《文学》的论战,半年后给姚克的信中,他说:“此君盖出自商家,偶见古书,遂视为奇宝,正如暴发户之偏喜摆士人架子一样,试看他的文章,何尝有一些‘《庄子》与《文选》’气。”鲁迅一直和徐懋庸通信探讨文章翻译问题,1933年韩侍桁和徐懋庸关于“现实的认识”和“艺术的表现”的辩论发生之后,鲁迅还给徐懋庸写信,信中他说:“中国的书,乱骂唯物论之类的固然看不得,自己不懂而乱赞的也看不得,所以我以为最好先看一点基本书,庶不致为不负责任的论客所误。”但是在徐懋庸攻击他之后,鲁迅再没有给他回信——而在1934年6月21致徐懋庸的信中谈到了林语堂,抱怨曾经的好友在逐渐“沈沦下去”希望徐懋庸自己的文章“有正当的主见”,似乎在用别的反面例子来提出自己的观点,但是这种通信中的交心方式似乎也并不恒久,甚至成为了一种讽刺——通信于此时此景的心态,于此时此刻的友人,谁也料想不到今后会发生什么。
林语堂一直是鲁迅的朋友,也是他介绍鲁迅离开北京去了厦门大学,后来两人志趣相同也离开了厦大,但是随着林语堂提出“小品”的主张,两个人的分歧越来越大,1934年6月8日致台静农的信中,鲁迅林语堂提倡的“小品”是一条歧路,“如此下去,恐将与老舍半农,归于一丘,其实,则真所谓‘是亦不可以已乎"者也。’”在给徐懋庸的信中,他认为林语堂眼界太小,“所以他不能在大处落墨,如果受其影响,那就是自己的眼界也给他们收小了。”这种后果便是“于自己,于社会,都无益处”;之后写给郑振铎的信中说,小品化的期刊文章“又唠叨,又无思想,乏味之至”,所以他以曾经的朋友身份认为林语堂在学金圣叹,“似日见陷没,然颇沾沾自喜,病亦难治也”;8月13日鲁迅给曹聚仁的信中说到自己曾经用诚意劝他放弃,并不想林语堂去革命去拼死,“只劝他译些英国文学名作,以他的英文程度,不但译本于今有用,在将来恐怕也有用的。”但是鲁迅说林语堂回信说这些事“等他老了再说”,鲁迅由此灰心,“这时我才悟到我的意见,在语堂看来是暮气,但我至今还自信是良言,要他于中国有益,要他在中国存留,并非要他消灭。”他认为林语堂已经钻在牛角尖里了,“以我的微力,是拉他不出来的。”似乎从此也再也没有试着拉他出来。
“但近半年来,大家都讲鲁迅,无论怎样骂,足见中国倘无鲁迅,就有些不大热闹了。”这是1928年5月30日致章廷谦的信中鲁迅对自己的评价,这既是对当时的一种描述,也是对未来的一种预言,但是在论战中,鲁迅也有意气用事的时候,1925年7月20致钱玄同的信中他讽刺了那个写“孥孥阿文”的人,“确尚无偷文如欧阳公之恶德,而文章亦较为能做做者也。”但是鲁迅所讽刺的不是其文,而是其人,“然而敝座之所以恶之者,因其用一女人之名,以细如蚊虫之字,写信给我,被我察出为阿文手笔,则又有一人扮作该女人之弟来访,以证明实有其。”这个被鲁迅成为“狼狈而为其奸”的人就是沈从文,他曾经在一九二五年七月的《国语周刊》中《乡间的夏》一诗,其中就有“欤耶欤耶脣----孥孥唉”的句子,而在一九二五年四月三十日的时候鲁迅收到了“丁玲信”,他疑心这是沈从文化名的来信,而这种疑心在随后出现有人说是其弟来访时被鲁迅确认是沈从文的恶心做法,但其实,沈从文根本没有化名丁玲,鲁迅一厢情愿的推测使得两人再无交集。
鲁迅的疑心病的确太重,而实际上在不停的论战中,鲁迅已经衍生出另一个鲁迅,一个出现在报章上的鲁迅,一个不停战斗的鲁迅,一个不会低头的鲁迅,一个让中国热闹的鲁迅,而这样的鲁迅作为符号存在,在另一个意义上却抽离了真实鲁迅的存在意义。所以鲁迅会在致李秉中的信中剖析自己,所以鲁迅会现在矛盾的漩涡里,1925年4月11日致赵其文的信里更是表达了自己的痛苦:“所谓‘自己’,就是指各人的‘自己’,不是指我。”1927年2月25日致章廷谦的信中,他更是像放弃“名人”的光环:“我想不做‘名人’了,玩玩。一变‘名人’,‘自己’就没有了。”所以对于鲁迅来说,那个“自己”到底是怎样一个鲁迅?这是一个想做点学问的鲁迅,在厦门的时候,他说:“永是这样的山,这样的海。便是天气,也永是这样暖和;树和花草,也永是这样开着,绿着。”这便是“我竟什么也做不出”的无奈:“一者这学校孤立海滨,和社会隔离,一点刺激也没有;二者我因为编讲义,天天看中国旧书,弄得什么思想都没有了,而且仍然没有整段的时间。”即使到了上海之后,也没得空闲,“倘若这样下去,是不好的,书也不看,文章也不做。”也终于没有成为那一个鲁迅,1933年63日致曹聚仁的信中,鲁迅似乎在哀叹:“我现在真做不出文章来,对于现在该说的话,好像先前都已说过了。近来只是应酬,有些是为了卖钱,想能登,又得为编者设想,所以往往吞吞吐吐。”
这是一个说出“爱与结婚,确亦天下大事”的鲁迅,和许广平在一起,有了孩子海婴,但是鲁迅似乎并没有沉浸在欣喜中,相反却表达了一种隐隐的无奈,“我不信人死而魂存,亦无求于后嗣,虽无子女,素不介怀。后顾无忧,反以为快。今则多此一累,与几只书箱,同觉笨重,每当迁徙之际,大加肇画之劳。但既已生之,必须育之,尚何言哉。”这是1931年3月6日海婴已经一岁半时鲁迅致李秉中的信中表达的想法,孩子成为一累,鲁迅对其也只是尽一个父亲的职责,4月15日写给李秉中的信中表达得更为明确:“生今之世,而多孩子,诚为累坠之事,然生产之费,问题尚轻,大者乃在将来之教育,国无常经,个人更无所措手,我本以绝后顾之忧为目的,而偶失注意,遂有婴儿,念其将来,亦常惆怅,然而事已如此,亦无奈何,长吉诗云:己生须己养,荷担出门去,只得加倍服劳,为孺子牛耳,尚何言哉。”
文章做不出来了,孩子成为新的负担,这其实是一个真实鲁迅的还原,再加上还要负担亲族生活,“负担亲族生活,实为大苦,我一生亦大半困于此事,以至头白,前年又生一孩子,责任更无了期矣。”1932年6月5日致台静农的信中仿佛能听到鲁迅的一声叹息,而在更早的1930年,在致章廷谦的信中也说:“老兄,老实说罢,我实在很吃力,笔和舌,没有停时,想休息一下也做不到,恐怕要算是很苦的了。”鲁迅也成了围城之中的人,“凡细小的事情,都可以不必介意。一旦身临其境,倒也没有什么,譬如在围城中,亦未必如在城外之人所推想者之可怕也。”或者正是这个符号化而不能停歇下来的鲁迅,把真实的鲁迅拖进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
1936年的书信中,鲁迅几乎都提到了一个话题:自己的身体:1月8日致沈雁冰的信中提到自己的病,“那一天,面色恐怕真也特别青苍,因为单是神经痛还不妨,只要静坐就好,而我外加了咳嗽,以致颇痛苦,但今天已经咳嗽很少了。”3月11日致杨晋豪的信中说:“病还没有好。我不很生病,但一生病,是不大容易好的;不过这回大约也不至于死。”说“不至于死”或者是鲁迅自己的判断,或者是对朋友的宽慰,但是鲁迅却正奔向那个死亡终点:3月20日写给母亲的信中说到二月底突发气喘,之后注射了针剂,后来卧床三天,“至于气喘之病,一向未有,此是第一次,将来是否不至于复发,现在尚不可知也,大约小心寒暖,则可以无虑耳。”6月3日写给唐弢的信中说:“我病加重,连字也不会写了,但也许就会好起来。”而这封信是鲁迅口授许广平代笔的;6月19日给邵文熔的信也是许广平代笔的,信中感慨“年事已长,筋力日衰,动辄致疾,真是无可奈何耳”;7月给王冶秋的信谈到了等自己好起来要去一次旅行;但是8月中旬鲁迅开始吐血,医生禁止他说话,实际上鲁迅也失去了一些自理能力,1936年9月28日致吴渤的信中,他说:“今年九个月中,我足足大病了六个月,至今还在天天发热,不能随便走动,随便做事。”
10月17日,鲁迅写出了给国内朋友的最后一封信,在这封给曹靖华的信中鲁迅谈到了译作、闸北时局、曹靖华排印的小说集,以及乌烟瘴气的文坛、所谓的“国防文学”,而说到自己的身体时,鲁迅介绍了最近的病情,“我病医疗多日,打针与服药并行,十日前均停止,以观结果,而不料竟又发热,盖有在肺尖之结核一处,尚在活动也。日内当又开手疗治之。”虽然被病魔缠身,但是鲁迅还是在信中选择了宽慰的语气,“此病虽纠缠,但在我之年龄,已不危险,终当有痊可之一日,请勿念为要。”而在18日寄给内山完造的信中,鲁迅还提到了“十点钟的约会”,抱歉说自己去不了了,也希望内山完造“给徐腾先生挂个电话”,请他速来看一下自己的病情——署名“草草顿首L拜”的鲁迅也许知道自己不久于人世,所以他希望医生速来,但是一天之后,鲁迅溘然去世,那个一生都在战斗的鲁迅,那个对敌人“一个也不宽恕”的鲁迅,那个让中国热闹的鲁迅,终于在回归肉体中走完了他的一生。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8047]
思前:如沙少女写下古诗十九首
顾后:《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