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05-20《X射线》:照见与诊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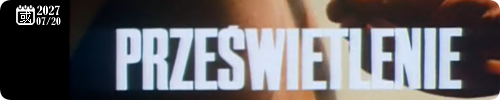
他们是病人,忍受着疾病的折磨,他们在讲述,表达着内心的不安与惶惑,他们接受治疗,渴望变成身体健全的人——基耶斯洛夫斯基再一次将镜头对准弱势群体,再一次借助镜头说话,也再一次反思波兰的社会性问题,与《我曾是个士兵》有着几乎相同的结构和镜头语言,自己不过这次不是表达自己的反战思想,而是深入个体疾病之产生的原因,探讨社会发展中人的命运这一母题。
或许是来源于基耶斯洛夫斯基的父亲在疗养院接受肺病治疗并死于肺结核的现实,基耶斯洛夫斯基采用《X射线》的片名,无疑具有双关意义:一方面,这些在疗养院的病人在接受治疗时,X射线就起到了探究病情的作用,这是一种工具意义;另一方面,基耶斯洛夫斯基也把镜头当成了X射线,在照见可能病兆的情况下,希望开出解决这一病症的方案——在字幕打出之前的“前奏”中,一只手拿着听诊器,然后把它贴在裸身的肉体上,这是医生和病人之间无声的对话,一只手、一个听诊器就是X射线,它需要从病人身上获取信息,从而提出治疗的方案,而基耶斯洛夫斯基的镜头对准这个过程,就是希望在影像中也完成如X射线那样照见和诊疗的作用。
照见的过程就是让那些病人叙说自己的疾病。“那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已经过去三年了,但我还是忘不了……我憎恶我的命运……”另一个病人说:“它让我们残疾,生活抛弃了我们,使我们无法行动,就像去戏院看电影,我们只能看而无法参与……”第三个病人则说:“我是一个群居动物,喜欢与人相处,但是这种疾病让我从一开始就过上了不可能的生活……”每个人都在叙说,叙说他们的痛苦,叙说他们的孤独,叙说他们的封闭,所以肺病并不只是一种身体的疾病,它更在精神上造成了困扰,在这个封闭的世界里,他们成了被遗忘的人,有人说起朋友和亲戚来这里看望自己,但是当他们走了就只剩下自己现在这里,“星期天最难熬……”“我受够了无所事事……”
| 导演: 克日什托夫·基耶斯洛夫斯基 |
这种孤独和封闭的生活,在基耶斯洛夫斯基的镜头里,变得有些可怕:在中景和远景构筑的景别中,护士拿着药分发给他们,他们坐在草坪上的椅子上,站起来却又无处可去。镜头变成了画框,画框变成了障碍,它成为了另一种无形的束缚,即使这些病人让自己有事干,比如有人不停地编织毛毯用来打发时间,比如有人积极配合治疗让自己成为一个健全的人,比如有人回忆过去的生活,让自己回到柴米油盐的生活中,但是那种孤独和无助的感觉依然困扰着他们,在疗养院的隔离中,在镜头制造的障碍里,他们困在残缺的世界里,而这正是对人生命运的一次审问:为什么我们会被社会抛弃?
这也是基耶斯洛夫斯基提出的问题,在X射线照见了病情之后,他也开始用镜头剖析疾病产生的原因。有人在讲述中说到自己曾经是建筑工人,因为得了这个病再也无法工作了,这是病人的某种抱怨,但是无法再继续工作,从另一个意义上讲是不是建筑工作本身就是致病的原因?基耶斯洛夫斯基显然没有直接给出病因,但是他的镜头里无处不体现致病的社会原因:朋友来探望病人,病人再次陷入困境,折射出的是人情的冷漠;护士和医生为他们致病,但是仍然把他们当成病人,在整个过程中基耶斯洛夫斯基没有拍摄到医生和病人的交流,”“在这里会给你提供一切服务,而你失去了每天不得不面对的问题……”这也是一种温情的缺失;最后病人们撑着伞坐上了公交车,似乎是病情好转离开的标志,但是在被他们背影挡住的镜头里,在摇晃的车身行驶中,他们的命运依然是未知的;更重要的是,在汽车缓缓驶出疗养院的时候,远景是浓浓的雾,雾中是模糊的城市,而城市中竖立的是几根大烟囱——这是工业社会的标志,也许正是在没有健康保障的生产一线,他们成为了病人,只有疗养院周边的树林、照耀着的光线和传来的鸟鸣,才是治愈的唯一办法。但是,基耶斯洛夫斯基又显得悲观,当病人离开,再不是清新的空气,而是冒烟的烟囱;再不是清脆的鸟鸣声,而是混杂着的警报声、敲打声和摩擦声——也许这些病人离开之后,还会有另一批病人到来,问题在重复,疾病在重复,命运也在重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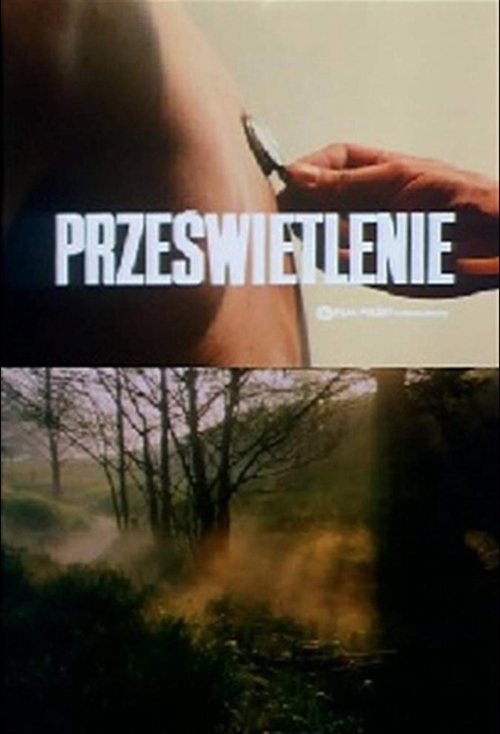
《X射线》电影海报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17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