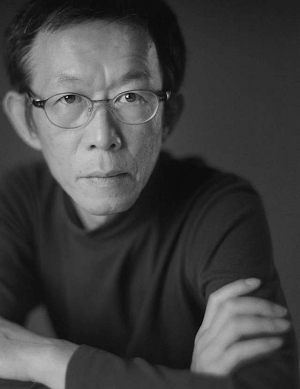2023-05-20《黄灿然的诗》:语言已不能够拯救我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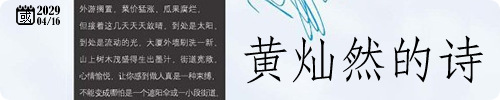
我常常想,如果有来生,
我下一辈子就不做诗人了。
我不是后悔今生做诗人。不,我做定了。
我是带着使命的,必须把它完成。
——《来生》
来生,将不做诗人了,因为来生可以有选择,因为选择可以做不用思考的人,因为不用阅读思考和写作将是幸福的事。黄灿然绘制了“来生”的生存方式,以“来生”的方式选择不做诗人,大约是基于两种表达:来生的对立面是今生,今生就是一个诗人,一个“做定了”诗人的人,而且黄灿然将其看做是一种使命,“必须把它完成”;做定的诗人,必须完成的使命,看上去像是一种无奈,因为这是没有选择的必然,而来生可以有选择,选择便是将自己放在今生的对面:不用文字,不用思考,用实际行动做一个人:或者是一个街头补鞋匠,或者是一个餐厅侍应,或者是一个替人开门提行李的酒店服务员——文字和思考之外是具有实际行动的人,而这对于黄灿然来说才是一种幸福,“我将不用赞美阳光/而好好享受阳光。我将不用歌颂人/而做我所歌颂的人。”
来生的对面是今生,是此世,是当下,实际上黄灿然以“来生”为题,就是在叙说着今生、此世和当下:一切都可以选择的今生,一切都可以用实际行动“心诚喜悦地服务人群”的此世,一切不用歌颂和赞美就能抵达幸福的当下。作为诗人的黄灿然为什么要舍弃做一个诗人的选择?来生不做诗人的感慨中有着怎样的无奈?文字和思考是不是在黄灿然看来有违诗人的真正的使命?黄灿然当然是一个诗人,他在诗集中首先提炼的就是“诗艺”:什么是真正的诗人?他说:“不写次要诗歌的诗人最终沦为次要诗人。”什么是真正的诗歌?他对“真诗”的定义是:“真诗:放弃虚荣的人找到它,追求虚荣的人炫耀它。”什么是诗歌的价值?他阐述说:“标准的价值在于立与破,在立与破之间标准没有价值。”什么是诗人的使命?他定义说:“—个过好日子的诗人谈起自己终于过上的好日子,应当含着比他过寒酸的日子时谈起自己过着的寒酸日子更深的羞愧。”
“诗艺”阐述了诗人和诗歌,而且是有价值的诗歌和写好作品的诗人,这样的“诗艺”在他关于诗歌、诗人的诗作中具体呈现出来。《收获的季节》直接指明了“伟大诗人”的定义,我们的时代有优秀的诗篇,“但没有出现伟大诗人”,在他看来,这种阙如是因为没有伟大的土壤,“并非表面的一派庄严/而是背后的莫大痛楚”,是痛楚而非庄严,是黄灿然对“伟大”的命名,而痛楚的意义就在于当下,就在于在灵魂深处得到“收获”,所以他认为彭斯是伟大的诗人,“我在日落时分读你纯朴的诗篇/纯朴的苏格兰人,我多羡慕你/你在人间种植了青枝绿叶/爱情的河流环绕你的家乡”,作为对比,“我已经丧失了故乡的优秀品格/绝望的肉体再也开不出美丽花朵(《彭斯》)”他纪念诗人荷尔德林,“从前神圣的祖国,神圣的家乡,/如今在你的心灵里暗淡下去,/因为你已经枯竭了,已经被弃置//在一个垃圾桶似的角落,像发霉的果酱”,因为涅卡河里的天空掉转了方向,因为涅卡河里的流水更换了目的;他看见了苦难的茨维塔耶娃像“有毒的玛琳娜”,“她在镜中收割红罂粟/她在蛇窝里蠕动腰肢/她到我梦中探访我并在离去的时候唤醒我/而我在睁开眼睛的那一瞬间失去我有毒的玛琳娜”,她是诗歌的玛琳娜,是疯狂的玛琳娜,是苦难的玛琳娜;甚至他和诗人吕德安在一起看见了消失的家园,“你现在转乘飞机/和地铁,明尼阿波利斯、曼凯托、/纽约(它生动起来)、时代广场,/它们依次在你慌乱的椭圆字形中出现,它们/在传达:那倒后镜里的家园正在消失。”
淳朴的彭斯种植了青枝绿叶,被弃置的荷尔德林“像发霉的果酱”,苦难的茨维塔耶娃在镜中收割红罂粟,和诗人吕德安看见了消失的家园,诗人遭遇的这一切都成为了“背后的莫大痛楚”,所以他们可以成为伟大的人,可以写下伟大的诗。黄灿然书写痛楚式的伟大,更凝结在他不多的长诗之《彼特拉克的叹息》中,以“尘世既没有欢乐,也没有永恒”为题辞,就是在书写着一种痛楚:1348年“闻劳拉死讯”,彼特拉克剩下的就只有绝望,“我青春的火焰已经熄灭,/别了,虚妄!我的泪水不禁渗出一片灼热:/我的痛苦从此得以凝固,前途即是深渊……”一半给了诗歌,另一半给了爱情,对于彼特拉克来说,诗歌和爱情早就合二为一,沿着时间的逆流而上,是1342年“重返阿维尼翁”,“我来到这里,只为了凭借草木和流动的风景/重温一下你沁人心脾的气息。我爱上帝,但/我也瞒着他悄悄爱你。”是1336年“在旺图封顶”,“我的高贵,我的修养,我所读所写的动人诗篇,/一想到你,它们便显得那么幼稚、羞怯和腼腆。”是1327年的“抒情诗之一”,“你的一颦一笑早巳注定我此生要一错再错:/我将无比暗淡,又不能放弃再见你的希望。”爱情被写进了诗歌,成为动人的诗篇,而在劳拉之死之后,彼特拉克这个文艺复兴的发起者,正是把诗歌中的苦难变成了人类向前探索的力量,1968年的彼特拉克发出了叹息,也写下了“抒情诗之二”:“我的破船已经驶入了//回忆的港湾,可是它已经无所谓安不安全:/一个人老了,就懒得去理会腐朽还是不朽。”
诗歌在灵魂的诗篇中,在人文主义的回忆里,在伟大诗人的痛楚中,当黄灿然否认现在没有出现伟大诗人的时候,实际上在感慨现实的无奈,感慨肉体的绝望,而这便是关于“命运”的当下风景,收录于诗集的第一首诗歌是写于1985年的《命运》,诗如其名,黄灿然描绘了关于命运的图景:农民在田野里,工人在厂房里,学生在校园里,“犯人在监狱里”,这是“无需惊奇”的事实,但真正的事实是:思想在头脑里,言论在心里,爱情在小说电影里,“幸福在不幸里”。不管是思想、言论还是爱情,似乎都被隐藏了,“无需惊奇”的现实取代了一切,最终每个人的命运都是“幸福在不幸里”。以1985年对现实的无奈为开端,黄灿然似乎一直在书写着没有痛楚却不幸的命运,这种当下的图景变成了我之存在的现实:在这里似乎看不见希望,“但我的前途一片暗淡/不祥的风雨就要降临/我即将失掉栖身的地方。(《日渐衰落》)”在这里似乎只有沉默,“我单纯的心灵毕竟脆弱/禁不起对自己稍微的怀疑/这使我深感生命的艰难/并使我写的诗日趋紧张。(《长久缄口之后》)”在这里还有自责,“我的灵魂因承受不住肉体的浩劫而叛逃,/我诅咒牙痛连带诅咒我那没有规则的生活。(《这是我个人历史最黑暗的时期》)”
| 编号:S29·2230205·1913 |
终于1987年的那首《倾诉》成为黄灿然对于“来生”观的某种感慨,这是一首写给自己女儿的诗,也是对女儿人生的“倾诉”:孩子是爱情的结晶,但是黄灿然认为是“偶然的种子”,这是一种残酷,也是无可奈何,从这个偶然开始,黄灿然似乎在表达着一种宿命,“如果你将来开出幸福的花朵/你不必感谢/如果你将来遭受了风吹雨打/也不要埋怨”,而不管是偶然还是必然,生命总是开始了,黄灿然在这样的生命面前,发出了“孩子啊,愿你一生平庸”的“期盼”,而且做出了唯一的忠告:“切勿写诗”,由此阐述了诗歌在现实中的遭遇:“坏诗糟蹋艺术,好诗为诗所误/好或坏,一旦染上,就无法自拔”,好诗和坏事,都无法构筑幸福,而这一切当然是黄灿然基于自身命运得出的结论,“你父亲不容于世俗,你母亲不懂得世故/结果他们走投无路,唯有彼此相濡以沫”,所以作为父亲给女儿的第一首诗,便成为了对诗歌的拒绝,便成为了平庸一生的注解。
父亲对女儿的倾诉,诗人对非诗人的忠告,完全是黄灿然“来生”的一次预言,因为身为后代的女儿就是自己“来生”的影子。一方面黄灿然认为这个时代没有产生伟大诗人的土壤,平庸是最好的出路,而另一方面,当黄灿然直击现实的残酷将生命归结为一种宿命的时候,实际上是在取消生命本身存有痛楚的意义,一种反对论的背后让现实又变成了平滑向前的庸世,在诗意渐失的书写中,诗歌反而变成了不再神圣、没有使命的存在,他对于命运的关照,完全变成了一种无奈,一声叹息,一种无所作为的颓然。《一生就是这样在泪水中》把一生看成是在泪水中默默忍吞的一生,是在时光中注满怨恨的一生,是在火光中寻找灰烬的一生,是在痛苦中模拟快乐的一生,是在诺言中迁徙漂泊的一生,“人就是这样,在泪水中结束一生。”《土地是残酷的》中则将一生看成是“永远在挣扎、在希望、再挣扎、再希望”中的残酷写照,“一生为它而活,因它而死,这残酷的土地。”《哀歌之五》还是在喟叹人的一生,做梦是我们的一生,平庸是我们的一生,邪恶是我们的一生,怯弱是我们的一生,耻辱是我们的一生……一生是不幸的一生,一生是残酷的一生,一生是平庸的一生,而且,人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完全落入了宿命论中,没有反抗只有妥协,没有转变只有压抑,没有抒情只有叹息,于是,具体而微,黄灿然在《给妻子》的诗中,记叙了“结婚六年,孩子五岁”的生活,即使妻子还保持单纯对爱情还抱有幻想,即使自己还在继续写诗,但是和人的一生一样,“生活就是这样”,“就是这样”的活着中,只是像活着一样,“那就是你们活着,而我像活着。”
我们的一生“就是这样”,我们的生活“就是这样”,所以在《哀歌之五》中黄灿然所抒发的“词语就是上帝”的创作,是不是也变成了一种虚妄?一种词语是剥削了意义的词语,是背叛了朋友的词语,而另一种词语是拯救我们的词语,“给我们绳索、草和幻觉。”但是在词语本身变成谎言之中,拯救使存在变成了虚无,使生命变成了废墟,于是悲观的黄灿然发出了叹息:“只有语言能够拯救我们。/而语言已不能够拯救我们。”拯救是因为无法拯救,拯救只是让自己变得毫无价值,拯救只是在毫无价值中“超越我们的死亡。”无法拯救的拯救,毫无价值的价值,词语已经沦陷,诗歌已经沦陷,诗人当然早就沦陷,于是在黄灿然的诗歌里只剩下对现实的喟叹,对命运的嘲讽,对当下的投降,平庸的一生也成为了平庸的诗歌。
收录了1998年至2005年诗歌的集子《灵魂集》,以“灵魂”为集名,却像一生“就是这样”那般,灵魂也在毫无意义中“就是那样”。“装着山川、风物、丧乱和爱,/让他一个人活出一个时代”的伟大诗人杜甫已不再,只有生命已到尽头的“老人”:“读书、工作、恋爱、结婚,/退休、丧偶、孤独、散步,/没有做过别人没有做过的事情,/没有浪费别人没有浪费的生命。(《老人》)”只有“她从未碰触过幸福”的外祖母,只有“每天两次,像巡逻”的邻居陆阿比,只有在演讲比赛中喊出了“我们——应该——追求/——自由,关心——苦难”的同学白诚。黄灿然还以小说的叙事写下了关于新闻翻译官朱伯添的两首诗,一首是《翻译》,朱伯添翻译北约空袭科索沃和塞尔维亚的新闻,其中科索沃的城镇的译名他参考了很多资料,最后他认为上司可能会将那些冷僻的地名删掉,“或更干脆一点,筒略为科索沃/——科索沃谁都知道。”另一首诗是《朱伯添辞职》,做了十年新闻翻译官的朱伯添为什么要辞职?就像那些地名被删除一样,人生的理想也会被删除,灵魂的追求也会被删除,“他们都像我在此之前一样,/为了为自己而活而为别人而活,/结果是白活;他们来到这儿,/带来头,带来脸,但不敢把灵魂/也带来,或假装忘了带来”,于是工作是沉闷的,生活更沉闷,而且“他们管它叫无奈”——正是面对这沉闷而无奈的生活,朱伯添选择了辞职。
|
| 黄灿然:我下一辈子就不做诗人了 |
朱伯添辞职,是对理想和灵魂的放弃,是因为生活“就是这样”,朱伯添辞职和黄灿然来生不做诗人的出发点是一样的,在被现实困厄的生活中,这其实是一个时代的通病,“我打赌你是一个一流诗人,/只不过活在一个二流时代。(《致一位英语诗人》)”这样一种自喻式的表达实际上是奔波到香港的黄灿然对整个时代的叹息:五年来每天从铜锣湾坐巴士到中环上班,下班后又从中环坐中巴回到铜锣湾,“两天换一套衣服,/一星期换三对皮鞋,/两个月理一次头发,/五年来表情没怎么变,/体态也没怎么变,/年龄从二十八增至三十三”,在“生活就是这样”的现实中,也发现了变化,比如一些“工程在进行中”的告示,一些“大减价”的横幅,一些“要求”和“抗议”的政党标语,以及“一些肇事者和受害人已不在现场的交通事故”,感觉自己曾经爱过很过,会比那些平平庸庸的人幸运,但是一切都没有变化,“你那些幸运的经历他全都经历过,/而他经历过的,正等待你去重复。(《你没错,但你错了》)”
你错了,是因为你以为的东西错了,是因为这个时代错了——1998年至2005年正是那个叫世纪末的时代到来又慢慢远去,“这城市把它的衰落/安排在世纪末”,于是城市已经生病,于是城市拒绝反省,这个时代就是这样,“只要你主观,你就不会乐观,/只要你客观,你就肯定悲观,/在这个时代,这个时代。(《给这个时代的打油诗》)”而在诗歌里,这个时代是“诗人之于文人,/就像文人之于文盲”的时代,是“先锋诗人都去做落后商人”的时代,是由“下半身、下半篇、下半首、下半句”写就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里,还有谁是诗人?还有谁会写诗歌?还有什么可能的伟大?还如何寻找灵魂?
2006-2008的《奇迹集》中,黄灿然的“平庸”之风更显强劲,他完全将诗歌变成了日常的关注,在慢慢消失的诗意中,“就是这样”的一生在说话,“就是这样”的生活在记录,“既然是这样,那就是这样”的无奈在表达。那年冬天朋友凌越结婚,他这里站站那里看看有点寂寞,“他想过来跟我们说话,/但进入不了状态,/过一会儿就没趣地走开。(《婚礼》)”那次黄灿然看见“一个委身屈膝的顺从者”,这是整个人类的形象,而那些诗人、艺术家、英雄和不屈不挠的人,“是他头上的短发/在风中挺立。”那个时代黄灿然呼吁:现在让我们去爱一个老人,或者,现在让我们去爱街上任何一样东西,因为,“我们的心灵一刻也没有停止过感受的这些物质更内在的秩序。”2009-2014的《发现集》,在“就是这样”的人生和生活中,黄灿然并没有发现什么,反而诗句越来越像大白话,比如《走上正确的路之后才有的喜悦》,比如“真理/必以不被相信为代价!”比如“只有清澈见底的人/才开始懂得混混沌沌之妙”;他开始为小狗写下《美好的事物》和《失去你之后》两首挽诗;他的拒绝变得决然,“对所知保持一种无知,对消逝的保持歌唱。”
2014至2016的《洞背集》是黄灿然生活在香港洞背时写下的诗歌,和《奇迹集》《发现集》一样,黄灿然依然游荡在“就是这样”的人生和生活中,“而一个人/很容易就在收收拾拾/洗洗擦擦中过完一生。(《一生》)”这样的一生甚至比“就是这样”还无奈,于是在这一集诗歌中,黄灿然不仅取消了生命的神圣化,将其变成了一种物化,它们是“迅速向高空飘啊、飞啊、舞啊,/瞬息间消失”的蝴蝶,是“为什么就没想到不去干扰它,/让它留在屋子里,和平共处?”的蟑螂,是“温顺而安全地/睡在他身边”的宠物蛾,是鸡鸭中的耶利米,是“黄狗/把一只手搭到黑狗的肩上”的狗兄弟,是“真的飞起来了,而且/一飞冲天”的臭屁虫……对动物抒发感情,是对“人生”的调侃,那只壁虎被诗人救起,诗人却为它想好了给壁虎家人讲述的“英雄史诗”——动物的遭遇变成英雄史诗,英雄早就变成了动物。在将人生动物化的同时,黄灿然更是表达对生命的无助,2016年1月至2月,黄灿然的母亲在军澳医院住院,他记录了在医院里的所见所闻:一个女人来探望邻床的婆婆,两个人开始祈祷耶稣为自己救人治病,他们同声说的是:“阿门。”邻床又新来一个老婆婆,她一变呻吟一边自言自语:“咁辛苦,不如死着好过啰。”还有两个婆婆坐在病床上的谈话,“前一个声音安详,昨天我曾听见她/在安慰她左边发牢骚的病友。/后一个声音同样平静,我刚才/还跟她互道过早安,并惊奇于她/一脸红润,一脸慈祥,/是任何老人或任何老人的子孙/都最愿意看到的。”
在医院里所见,在医院里所闻,耶稣在他们的祈祷中,死亡在他们的对话中,生命在走向最后一步时,只剩下了无奈、无助和无力,而黄灿然身为诗人在那一刻也变成了旁观者,最后在生命的叹息中他仿佛也看到了无奈、无助和无力,“我的诗神,如果我的诗能传世,/请允许我预支这首诗的/未来读者们的全部能量和同情心,/为我母亲祈祷:愿她今天/手术顺利成功,迅速恢复健康,/回家过正常日子。”这是标注着“2016.2.22”的诗作,诗集的最后一首,也是唯一具体到年月日的一首,详细地记录,强烈地渴望,黄灿然为母亲祈祷,用诗歌的力量为母亲祈祷,在生与死之间为母亲祈祷,“回家过正常日子”也许就是回到“就是这样”的生活和人生,当下是日常,是重复,是行动,当然,也是平庸。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6696]
顾后:对犀牛和狗心的过度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