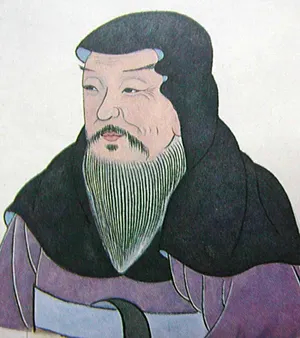2022-12-09《说文解字》:引而申之,以究万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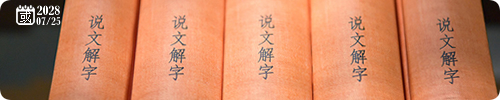
公 平分也。从八,八犹背也。韩非曰:“背厶为公。”古红切。
食堂吃早餐,咀嚼中抬头,瞥见桌上贴着宣传纸片,上面写着:“使用公筷公勺”。平时一点也没有注意到,今天却被这一句话吸引住了,也不是被整句话吸引,使用公筷公勺的倡议早已有之,疫情期间加大了宣传力度,但是被吸引住的关键点在于其中一个字的设计:“公”,上面是一个“八”,下面则是一个“厶”,下面的“厶”字用了红色,所以看起来格外显眼,而格外显现似乎正好进入到了和“公”有关的“说文解字”中。
“公”的解释是“平分”,如何平分?“公”字属于“八”部,“八,别也。象分别相背之形。”这是一个象形字,它所具有的是划分、区别的意思,像一分为二、相别相背的形状,在八部之下有“公”字,有“分极也”的“必”字。那么下面的“厶”字又作何解释?“厶”为“奸衺也”,这是一个“指事”字,按照韩非的解释:“仓颉作字,自营为厶”。既然“自营为厶”,那么和“厶”相背则为“公”,“背厶为公”的相逆即“八厶为公”——一个被标红的“厶”在这张宣传纸片中便是一种警示,而警示的终点就是“公”,徐锴在《说文解字系传》中更明确地做了解释:“厶音私,不公也。”
| 编号:W27·2221112·1897 |
小小的餐桌,小小的纸片,小小的“公”字,就这样具有了日常生活“说文解字”的意义。《说文解字》作为许慎倾注毕生精力而完成的著作,其突出的便是“文”和“字”,在被称为汉字学纲领的《说文解字》序中,许慎系统阐释了汉字的产生和发展:先是古者庖牺氏王天下后“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之后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之后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蹏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然后是“百工以乂,万品以察,盖取诸夬”,“夬,扬于王庭”……这段关于汉字发展史中,“文”和“字”就已经有了区分,许慎之后则说明了两者之间的关系:“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著于竹帛谓之书。书者,如也。”这一段话可以看做是关于汉字起源的经典叙述,仓颉造字,根据事物的形象画出它们的图形,也便有了“文”,所以文是“物象之本”,后来又根据形声字声旁相互结合而出现了“字”,这是一个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字”就是由文孳生出来而逐渐增多的:文是源,字是流,文是物象之本,字是一种扩展,文是象形,字是形声。在“文”和“字”之上便有了“书”:书就是将文字连贯起来写在竹帛上,就是“如”——如描写对象之情状。
对“文”“字”和“书”产生的说明,就引出了造字的“六书”:
一曰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三曰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会意。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撝,武、信是也。五曰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
上和下的“指事”是从认字识字的过程说的,日和月的象形是从画物显象的角度说的,会意字则是从组合部件汇合意义的角度而言,形声字则从形符、声符与形声字的关系的角度说的,转注则是一类特殊的形声字,假借是把意义寄托在音同或音近字的角度说的,所以从整体上来说,作为造字的方法,六书的阐述基本层次是清楚的,许慎对六书做了界说,在逐字解说中将六书的原则贯彻始终,牢固地建立了汉字结构的理论体系。而在功用的表达上,他认为:“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在他看来,文字是经艺的基础,是政治的基础,文字需要传承,所以“本立而道生”,所以“知天下之至啧而不可乱也”,许慎编写这本《说文解字》的意义也就在这里。
|
| 许慎:知天下之至啧而不可乱也 |
在编写的具体体例上,许慎也是开创者,《说文解字》共十四篇五百四十部,九千三百五十三文,重文一千一百六十三,解说凡十三万三千四百四十一字。如何将近一万个汉字进行分类?许慎以形为标准分成五百四十部,建立部首制,就是一种独创,“其建首也,立一为耑。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同[条牵]属,共理相贯。杂而不越,据形系联。引而申之,以究万原。毕终于亥,知化穷冥。”部首制就是以“方以类聚,物以群分”的方式,将同一枝条的孽叶牵连在一起,共一义理的文字连贯在一起,又根据字形进行排序,而顺序以“一”为开端,以“亥”终结,这种“始一终亥”的编排来源于汉阴阳五行家“万物生于一,毕终于亥”的说法,从而直观了解汉字的变化,穷尽构型的精深。许慎便是按照这样的分类注解法,同时配以篆文,古、籀字,达到“博采通人,至于小大,信而有证”的目的,“稽撰其说,将以理群类,解谬误,晓学者,达神恉。分别部居,不相杂厕。万物咸睹,靡不兼载。厥谊不昭,爰明以谕。”
《说文解字》的意义就是在“万物咸睹”中“爰明以谕”,“恐巧说邪辞使学者疑,慎博问通人,考之于逵,作《说文解字》。”许慎的儿子就是这样评价父亲的。当然许慎《说文解字》的最重要意义就是创造了汉字释义的典范。比如全书解说的第一个字便是“一”:“惟初太始,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万物。凡一之属皆从一。”一是世界的原初状态,是天地成万物的起点,在这里,“凡一之属皆从一”便是“说文解字”的体例,它说明了部首制、部首和部属,“一”就是部首,其他则是部属;“弌,古文—。於悉切”,这里的“古文”是指春秋战国的东方文字,并非是指“弌”比“一”字产生的时代更古,而是说“弌”是指古文“一”的别字,其他还有“籀文”,它是春秋战国时的西方文字;“於悉切”是指反切注音法,是徐铉采用孙愐《唐韵》的音;在“天”字的注解中,有“颠也。至高无上。从一、大。”在这里,“从……是”是分析会意字的专门术语,对于这样的注解,王筠在《说文系传校录》“祏下”注曰:“按会意字相连成文者,则一言‘从’,如天‘从一、大,是也。两字对峙为义者则两言‘从’,如吏‘从一,从史’,不可言‘从一、史’也。”会意字是“从……是”的格式,而当“两字对峙为义”则为“从……从……”的格式;“丕:大也。从一,不声。”这里的格式则是“从……,……声”,这是分析形声字的专门术语,丕字以一为形旁,以不为声旁;“吏:治人者也。从一,从史,史亦声。”这里的格式则是“从……,从……,……亦声”,这是会意兼形声字的专门术语,“吏”从一,是说其执法如一,从史,史借作人字用,表示执法的官员,而它也有“史”的发音;在相同部首的部属注解完之后,有“文”和“重”的说法,“文”即指“文”和“字”,比如“一”部为“文五”,即“一、元、天、丕、吏”五个文字。”“重一”则是指一个重文,凡文字音、义全同,而形体不同的,而又附出于《说文》说解之后的,许氏称为重文,如“一”部的“弌”即“一”的重文;除此之外,还有“或体”,它是指某个字在同一字体中的不同写法,相当于异体字,还有“多文词”,这是仪式文词多的缘故,如“祠:春祭曰祠。品物少,多文词也。”许慎用词字申说祠字受义之原因。
许慎通过释义、析形、譬音、征引的方式进行说文解字,但是对于“说文解字”来说,重要的意义或者就是“引而申之,以究万原”,也就是探寻文字之源流,寻找汉字之本原,在文字经过时代的演变之后,对本原之探究可以更好理解文字最初产生的背景和意义。比如“示”,“天垂象,见吉凶,所以示人也。”这个意义是如何从“示”的本原引出的?“从二;三垂,日、月、星也。”这便是真正的“解字”,由此,示就是“神事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
摘录部分对本原进行“说文解字”的文字:
三 “天、地、人之道也。从三数。凡三之属皆从三。”“三”是数名,但是这个数名是一种指事,它是指“天、地、人之道”,许慎在这里阐述的思想来源于董仲舒的说法,这一观点在“王”字得到了更进一步的体现,“王:天下所归往也。”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说,“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参通之者王也。”这是从“三”演绎而来,三代表着天地人三道,而“王”则是对天地人三道的“参通”,按照孔子的说法,“一贯三为王。”而吴其昌在《金文名象疏证兵器篇》中则认为,“王字之本义斧也。”“王”字象无柄斧钺,其头刃部朝下放置,这倒变成了一个象形字,用以象征权力。在“王部”中有“閏”:“告朔之礼,天子居宗庙,閏月居門中。从王在門中。”有“皇”:“大也。从自[王]。自,始也。始(皇)[王]者、,三皇,大君也。自读若鼻,今俗以始生子为鼻子。”
玉 玉为“石之美”,玉有五德,“润泽以温,仁之方也;鰓理自外,可以知中,义之方也;其声舒扬,尃以远闻,智之方也;不桡而折,勇之方也:锐廉而[忮,絜之方也。”在“玉”部中有“球”字,球,本意就是“玉声”,是玉石撞击之声;有“理”字,“治玉也。”由治玉而治理;有“玩”字,“弄也。”玩最初就是捧玉玩弄的意思。
每 说文解字上说:“艸盛上出也。”“每”字是“屮部”,它的意思是草木茂盛的样子;屮部还有“苦”字,“大苦,苓也。从艸,古声。”苦字原意不是味道,而是一种叫“大苦”的草,也即蘦草;还有“茜”字,“ 茅蒐也。从艸,西声。”茜就是茅蒐草;还有“蔣”字,现在大多用于姓氏,而说文解字上说,“苽蔣也。从艸,將声。”蒋是一种植物,即茭笋;“若”字,“从艸、右;右,手也。”若指的是择菜,这是会意,另外“若”也指杜若,一种香草“蒸”字,“析麻中干也。从艸,烝声。”蒸就是析去麻皮的中干;还有“葬”字,“藏也。从死在茻中。一其中,所以荐之。”《易》上说:“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就是由“死”和“茻”构成,中间还有一横,表示用来垫着尸体的草席,所以埋葬也和草有关。
特 属于“牛部”,“朴特,牛父也。从牛,寺声。”“特”的本意就是指没有阉割的牛,就是牛父;“物”也在牛部,“万物也。牛为大物;天地之数,起于牵牛:故从牛,勿声。”物就是指大物之牛。
名 “自命也。”拆开来看,“名”字从口,从夕,“夕者,冥也。冥不相见,故以口自名。”也就是说,名的意思是自己称呼自己的名字,由口、由夕会意,夕就是夜晚的意思,当夜晚彼此看不见,所以只有自己说出自己的名字。张舜徽在《说文解字约注》中并不认同这种说法,在他看来,则是一种古代的礼制,他从《礼记·内则》云:“夜行以烛,无烛则止。”这一句得出结论:“盖所以间内外者为至密,故禁冥行。冥行则必自呼其名,使人知之,所以厚别远嫌也。”
唐 说文解字曰:“大言也。”“唐”的本意就是“大言”,《庄子·天下》上说:“荒唐之言。”就是大言。
正 “是也。从止,一以止。凡正之属皆从正。”“正”字的意思是正直无偏斜,从止,而上面的“一”是古文上字,表示在上位的人,用“一”放在“止”上,会合上位者止于正道之意。它的对立面是“乏”,《春秋传》曰:“反正为乏。”
彳 是“小步也,是一个象形字,“象人胫三属相连也。”“德”字从彳,“ 升也。”《说文解字义证》:“古升、登、陟、得、德五字义皆同。”还有“彼”字,是“往、有所加也。”从彳,就是有所增益的意思。“很”字不是现在的副词,它是“不听从也”,另外也是“行难也。”从彳也和步子有关,不管是是“不听从”还是“行走艰难“,或者“违逆乖戾”,都是“很”的本意。
爲 在“爪部”的“爲 ”,竟然它的本意是“母猴”,“其为禽好爪。爪,母猴象也。下腹为母猴形。”
几 鸟之短羽飞几几也。象形。凡几之属皆从几。
自 鼻也。象鼻形。凡自之属皆从自。
美 甘也。从羊,从大。羊在六畜,主给膳也。美与善同意。
初 始也。从刀,从衣。裁衣之始也。
某 酸果也。从木,从甘。(徐灏《说文解字注笺》:“‘某’即今酸果‘梅’字。因假借为‘谁某’,而为借义所专,遂假‘梅’字为之。古文‘槑’或省作‘呆’,皆从木,象形。”某,酸果。由木、由甘会意。缺其会意之由。)
校 木囚也。从木,交声。
月 阙也。大阴之精。象形。
秒 禾芒也。从禾,少声。
科 程也。从禾,从斗。斗者,量也。
程 品也。十发为程,十程为分,十分为寸。从禾,呈声。
卒 隶人给事者衣为卒。卒,衣有题识者。
演 长流也。一曰,水名。从水,寅声。
洞 疾流也。从水,同声。
派 别水也。从水,从辰,辰亦声。
戲(戏)三军之偏也。一日,兵也。从戈,盧声。(王筠《说文解字句读》:“凡非元帅则曰偏。”兵: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谓兵械之名也。”王筠《说文解字句读》:“未闻。”)
或 邦也。从口,从戈,以守一。一,地也。域,或又从土。(或:徐灏《说文解字注笺》:“邦谓之國(国),封疆之界谓之域。古但以或字为之。其后加口为國,加土为域,而别为二字二义。”邦:段玉裁《说文解字注》:“邑部曰:‘邦者國,也。’盖或、國在周时为古今字。”)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53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