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12-09《康拉德与自传的虚构》:“双重人”的命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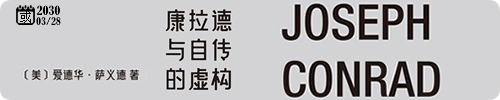
康拉德致克利什切夫斯基的信是出于他对混沌所带来的威胁的烦忧感;认识到这一事实后,批评家即可“立定跳远”,一跃进入小说。
——《个体性的诉求》
克利什切夫斯基是一位波兰钟表匠,当时身为水手的康拉德认识了他,克利什切夫斯基欢迎他前往英国海岸,这不是水手和钟表匠的相遇,这是波兰人和波兰人的相识,在写给克利什切夫斯基的信中,康拉德表达了对他和他的妻子的感激之情,一种基于身份认同的感激之情,“时光老人,一向勤于工作,已让人把许多人、事和回忆抛诸脑后:然而,我不相信他会从我的头脑和心灵中抹去关于您和您家人的回忆,那是出于遥远的民族同胞联系而对一个陌生人表达的好意。”基于波兰同胞而具有的民族归宿感让康拉德的这种感激之情变得强烈,而一份信所传递的充沛情感也不再基于纯粹个体性的邂逅。
这是康拉德现存最早的一封信,这封信具有的样本意义在古斯塔夫·莫夫的《约翰·康拉德的波兰遗产》中成为了批评家“立定跳远”而观察到的主题,那就是“从精神到肉身均被驱逐出波兰”这一事实导致处境的不确定性。但是同为被驱逐出自己祖国的爱德华·萨义德似乎在康拉德的“个体性诉求”中看到了另一种“斗争的形式”,那就是自身存在之中拯救出意义和价值变成了“真正的冒险”:一方面康拉德在书信中展示了自己的个体性经历,将现在和过去连接的过程中他锻造了自我意识,“康拉德的书信呈现了对其心智、气质和性格缓慢展开的发现过程,——简而言之,这一发现即康拉德本人书写的康拉德之精神史。”康拉德在个体性施展中表现了其痛苦和极度努力都是在书写自己的精神史;另一方面,爱德华·萨义德认为,康拉德在书信中表现的存在机制是在生活过程中的自我写照,但是这种写照却成为了“长剧的一部分”,“里面布景、表演和演员的安排都是康拉德在追求品格平衡的斗争过程中的自我意识。”也就是说,康拉德将自己精神史的书写纳入到人类的长剧中,并以表演的方式展示给更多的观众。
一方面和另一方面,精神史和表演的长剧,这或者就是爱德华·萨伊德本书标题所展示的两部分:“康拉德”指向的是不断探索自己个体性诉求的自我意识,而“自传的虚构”则指向了那部安排了自我意识的表演长剧,它们被“与”联结起来,对于爱德华·萨伊德来说,康拉德的标本意义就在于:“他的生活就是他本人与外部世界之间伙伴关系的例证。”但是为什么这样一种连接却是“真正的冒险”?在萨义德看来,康拉德的个人经历沉淀了他的经验,这种经验也是人类经验的反映,而康拉德从这些经验中提取拯救的意义,无疑“根植于人类的渴望之中”,也就是说,个体成为时代和社会的一种写照,精神史的来源也是外部世界的一部分,而更为重要的是,康拉德将自身的感觉不断暴露在“对于不属于其自身之物的感觉之中”,甚至对立于充满动态、流动不居的生命过程中,只有在这种暴露和对立之中,康拉德才能创造出一个拯救的意义:要么允许向混乱屈服,要么向自我中心的秩序投降,这样的主导模式必然带给康拉德对于自传的“虚构”,对于长剧的安排,对于命运的斗争,从而构成了一种“真正的冒险”。
在《序言》中,萨伊德直接指出了康拉德生活中的这个奇特现象:“这就是一种公共人格的创造,用以掩饰他与自身及工作之间更为深层、更成问题的困难。”他的书信就构成了这种奇特现象的文本,一方面它们作为康拉德个人史的时候,思想和精神的高潮与他自我发现欲望的实现相吻合,另一方面也与欧洲历史上的那个重要阶段的高潮相符合——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一历史现实,“他的观念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影响到他的精神和艺术活动,直至他1924年去世。”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出现之前,康拉德的书信就已经提供了个人史和欧洲史的双重书写经验,萨伊德将康拉德1896年至1912年的书信在两个维度上进行了考察,一个是“性格、角色和编织机”,另一个则是“虚构小说的主张”,而这两个维度多对应的就是个人史和人类经验,在康拉德身上所反映的则是水手和作家不同身份构筑的“双重人”的命运。
1896年的时候,康拉德已经出版了两部小说,《阿尔迈耶的愚蠢》和《海隅逐客》,但是这期间的康拉德还是在寻找着自我的定位,他在1898年2月的信中说到:“我属于那帮可怜人。我们都是。我们奉神的名而生,世世代代牢牢抓住继承下来的恐惧和残暴,不假思索,毫不犹疑,毫无顾忌。”1月份写给满怀理想主义的朋友罗伯特·坎宁安·格雷厄姆时说:“自我主义是好的,利他主义是好的,而忠于自然将是其中最好的……”同时认为人类之所以悲惨,就在于他们意识到了是自然的受害者;“困难太多了”成为这一时期他处在海员和小说家之间摇摆的一种痛苦写照。在萨义德看来,这时期的康拉德积极地参与到自己的心智实验室中,不断探索毕生事业的智识和精神设计,而要重建智识,就需要摆脱那种意识,但是对于康拉德来说,这个过程是痛苦的,基于个体的挣脱实际上反而抓住了“他们继承而来的恐惧和残暴”,而所谓的编织机作为“想象出来的背景”,又把康拉德拉回到最初的状态,他在绝望中回归,又坚定着为自己的忧郁寻找认同,1906年11月写给加内特的信中,他依然写道:“人类事物的凄美之处在于别样的选择……”
| 编号:H22·2231004·2008 |
编织机是对自我性格的一种挣脱,但是编织机的魔掌还在控制着康拉德,所以康拉德选择了对自己水手角色的遗忘,他开始探索小说家“不可思议”的奇幻世界,像奥德修斯一般,根据自己个体性深刻的内在需求,“冒险去雕刻自己的命运”。所以一方面将水手的角色忘得一干二净才能成为一名小说家,而另一方面探寻和雕刻自己的命运又必然是水手应该做的事情,萨伊德将此归结为康拉德的“双重人”的命运,而这正是康拉德的冒险:当遗忘角色成为一种故意的行为,当写作成为一种合理化的需求,“有—个危险是,使虚构小说具有说服力的努力,可能会使作品沦为既带有奴性又缺乏想象力的文档。”而虚构也成为康拉德在书信中一种属于作家身份的行动,他给高尔斯华绥、桑德森夫妇、加内特和格雷厄姆等最亲密的朋友写信,明确指出了自己遭受到的“自我情绪的伤害”,在敞开自己的同时,也人为制造而呈现给公众一个从容自若的形象,包括写作的《大海如镜》而和《个人札记》,在萨义德看来,都是关于“真正非个人化的亲密关系”,是康拉德利用了自己所谓的“异域性”摆出的一种姿态,这是一种对真理的寻找,是一种生成,但是,这种不断变化的人生观导致了一种精神错乱和疑病症的感觉,“所有这一切共同促成了战前那些年煞费苦心的逃避和妥协策略。”
而当大战前夕以及爆发,逗留在波兰的康拉德更是以一种“通过仪式”完成了公共人格和经验的塑造。在个人精神史上,康拉德的心智处在持续的危机状态中,这种危机让他时时从宿命般的噩梦中惊醒,在写给克里斯托弗·桑德曼的信中说,这是一个“我们”应该宣告的伟大讯息,“我们,老欧洲人,在现实与幻想方面拥有漫长而痛苦的经验”;所以他抓住这场战争的炼狱性质,将他转变为世界不得不接受一场形而上的通过仪式,在《拯救》中他选择了“生命的索取与死亡的代价”为最后一张的标题,他曾经写给林加德的一段话是:“他被一种紧绷的存在感所诱惑,这种感觉远远超过了单纯的生命意识,充满了无尽的矛盾,欢乐、恐惧、狂喜和绝望,既不能面对,也无法逃避。那里面没有和平。但谁想要和平呢?”在他看来,现代水手只有接受了训练,才能将感受变成写作,才能对未来充满自信,才能让未来变得自主。当战争结束,康拉德写给小说家林·沃波尔的信中说:“伟大的牺牲已经完成,——它对地球上的国家会产生什么影响,未来会显现出来。”《漫游者》便是对他对旧秩序逝去为主题的小说,1918年给高尔斯华绥夫妇的信中,他认为和平和幸福之类的词语有一种“打包的手提箱”的气息,非常适合“北极冰冷的寂静”——直到1924年康拉德生命终结,他的个人精力都投入到了慷慨激昂的欧洲主义之中,即使艺术并没有找到最终的目标,但是这一失败在萨义德看来,是他为新欧洲所作出的牺牲,“尽管如此,的确曾有过一次拯救。”
书信构筑了康拉德“冒险”的一部分,萨伊德的真正疑问在于:“我很难相信一个人会做如此不划算的事,会在一封接一封的信中倾诉心声,然后在他的小说中却并不使用和重新表述他的见解与发现。”书信在其属性来说,是写信人和寄信人之间点对点的交流,是个体意义上的是私密性写作,甚至还称不上真正的写作,但是康拉德显然将这种私密性变成了表达公共性的平台,显然他并没有从无序的经验中拯救出意义,未能从生活的困境中拯救出自身,但是他的冒险,他的通行仪式,他的欧洲主义,他的牺牲,都构筑了一种斗争形式,而小说则通过对书信的理解更成为他编排的长剧重要的一部分,萨伊德认为康拉德书信中的主题是一种自觉的坚持,“坚持作家的作品与其根本上的个体性之间的重要联系”。那么对康拉德小说创作的考察,他的创作是不是也构成了“虚构的自传”?
康拉德在书信中说到了作家创作的一些观点,比如他认为“男人往往先行动后思考”,无疑排挤掉了理性的启示作用,比如他写信给高尔斯华绥认为作家的人物不在于“发明深度”,“发明深度也不是艺术,大多数事物和大多数天性都只有一个表面”,对表面的忠诚看起来更像是康拉德的一种逃避。萨伊德认为,康拉德的大部分短篇小说都戏剧化地表现了过去和现在、当时和现在之间“成问题”的关系,背后是康拉德对过去的感觉与他对现在的感觉出现了冲突,所以他在小说中试图在过去和现在之间建立关系,萨伊德认为,这种努力最后反而变得刻意。一种手法便是让时间停滞,从而带入审视、回忆、重温或解决,这种时间的停滞性在康拉德小说中变成了“等待”:《进步前哨》中的凯亦兹和卡利尔被挪移出正常的欧洲生活,开始在东方的丛林深处等待生意;水仙号漂洋过海,它的使命是清楚自身造成拖延的原因,黑人韦特的名字就是等待的“Wait”;《回归》中的阿尔万·赫维在伦敦过着停滞不前的生活;《青春》和《黑暗的心》中,也都有一个长时间停顿,在那段时间里,一群隐隐心绪不宁的前水手们听着马洛那陷入沉思般不着边际的话。
等待而迟延,等待而停滞,康拉德的这种充满技术主义的处理就是要建立过去和现在的因果关系,就是让现在接受来自过去的治疗,当韦特在“等待”而成为一个垂死之人,当惠利船长早就是一个失业者,康拉德并没有在现在找到过去的原因,反而让现在变得茫然,萨伊德说:“但如今我们看到,现在令人抓狂地被隔离在未来的解决方案之外,使我们所熟悉的可耻的过去起死回生。”似乎康拉德还有着更大的野心,他想在这个自称体系的过去之中发现一个可定义的结构,从而带入到现在之中,这就是萨义德所说的通行仪式,它表现为《大海如镜》中的“入行仪式”:当那艘丹麦双桅船沉没,康拉德的船前去救援,船长命令康拉德指挥此次行动,以浩瀚的大海为背景,这便成为了“入行仪式”——被破坏的情况下举行的救援,是对于过去的一次真正告别,获救的船长最后朝康拉德微笑。
康拉德也在寻找属于自己的入行仪式,当他揭露出命运的过去和现在,他也完成了双重人的定义,“他可以把自己描绘成一个水手和一个作家、一个行动者和一个反思者,以及一个明确定义的双重人,因为他现在能够相信所有这些角色。这是一个对个人和公众都有利的经济体。”个人精神史在这种仪式中转变为一种转向公众、面对公众并由公众书写的历史:康拉德在小说中将个体的生存理念放置在了黑暗之中,并通过抵抗找到了“个人真理观”,这种个人真理观就是“人类存在的一个必要但绝望的事实”,作为波兰人,在俄国手中遭受了痛苦,抵抗俄国淹没他的波兰身份就是康拉德主导性力量,而这种力量在小说中成为了人类对抗黑暗的力量,“从《大海如镜》中充满希望的形象开始,到《小说六篇》中灾难性的形象,现在他把注意力转向了拥有明确开端的形象。”水手的康拉德启航,而登陆再起航则变成了小说家的康拉德,同时,小说家的康拉德启航,再登陆、再起航又变成了水手的康拉德,“你会发现它是康拉德自身精神体验的重演,它充满活力,经过锤炼,然后用来之不易的洞察力重新把握和呈现。”
而这就是萨义德所认为康拉德的成就:“他将自身存在中的种种混乱,重组为一种高度模式化的艺术,准确反应并控制其所处理的现实。”康拉德的最后一部小说《阴影线》就是这种自我戏剧化创作的尝试,它让“整个世界都充满了它的深度和广度”,萨伊德认为,他的经历是英国文学中独一无二的,他的文学创作是奇特而富有创造力的。但是,对于康拉德来说,书信和小说构建的双重人命运依然是一种创作,甚至依然是一种冒险,因为在这两个维度之外,康拉德无可避免地陷入到现实的困境中,他凭借着“虚构的自传”已经无法使他找到救赎的力量。康拉德投入到新欧洲的秩序重建,在欧洲主义中摇旗呐喊,这种仿佛是入行仪式的举动却无法让康拉德真正脱离过去,甚至他对现实毫不妥协的态度让他成为敌人,他的私人斗争的公开化身不再是一部小说,直到1924年逝世,康拉德所书写的依然是一曲哀歌,他让书中的人物得到最后的救赎,他在小说创作中收获名声,但是他从来没有得到安全感,他的人生和命运是一部小说,但永远不是虚构的,“这是一个典型的康拉德式讽刺,他终究无法把自己所有的痛苦转化为赢得的和平。”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54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