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01-25《资治通鉴(七)》:怒其室而作色于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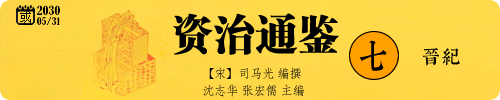
《资治通鉴》第七册记载了《晋纪二十五》至《晋纪四十》的历史事件,即起于公元371年辛未,尽于公元419年己未。
【倚傍先代】
公元372年,即太和六年,司马昱即位为东晋皇帝,司马昱历经元、明、成、康、穆、哀、废帝七朝,先后封琅琊王、会稽王,累官抚军将军,在晋穆帝的时候,升任抚军大将军、录尚书六条事,与何充共同辅政,何充逝世后,司马昱总揽朝政,废帝即位后,再次徙封琅玡王,又进位丞相、录尚书事。作为一个七朝元老,见证了太多的内政外交,但是东晋国祚已终在司马昱身上得到了轮回式的体现,他成为皇帝被桓温所挟,在位期间实同傀儡,始终害怕被废黜的他最后忧愤而崩。
“男子不能流芳百世,亦当遗臭万年!”这句话就出自东晋大司马桓温之后,他自恃自己有雄才伟略,“阴蓄不臣之志”。咸安元年即371年,桓温子广陵将还姑孰,屯于白石,他直接讽褚太后要废帝立司马昱,“并作令草呈之。”十一月十五日,在桓温一手策划下,他召集百官于朝堂开始废帝,但是废立皇帝的事历代都无先例,百官都震惊恐惧,当时的桓温也有点紧张,尚书左仆射王彪之知道事情不能半途而废,他为桓温出谋划策,“公阿衡皇家,当倚傍先代。”这个先代的成规就是汉代霍光,于是取法《汉书·霍光传》的记载,“礼度仪制,定于须臾。”于是一切变得顺理成章,宣布太后的诏令后,司马奕被废黜为东海王,而当时的丞相、录尚书事、会稽王司马昱继承皇位。
对于桓温的这一举动,当时的前秦王苻坚也看不下去了,他对群臣说:“温前败灞上,后败枋头,不能思愆自贬以谢百姓,方更废君以自说,六十之叟,举动如此,将何以自容于四海乎!”连续在灞上和枋头战败,不反思自己的过错反而问罪百姓,现在又废黜皇帝自我解脱,完全是“怒其室而作色于父”的做法。的确,桓温看上去是把司马昱立上了帝位,但是七朝元对于桓温也是没有任何办法,“温威振内外,帝虽处尊位,拱默而已,常惧废黜。”在惊恐了八个月之后,司马昱就驾崩了,而在他驾崩的时候还改诏说:“家国事一禀大司马,如诸葛武侯、王丞相故事。”就是让家事国事都交付于大司马桓温。
但是桓温的野心并不在于,他最大的希望就是在司马昱临终前将帝位禅让给他,所以当听说只是让自己像诸葛亮、王导一样的角色,自然颇为不满,他给弟弟桓冲写信,就说到:“遗诏使吾依武侯、王公故事耳。”他怀疑这事是王坦之、谢安所为,于是对他们怀恨在心,当朝廷诏令谢安前去征召桓温入朝辅政,桓温又推辞了。
【骤胜而骄】
对桓温废立皇帝的做法颇有微词的苻坚,开创了前秦的最大版图,但是在治理中也犯下了致命错误。《晋纪二十六》,司马光就发表了看法,赏罚分明是体现公正和法治的基础,如果有功不赏、有罪不杀,是不是能实现大治?回答是否定的,他以苻坚为例,“秦王坚每得反者辄宥之,使其臣狃于为逆,行险徼幸,虽力屈被擒,犹不忧死,乱何自而息哉!”苻坚每次擒获了反叛作乱的人,不是惩罚他们而是宽宥他们,这种“宽容主义”使得叛逆不再是一种罪,臣下也对此习以为常,因为他们知道险恶的勾当不用担心被杀,而这正是苻坚养虎成患所在,引用《书》则是:“威克厥爱,允济;爱克厥威,允罔功。”如果国家以威胜爱,必定成功,否则以爱胜威,必定失败。而《诗经》中则指出:“毋纵诡随,以谨罔极;式遏寇虐,无俾作慝。”苻坚无疑反其道而行之,失败甚至灭亡都已经被注定。
公元383年的淝水之战在前秦和东晋军队中展开,前秦战败,无疑是灭亡的关键,淝水之战之后,《资治通鉴》记载了前秦灭亡的经过。太元十年,后秦王姚苌向苻坚要求给他传国印玺,“苌次应历数,可以为惠。”姚苌将后秦取代前秦看做是一种天命,但是苻坚怒目而斥,“小羌敢逼天子,五胡次序,无汝羌名。玺已送晋,不可得也!”他把后秦称为小羌,即使五胡的次序也没有羌族的名字,姚苌又派右司马尹纬劝说苻坚,让他把君主之位禅让给他,苻坚再一次拒绝,“禅代,圣贤之事,姚苌叛贼,何得为之!”他将姚苌视为叛贼,并且认为平时对姚苌有恩,更加愤恨他,并且对丈夫人说:“岂可令羌奴辱吾儿。”苻坚甚至杀掉了自己的孩子苻宝、苻锦,自己也只求一死。辛丑日,姚苌便派人将苻坚吊死在新平佛寺,张夫人、中山公苻诜全都自杀。
前秦灭亡,对于苻坚的这一结局,很多人认为是苻坚纵容了慕容垂、姚苌的缘故,最后导致恩将仇报、养虎为患,但是司马光却不同意这样简单的说法,他认为,苻坚的悲剧就在于“由骤胜而骄故”,也就是迅速取胜招致的骄傲,为什么取胜会招致最后最后的失败,司马光引用魏文侯曹操和李克之间的一段对话来阐述这个道理,当时曹操问李克吴国失败的原因,李克回答说:“数战数胜。”曹操不解,数战数胜不是国家的福分、君王的幸运吗?李克回答说:“数战则民疲,数胜则主骄,以骄主御疲民,未有不亡者也。”曹操之所以被许劭称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就在于在不同的环境中,面对不同的形势可以灵活转变,而苻坚违背治国之道,既“爱克厥威”又“骤胜而骄”,所以灭亡就是一种必然。
【淝水之战】
再回过头来看看淝水之战,谢安指挥的东晋军队能以少胜多取得淝水之战的胜利,在某一方面来说,也正是苻坚的轻敌思想。太元八年即383年,苻坚想要消灭东晋,率领60万军队前来攻打,而东晋谢安的军队只有8万人,实力相差悬殊,在这场战役中,到底发生了怎样的形势转变?前秦的军队紧逼淝水布阵,东晋的军队却无法渡过,谢玄派使者对阳平公苻融说:“君悬军深入,而置陈逼水,此乃持久之计,非欲速战者也。若移陈少却,使晋兵得渡,以决胜负,不亦善乎!”谢玄的意思是让晋军渡河一决胜负,当时的前秦战士认为我众敌寡,表面上让他们渡河,实际上可以在他们渡河后遏制他们使他们无法上岸,然后一举歼灭。苻坚也认为有理,于是下令让士兵们稍稍后撤,等到晋军渡河到一半,然后以铁骑蹙而杀之。
但是当前秦的军队一向后撤退,无法控制的场面便出现了,谢玄、谢琰、桓伊等率领军队渡过淝水攻击他们。当时的苻融率领退逃的士兵反击,却人仰马翻被晋军所杀,兵败如山倒,谢玄等乘胜追击,一直追到青冈,前秦的军队大败,自相践踏而死的人,遮蔽山野堵塞山川。悲惨的情况是:“其走者闻风声鹤唳,皆以为晋兵且至,昼夜不敢息,草行露宿,重以饥冻,死者什七八。”如同四面楚歌一般,吹响了前秦灭亡的号角。为什么前秦占有人数和地势的优势还会一败涂地?原因在于:“初,秦兵少却,朱序在陈后呼曰:‘秦兵败矣!’众遂大奔。”朱序喊出的那句“秦军失败了”让前秦士兵乱了分寸,而朱序也乘机与张天锡、徐元喜来投奔东晋,并缴获了前秦王苻坚所乘坐的装饰着云母的车乘,又攻取了寿阳,抓获了前秦的淮南太守郭褒。
【因魇暴崩】
淝水之战前秦战败,东晋朝野振奋,司马曜也被全国人民寄予了中兴东晋的希望。但是,孝武帝对国事根本不关心,他崇尚黄老,什么也不愿意做,在谢安取得巨大成功后,反而遭到猜忌,不久谢安就病逝了,反观孝武帝确乐得自在,更加不理朝政,荒淫享乐,最终因为一句酒后醉言,死在了后宫嫔妃的手中,上演了历史上的一出笑话。
《晋纪三十》中记载了太元十九年九月发生的这个悲喜剧,孝武帝非常喜欢喝酒,内殿里总是流连迷醉。那天孝武帝和后宫的嫔妃们一起宴饮,张贵人也在旁边,这时孝武帝调笑将近30岁的张贵人说:“汝以年亦当废矣,吾意更属少者。”孝武帝或许只是在酒多了之后讲了一句笑话,但是张贵人暗中愤怒,到了晚上,孝武帝已经大醉,在他来清暑殿就寝的时候,张贵人拿起酒赏赐了所有的宦官,将他们打发走,然后让贴身的丫头用被子蒙住孝武帝的脸,最后弑杀了他,杀了孝武帝之后,张贵人声称“因魇暴崩”,当时的太子司马德宗愚昧懦弱,会稽王司马道子也昏庸荒淫,便都不追究查问。一代君王就这样在醉酒中、在笑话中魂归西天,“辛酉,太子即皇帝位,大赦。”而即位的安皇帝也无法掌控局面,“安帝幼而不慧,口不能言,至于寒暑饥饱亦不能辨,饮食寝兴皆非己出。”
【御坐忽陷】
桓温想要司马昱禅位给自己,姚苌想要苻坚将君主之位禅让给他,而桓温的儿子桓玄也受到家族基因的影响,想要安皇帝将帝位禅让给自己——想要从禅让中得到帝位的人越多,就说明政治越昏暗。“自隆安以来,中外之人厌于祸乱。”隆安是东晋的一个转折时代,天灾人祸、动乱战争接连不断。桓玄刚来京师的时候,就罢黜奸佞的小人,选拔贤明的才俊,健康的百姓似乎看到了希望,但是不久之后,“玄奢豪纵逸,政令无常,朋党互起,陵侮朝廷,裁损乘舆供奉之具,帝几不免饥寒,由是众心失望。”三吴地区发生大饥荒,住户人口减少了一半,而会稽郡的人“减什三四”,永嘉、临海两地的人人口“殆尽”,一个极端的例子是:“富室皆衣罗纨,怀金玉,闭门相守饿死。”
作为大司马桓温的儿子,桓玄先后消灭了殷仲堪和杨佺期,除掉执政司马道子父子,把持朝政大权,历任侍中、都督中外诸军事、丞相、录尚书事、扬州牧,进位相国、大将军,晋封楚王。元兴二年即403年,冬十月,楚王桓玄呈上奏表,请求自己回到封底,又让安帝亲手写诏书挽留他;他还唆使手下的人造谣说,钱塘临平湖的湖水又突然盈满,江州也降下了甘露,就让文武百官聚集到一起来庆贺,以此作为自己接受皇帝禅让的吉祥预兆;又因为前几代改朝换代的时候,都有隐士不出来做官,而觉得自己接受帝位的时候独独没有是一种耻辱,所以便通过访查,找到西晋的隐士安定人皇甫谧的第六代孙子皇甫希之,供给他生活的一切费用,让他隐居到深山老林里去,又反过来以朝廷的名义,征召他出山做著作郎,并让皇甫希之坚决推辞,不去任职,然后再下达诏书,表彰、称赞他,称他做高士;桓玄又打算废除钱币,而用粮食谷物、绸缎布匹等作为交换、流通的工具,以及恢复使用肉刑等……
一切都是桓玄想要获得帝位,所以不断颁布各种法令规章又没有实行,使得乱上加乱。后来安帝下诏,让楚王桓玄行天子礼乐,散骑常侍卞范之拟写了禅让的诏书,让临川王司马宝逼迫安帝亲笔抄写。庚辰日,安帝驾临宝殿,派遣兼太保、领司徒的王谧手捧皇帝的玉玺印绶呈献给桓玄,正式向他禅位。壬午,安帝被搬出了皇城,改居永安宫,文武百官则劝说桓玄尽快登基称帝,十二月庚寅朔,桓玄在九井山的北侧修筑祭坛,壬辰,桓玄正式登基——后来桓玄进入建康宫,当他登上皇帝御座的时候,御座突然塌陷,群臣大惊失色,而殷仲文却说:“将由圣德深厚,地不能载。”听到这句话,桓玄大悦。
【坚凝之难】
桓玄称帝,起来征讨他的就是之后建立宋朝的刘裕。刘裕出场在《晋纪三十三》,文字记载了他的贫苦出生,“初,彭城刘裕,生而母死,父翘侨居京口,家贫,将弃之。同郡刘怀敬之母,裕之从母也,生怀敬未期,走往救之,断怀敬乳而乳之。及长,勇健有大志。仅识文字,以卖履为业,好樗蒲,为乡间所贱。”后来加入刘牢之的军队,在击败孙恩的战斗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之后讨伐桓玄。
在《晋纪三十七》中记载了刘裕大开杀戒的一幕,刘裕忿恨广固久攻不下,打算把所有军民全部活埋,然后把他们的妻子女儿,赏给自己的将士。这时韩范劝阻说:“晋朝帝室迁移到南方去之后,中原地区混乱不堪,士人百姓无依无靠,对待强有力的政权,自然便依附过去了。既然做了人家的臣民,就一定要为人家尽力拼命。他们都是古老的世族,先帝遗留下来的子民。今天,王家的军队前来讨伐异族拯救他们,却要把他们全部活埋,那么您打算让百姓往哪里去呢?我私下里担心西北的百姓从此不会再有盼望我们去拯救他们的愿望了。”刘裕马上肃然起敬,向他道歉,但是还是杀了王公以下的三千多人,籍没的家庭人口也有一万多,拆毁了广固城墙。把慕容超押回建康,斩首。
对此司马光发表评论,他认为,南渡以后,“威灵不竞,戎狄横骛,虎噬中原。”刘裕以王师翦平东夏,但是,“不于此际旌礼贤俊,慰抚疲民,宣恺悌之风,涤残秽之政,使群士向风,遗黎企踵,而更恣行屠戮以快忿心;迹其施设,曾苻、姚之不如,宜其不能荡壹四海,成美大之业,岂非虽有智勇而无仁义使之然哉!”刘裕没有掌握机会,更没有破除破败污秽的劣政,而且变本加厉肆意而为,大开杀戒只为自己一时快慰,所以平定四海是武功,成就大业更需要仁义。这也许是司马光的一家之言,在《晋纪四十》中,记载了崔浩为拓跋嗣讲解经典时对刘裕的评论,“刘裕奋起寒微,不阶尺土,讨灭桓玄,兴复晋室。北禽慕容超,南枭卢循,所向无前,非其才之过人,安能如是乎!”
司马光对刘裕的批评还有另一事,刘裕攻克长安,其中功劳最大的就是王镇恶,由此南方的将领忌恨王镇恶,其中的沈田子自以为功绩不凡,于是与王镇恶争功。刘裕回到建康的时候,沈田子和傅弘之多次对刘裕说:“王镇恶的老家在关中,不能完全信任他。”刘裕并没有反驳,而是对他们说:“现在,我留你们这些文武官员、将领和精锐士卒一万人,王镇恶如果图谋不轨,只能是自取灭亡。你们别再多说了。”刘裕私下还对沈田子说:“锺会之所以没有作乱,是因为卫瓘的缘故。俗话说:‘猛兽不如群狐’,你们十多人,难道还惧怕王镇恶不成!”
对于刘裕的这一态度,司马光用了“疑则勿任,任则勿疑”来批评他,既然刘裕已经委任王镇恶镇守关中,就应该信任他,但是刘裕又与沈田子说了那些话,这无疑是挑拨他们的关系,让他们相斗,“惜乎,百年之寇,千里之土,得之艰难,失之造次,使丰、鄗之都复输寇手。”按照荀子的说法,“兼并易能也,坚凝之难。”兼并并不难,但是要将所有东西凝结为一体则太难了。司马光的看法在之后果然得到了印证,公元418年,王镇恶和沈田子同时出军北地抵抗夏兵的进攻,东晋军中传言:“王镇恶打算全部杀掉南方人,然后派几十人把刘义真送回江南,自己占据关中背叛朝廷。”辛亥,沈田子请王镇恶来到傅弘之的大营商讨战事,沈田子请求屏退左右侍从密谈,然后命他的族人沈敬仁在虎帐下将王镇恶斩杀,声称是奉太尉刘裕的旨意行事,不久,沈田子率领几十人赶来,声称王镇恶谋反,王脩逮捕沈田子,历数他擅自杀戮的罪行,将他斩首。对此,刘裕上书晋安帝司马德宗“沈田子忽发狂易,奄害忠勋”,东晋朝廷追赠王镇恶为左将军、青州刺史。
刘裕挑拨相离,是一种两面派的做法,而他对待帝王似乎也是两面派,“宋公裕以《谶》云“昌明之后尚有二帝”,乃使中书侍郎王韶之与帝左右密谋鸩帝而立琅邪王德文。”正是在他的操控下,司马德宗被杀死在东堂,刘裕于是声称奉司马德宗的遗诏,拥立司马德文即帝位,大赦天下。而刘裕也开始表现出称帝的野心,元熙元年秋七月,宋公刘裕接受晋封的诏命,成为宋王,“辛卯,宋王裕加殊礼,进王太妃为太后,世子为太子。”随着刘裕登上王位,经历了西晋和东晋的晋王朝也走向了最后的覆灭。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58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