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08-20《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重要的是建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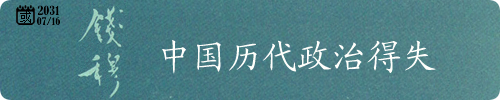
只有在当时成为时代意见的,所以到后来,才能成为历史意见。
——《前言》
1955年,何敬之找到钱穆,想让他作关于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的演讲,但是演讲只限五次,而且每次只有两个小时,由于“不能对历史上传统制度详细陈述,精密发挥”,所以钱穆只选择讲述汉唐宋明清五代,而且只是“略举大纲”,从每个朝代的政府组织、考试和选举、赋税和兵役等四个方面概述,“在此四范围以外的,则暂不涉及了。”后来因为钱穆负伤养病,没有精力对讲稿进行改进,“将来若偿夙愿,能写出一部较详备的中国政治制度史,则属至幸”,但实际上后来钱穆也没有实现自己写一部宏大而具体的中国政治制度史,这或者也留下了遗憾。
五次演讲分别择要讲述了汉唐宋明清五代的制度,不仅只是略举大纲,而且五代之制度也并非涵盖“中国历代政治”,但是钱穆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却是从这代表性的五代延伸出对于中国政治的得失考察,在这个意义上,作为一种管窥,择要讲述的制度反而构成了“历代政治”的观察样本,而在更为学术的观点上来看,汉唐宋明清,每一朝代的制度所形成的意见,都是基于“那制度实施时代的人们所切身感受发出的意见”,这就是钱穆称之为的“历史意见”,对于那个时代来说,是真实而客观的;但是,这些制度在时代的变迁中消失不在了,后代人从自己所处的环境和需要批评历史以往的各项制度,这就形成了时代意见,时代意见虽然并非全不合真理,“但我们不该单凭时代意见来抹杀已往的历史意见。”历史意见不一定会成为时代意见,时代意见也不是历史意见的堆叠,它们的不同正是共时性和历时性的不同。但是历史意见和时代意见在分野的同时,也有其不可分割的关联,在钱穆看来,只有在当时成为时代意见的,到后来才能成为历史意见,我们现在重视历史意见,就像当时重视时代意见一样,“这两者间,该有精义相通,并不即是一种矛盾与冲突。”
历史是发展的,历史是变化的,历代的政治和当时朝代的社会环境相关,制度也必是政治变化的一个见证,这就是历史的历时性,但是在变动中却有政治上的规律,发展中也能显露出中国政治的普遍规律:钱穆介绍了汉唐宋明清五个朝代的四个范围的制度,这些都是历史中的知识点,都是历史意见的反映,但是他并不是单纯就知识而知识,也并不在讲授和接受之间建立一个简单的教学关系,而是从历代政治提炼出时代意见,“任何一制度,决不会绝对有利而无弊,也不会绝对百并而无利。”得失就是根据实际利弊而定,利弊,就是在当时所发生的实际情况而觉出,最后形成了在“精义相通”中得出中国政治制度的得失论,并且用来指导还没有成为历史的现实。
钱穆在历代政治中如何发现历史意见?有如何将这些历史意见变成用于指导现实的时代意见?在《序》中钱穆其实陈述了自己研究历史的目的,“要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绝不该忽略中国传统政治。”如何从传统政治中客观检讨中国文化,这是钱穆想写中国政治制度史的第一个原因,在这里历史的“客观性”是他所极力强调的,客观性必须将历史放在历史本身的框架里,这个历史的框架就是基于历史意识的时代意识。辛亥革命前后,把秦以后得政治传统简单地用“专制封建”四个字一笔抹杀,这就是对传统政治的忽视,也加深了对传统文化的误解,在他看来,这就涉及到制度的本质:政治制度必然要“自根自生”,要与传统融合,这样才能发生相当的作用,即使从国外移来,也并非要全盘接受;在这个观点之上,钱穆认为,政治是有生命的,是需要配合的,否则就无法生长,他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历史观点:“制度必须与人事相配合。”制度是死的,人事才是活的,死的制度必须要配合活的人事,如果摧残人事来迁就制度,就是模仿抄袭,他举例在人人言变法和革命的年代,似乎只要建立了制度一切人事就会随制度而转变,所以出现了对外国现成制度的照搬,出现了高唱民主却痛斥旧传统的革新派,这又回到了对历代政治的简单评说,所以钱穆认为,“任何一制度,亦绝不能历久而不变。历史上一切已往制度俱如是,当前的现实制度,也何尝不如是。”
由此在《前言》里,钱穆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政治观:政治应该从人事和制度两方面来讲,“制度由人创立亦由人改订,亦属人事而比较稳定,也可以规定人事,限制人事。”第二,即使讲制度,制度也并非是孤立存在的,各项制度间相互配合才能形成一整套的制度;任何制度的设立尤其外在的需要,也有内在的用意,而这种外部和内在的需要也来源于人事;不存在绝对有利的制度,也不存在绝对好的制度,它必须在历史发展中进行调整;讨论制度,应该重视其时代性,同时要重视其地域性,也就是说,必须重视制度的国别性;历史的特殊性牵连到深入全部文化史中,“政治只是全部文化中一项目,我们若不深切认识到某一国家某一民族全部历史之文化意义,我们很难孤立抽出其政治一项目来讨论其意义与效用。”
在这里,钱穆提出制度和人事结合、死的制度要在活的人事中发挥作用,可以看做他对历史的一个基本且重要的观点,而这也是他阐述几千年的中国政治绝非只可用“专制黑暗”四个字简单拒斥的。在讲述汉代政府组织中,钱穆认为秦以后,中国开始有一恶搞统一的政府,在统一的政府里,不能没有一个领袖,这个政治领袖就是皇帝,在中国以往政治条件中,皇位世袭是一个自然的办法,但是在秦汉以后,封建制度已被推翻,只有皇帝一家是世袭的,这在中国政治制度上是“一项绝大的进步”,但是它同样留下了一个问题:皇室和政府的关系,这不仅是秦汉时代留下的问题,也是中国政治史上一向要碰到的大问题,这就是一个国家权力问题,“皇权和相权之划分,这常是中国政治史上的大题目。”
比如汉代的政府组织,皇权和相权是分开的,皇室和政府也就分开了,但是皇室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固守而不变,汉武帝具有雄才大略自己揽权,似乎并没有什么大问题,但是他死了,那些后代小皇帝缺少能力,于是大司马大将军来辅政,便出了问题,比如汉宣帝之后的外戚造成了内廷权重外朝权轻的局面,于是有了王莽代汉;到了光武帝,因怕大权旁落加重了尚书的地位,外朝的宰相也分成了三个部门,致使政府的权力分散,所以钱穆认为,皇帝好只是人事好,但没有立下好的制度,更没有管束皇帝的制度,这就成为了中国政治制度史上的一个大问题。皇室和政府的关系,在这里就发生了冲突,而汉代的选举制度,到后来也造成了门阀新贵族,经济制度和兵役制度也都出了毛病,所以,钱穆认为,说汉代并无制度,或者说一切制度都是专制和黑暗,都是不对的,制度是历史事项中的一项,没有哪部人类历史是百年不变的,也没有哪项制度经过以两百年还是好制度,“一项好制度,若能永远好下去,便将使政治窒息,再不需后代人来努力政治了。惟其一切制度都不会永久好下去,才使我们在政治上要继续努力,永久改进。”
这就是制度的变化观,同样,在唐代的政府组织里,它改变了了汉代宰相具有的领袖制,采用的是委员制,宰相之下的中书省、门下省和尚书省“职权会合”,不会出现皇帝未经中书门下而径直颁下诏书的规定,这是一种变通,但更是一种通融性的表现,“往往每一制度,都留有活动变通之余地,不肯死杀规定,斩绝断制。”所以中国的政治并不是完全皇权和相权有分别,而是比较合理开明的专制,“它也自有制度,自有法律,并小全由皇帝一人的意志来决定一切的。”唐代正式有六部尚书,成为管理国家政务的机构,改变了汉代只似皇帝侍从的地位,这就是中国政治的一大进步,无论从体制上还是从观念上。但是在地方政府的制度上,则不如汉代,唐代的中央集权造成了内重而外轻的局面,唐代监察使逐渐演变为地方长官中的最高一级,压制了地方,后来慢慢产生了节度使,最后演变成了“藩镇”,安史之乱就是由此产生的;唐代的科举制度开放了政权,成为门第特殊阶级的一条道路,比起汉代的选举制度外而言更广也更自由,这也是进步,但是当参加考试的人越来越多,出现了“土无官,官乏禄,而吏扰人”的大流弊;在经济上,汉代实施了盐铁政策,唐代则在租庸调制被破坏之后兴起了茶盐诸税,后来通过赋税向外开疆拓土,再加上向外用兵而引起军人,内战频起,这些都是由兵祸引起的经济制度之变动。
| 编号:Z96·2240516·2119 |
所以考察制度的变迁,钱穆认为,制度一方面需要不断生长,而且必须在现实环境下生长,它绝不是凭空从某一理论而产生的,另一方面,现实中产生的制度,也必然有一套理论和精神。因为,理论是制度的精神生命,现实是制度的血液营养,两者缺一不可,唐代的府兵一变而成为藩镇,军阀割据,胡族临制,这是惊天动地的大变迁,但这并不仅仅是一种政治制度的变动,“所以我们要研究政治制度,也该放大眼光,不要单就制度来看制度才得呀!”这是钱穆从历代历史这一纵向切面的考察提出的观点,制度是随着环境而改变的,制度是因为人事变动而修正的,制度也可能随着时代而灭亡,这是一种历史性的变化思想。在这种历史的考察中,钱穆也创新性地分析了中国历史中的一些怪现象。在分析了明代的政府组织体系后,他认为宰相的废止是传统政治的一大变革,但是由此也此女工程了一个多头政府,设立的内阁大学士没有实权,他只能“勾结太监”——明代的张居正实施的变法为什么失败了?钱穆并非分析变法之败,他直接指出正是因为内阁大学士的尴尬地位,他主张法治实际上是“违法”了,而且违反了当时国家的大法本法,如果张居正在汉唐宋时一个好宰相,但是在明代他只是内阁大学士,不是政府中的最高领袖,当然不能以此擅自做宰相,“这是明代政制上最大的法理,也是明代之所以异于汉唐宋传统的。”
另外,钱穆在这里也谈到了“官与吏流品泾渭之所分”,在中国政治上官和吏之分就形成了流品观念,也使得中国社会有流品而无阶级,而西方社会中则完全相反:有阶级,无流品,“直到今天,流品观念在中国人脑里还很深。”行业语行业之间,就分出了清浊高下,文官和武官一样是官,官阶相等,但是因为流品观念他们显然有了分别,“这一流,那一流,各自有品,等级不同。”在流品观念中,职业被完全人为化了,而且根深蒂固,“在上面流功的叫清流,在下面沉淀的是浊流。只要一行做吏,必淀入浊流,再也不要想翻身,再也爬不上来。”另外,在考察清代制度的时候,钱穆提出了“法术”的概念,他认为制度指的是政治,而法术指向的是事情或手段,制度出自于公而法术出自于私,清代因为部族政权的存在,由于满族人的统治,“一切由满洲部族的私心出发,所以全只有法术,更不见制度。”在这个意义上,当清朝末年出现了变法一派,在钱穆看来,并没有认识到这种法术,康有为认为只要皇帝实行变法就会成功,这就是他犯的错误,“他误认为中国传统政治只是皇帝专制,故而以为只要皇帝听我话,便可由皇帝专制一变而为皇帝立宪。”清朝是部族主权,是私性法术,并不是所谓的皇帝专制,所以真正要推翻清朝统治,就非革命不可,“打倒满洲人,就是打倒这政治上的一种特权。”
在指出中国历代政治问题的同时,钱穆通过对中国历代制度和西方制度、人事的比较和考察,在横切面上提出了中国政治的得失问题。汉武帝时制定了盐铁制度,这是皇帝把所有权收回的一种制度,于是就盐铁就变成国营与官卖,“这个制度,很像近代西方德国人所首先创始的所谓国家社会主义的政策。”也就是说,在汉代已经有了“国家社会主义”的政策;汉代的兵制是全国皆兵,这样的制度和西方近代普鲁士的俾斯麦政策相似;唐代出现了三省职权会合,这说明对意见的抉择往往不取决于多数,这个西方的民主精神不同,是取决于贤人的制度,“贤属质,众属量,中国传统重质不重量。”但是正因为皇帝权力被限制,中国皇帝也不会也西方革命中的皇帝那样被推上断头台;宋代的考试制度,在汉代、唐代制度基础上进行了改革,集聚了不少聪明才智,直到晚晴,西方还采用这样的制度来弥补他们政党选举制的偏陷,而我们却“一口气吐弃了”,实在是一件诧怪的事;清代出现了部族政权,钱穆考察中国的政治主权,认为不会被一个人掌控,掌控政权者一定是集体的,但是和西方的政权相比,中国的政权不是皇权,不是贵族政权,不是军人政权,当然更不是资产阶级政权,“若说政权,则中国应该是一种士人政权,政府大权都掌握在土——读书人手里,从汉到明都如此。”除此之外,还有特殊的政权,就是部族政权,清代就是部族政权,不管何种政权,要建立一种全民政权是理想,但更是一种理论,通过比较,钱穆认为西方民主国家说他们的政权代表着全民,那么中国历史上的读书人也可以说代表着全民。
通过对中国历代政治和西方政治的比较,对中国制度和西方制度的对比,钱穆的这种横向切面无疑具有现实意义,在辛亥革命开始的变革甚至革命中,要建立像西方的民主制度成为了一种呼求,但是就像对待中国历代政治的态度一样,决不能简单化,他从两千年的历史发展来总结中国传统政治的大趋势,其中提到中国政府的集权是逐步发展的,国家需要凝固的中央,政权自然要集中,但是后来集权之势越来越明显,最后地方政府反而衰败了,这就成为了中国历史的“极大一问题”,所以他提出的一个历史议题是:“如何使国家统一而不要太偏于中央集权,能多注意地方政治的改进,这是我们值得努力之第一事。”第二,中国的传统政治,造成了社会各阶层“一天天趋向于平等”,那就带来了一个问题:谁来关政治呢?当读书人通过做官成为政府的主力,当士人政权被建立,工商业就被人看不起,这就造成了和西方社会的本质不同,在现代化的道路上便被西方落下;第三,中国的政治制度在不断发展中变得越来越繁密,这样就造成了对人才的束缚,中国政治的制度化也偏重于法治,但是西方的近代政治则偏重于人治,偏重于事实化,“我们的传统政治,往往一个制度经历几百年老不变,这当然只说是法治,是制度化。法治之下,人才就受束缚了。”所以要走西方的路,就需要有一种新政,这种新政要将社会在“新的共尊共信之点”凝结起来。
很明显,从横向和纵向对历史的考察,钱穆就是要从历史意见中寻找适合现实的时代意见,这正是历史面向现在面向未来的关键所在,“历史终是客观事实,历史没有不对的,不对的是在我们不注重历史,不把历史作参考。”所以梳理中国历代政治,考察中国制度变迁,分析中国传统政治和西方近代政治的异同,就是要寻找适合中国的新政,但是这新政不是简单推倒过去制度而实现的,“重要的不在推倒,在建立。”而建立也并非是简单地制度,而是和制度相适应的人事,和制度有关的社会,更重要的是,历史上的政治就是文化的一部分,“政治也是人文科学中一门,我们回头把以前历史经过,再看一道,总还不是要不得。”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5916]
思前:豁出命去西域考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