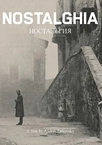2021-08-20《乡愁》:最后剩下灰烬和骨头

9分6秒的长镜头:安德烈点燃手中的蜡烛,走下水已经排干的圣凯瑟琳温泉池,向前走了几步又回过来,伸出左手触摸了一下温泉池的石壁,像在起点做了一个记号,然后小心翼翼向前;烛光在风中摇曳,安德烈一边向前一边看着蜡烛;风终于吹灭了蜡烛,安德烈又回到起点,然后再次点燃蜡烛,又沿着刚才的方向前进,烛光依然在风中摇曳,安德烈用风衣挡住了风,但是没走几步,风还是吹灭了蜡烛;再次回来,再次点燃蜡烛,再次从原点出发,再次用衣服或者手掌遮挡风;慢慢地,安德烈已经靠近了温泉池对面的石壁,他将蜡烛放在了石壁上,风吹动着烛光,烛光在摇曳中却没有熄灭。
从做了记号的石壁,到最后抵达的石壁,这是一个由起点和终点组成的路线图,蜡烛灭了,蜡烛再次灭了,蜡烛终于没有熄灭,9分6秒的长镜头完整记录了整个过程,当点燃的蜡烛在风中摇曳,安德烈完成了一个奇迹,按照多米尼克的说法,这个温泉池是以和上帝说话的圣凯瑟琳的名字命名的,烛光不灭就是一次奇迹,而这个奇迹的意义在于对世人的救赎,“如果有人能擎着烛火走过这个温泉而烛火不熄灭,那么世界将得到拯救。”因为多米尼克把家人关在房子里达七年,所以他被当地人称为疯子而失去了进入温泉池的机会,当他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安德烈,而安德烈又以自己的努力完成了这个行为,奇迹便诞生了。
但是,奇迹却以另一种方式坍塌了:当安德烈最终将燃烧的蜡烛立在石壁上,他自己却倒下了,常年患有心脏病的身体仿佛再也无法承受内心的压力,在安德烈一次一次回到原点继续行走中,小心翼翼的他已经感到了不适,但是他没有停下,最后是忍者疼痛走到了终点,奇迹诞生,生命却停止了。当烛火不灭成为奇迹,成为对世界的救赎,为什么他无法在奇迹中救赎自己?这是不是关于生命之火熄灭的寓言?当安德烈以个体的死亡完成奇迹,在罗马的街头,多米尼克也以另一种方式燃烧了自己:他登上骑士雕像,向过往的群众发表演讲:“你们的心灵之路已经被阴影笼罩,让我们去聆听虫鸣,让我们伸展我们的灵魂,让我们手拉手——自由没有用……”准备好的音乐似乎放不出来,多米尼克却已经将汽油倒在了身上,在喊出“母亲”之后,他继续针对人类信仰的丧失发表了演讲,“你们体内的水,是火,然后是灰烬和骨头……”终于,他打着了打火机,然后点燃了自己,大火在他身上燃烧,最后他从雕像上跌落下来,仆倒在那里再没有动弹。
多米尼克认为人类已经走向了迷途,已经丧失了信仰,所以他用点燃自己身体的方式警示,这种以身殉道的结果最直接的呈现方式便是死亡。一个在罗马大街上以自燃的方式完成救赎,一个在干涸的温泉池中让烛火不熄的方式完成救赎,但是他们都牺牲了自己的生命,甚至都在火中实现了奇迹,当信仰意义上的奇迹和个体意义上的死亡一起发生,他们真的可以拯救他人?真的可以唤醒信仰?“你们体内的水,是火,然后是灰烬和骨头。”安德烈和多米尼克最后都走向了自己的灰烬和骨头,他们甚至也无法看见这个奇迹对于他人的意义。而似乎更为可悲的是,他们创造奇迹都只是在“私人性”的层面上:安德烈一个人走完了奇迹之路,他的旁边没有观者,更没有被打动的人,而多米尼克选择罗马大街,是为了获得一种群体效应,但是他点燃自己的时候,旁边的人也都成为了旁观者,他们甚至是冷漠的,就像观看一场演出一样,不和自己的生活发生任何的影响。
| 导演: 安德烈·塔可夫斯基 |
当奇迹和救赎变成灰烬和骨头,那种悲壮的牺牲里,似乎渗透了安德烈·塔可夫斯基浓厚的悲观主义,或者说,无论是安德烈还是多米尼克,他们无法构建一个“布道”式的牺牲场景,所有的信仰,所有的救赎,所有的回去,也都变成了一种个体行为,而这是不是意味着对乡愁的寻找,对故乡的回归,都只是一个幻梦式的存在?就像安德烈吟咏的诗句:“我就是那蜡烛,在盛宴中消亡,天明后收起一地的烛泪……”蜡烛消亡变成了宿命,他们或者还是当地人口中的那个疯子,女翻译口中被讥讽的“圣人”,只能在自己的圣火中点燃,最后是无情的熄灭。
实际上,当他们变成一种个体性的牺牲,他们其实已经被“他人”所异化了,安德烈离开故乡来到意大利,是为了写作一本关于音乐家索斯诺夫斯基的传记,索斯诺夫斯基曾经生活在意大利,但是后来因为无法忍受“异国土地的寒气”回到了俄罗斯,这是一次回归,爱上女农奴也好,满足自己的乡愁也罢,他回去了,但是最后也是“灰烬和骨头”,因为他已经找不到故乡的感觉了,他选择了自杀。索斯诺夫斯基是一个预言式的文本,安德烈的回归和死亡更像是对这个文本的复制,所以意大利翻译尤金妮亚曾经就问过安德烈:他为什么要回到俄罗斯?其实这才是最为关键的问题,为什么要回去指向的是一个无法融合的“现在”的问题,因为无法成为现在的在场者,他必须在过去、在故乡中寻找自己存在的意义,但是故乡已经不再是那个故乡,当一切都改变了,回去就变成了“回不去”。
过去和现在的隔阂,就是现实和信仰的分裂,就是自我与他者的分离,安德烈重走索斯诺夫斯基的这条路,就是重新跌入到这种分裂和隔阂中,就像他对尤金妮亚说:“诗歌是不可翻译的。”他知道有些隔阂是永远无法消除的,但是他的偏见在于他想要寻找一种共融的东西,比如他说诗歌不可翻译的时候,却又说“只有音乐是相通的”,他看到了不同语言之间天然存在的隔阂,却又努力寻找另一种相通的路径,但是音乐和诗歌真的存在本质差别吗?另一方面,他甚至期望通过工具来跨越这种不可通约性,就像他意大利语不好,所以让尤金妮亚来做翻译,而两个人之间也存在着无法弥合的矛盾,不仅仅关于个别词的翻译,也涉及到不同信仰、真理和文化的理解,安德烈自负地对尤金妮亚说:“你们没有人能理解俄罗斯。”而尤金妮亚也反驳道:“你也没有理解真正的意大利。”
在音乐中寻找相通性,用“翻译”工具来对话,这是安德烈消解隔阂的办法,但是“你们没有人能理解俄罗斯”又把自己禁锢在私人性的故乡中,这当然是关闭了那扇让外界通向自己内心的门,所谓孤独者,就是沉浸在自己永不打开的世界里。在和尤金妮亚一起来到乡村教堂的时候,身为意大利人的尤金妮亚似乎对这一切都很感兴趣,她盛赞那里呈现的美,而安德烈却在尤金妮亚走远之后自言自语:“我厌倦了了这些病态的美景,除了我自己再无所求。”虽然尤金妮亚身为他的翻译,但是在她内心深处有着对安德烈的喜爱,她会询问这两天有没有打电话给在莫斯科的妻子,她会在屋子里对安德烈说:“我的房间没有水了。”但是安德烈似乎对她冷漠着,他甚至只是将她当成一个翻译,那次拜访多米尼克回到屋子里,尤金妮亚正在吹头发,安德烈告诉了他关于多米尼克蜡烛的意义,尤金妮亚似乎并不感兴趣,安德烈问她的是:“为什么你这么害怕,你不自由,你也不懂。”尤金妮亚的回答是:“因为你是圣人,你想要圣母露出一只乳房。”尤金妮亚最后离开了安德烈,她让安德烈回到妻子那里,后来她打来电话告诉安德烈,她将要和自己的男人一起去印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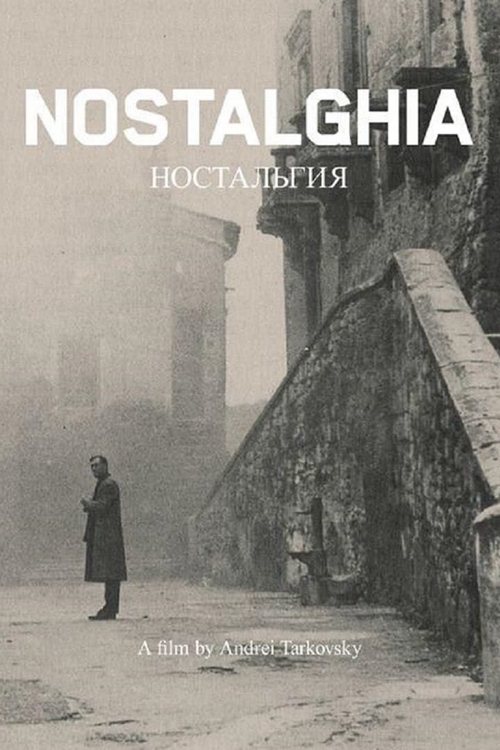
《乡愁》电影海报
安德烈有着强烈封闭性,他和尤金妮亚之间存在着语言上的隔阂,但更多是关于自我和他者之间的对话问题,而当尤金妮亚讽刺他是“圣人”,却给了他“露出一只乳房”的圣母作为对话者,圣母和乳房组合在一起,以及单独的一只,无不是对安德烈“乡愁”一针见血的讽刺,而安德烈就是生活在自我神圣化的世界里,在这个世界里,他的门关闭了——但是,他却在多米尼克那里找到了对话的通道,因为多米尼克和他一样,是在自我神圣化中变成了众人无法理解的“疯子”。一开始尤金妮亚作为他们之间的桥梁,和多米尼克对话,表达了安德烈想要和他聊聊的想法,但是被多米尼克拒绝了,第二次尝试依然失败,尤金妮亚一气之下拒绝翻译而离开。安德烈于是自己走近了多米尼克,在那间斑驳而潮湿的房间里,两个圣人开始了关于救赎的对话。
多米尼克曾经把自己和家人关在屋子里长达七年,因此当地人把他看成是不可理喻的疯子,他也丧失了走进圣凯瑟琳温泉池的机会,一方面他无权进入温泉池也是一种解脱,因为在温泉池里泡着的都是达官贵族,“他们为何泡在水里?因为他们想要长生不老。”凯瑟琳据说是见过上帝的人,以她的名字命名的温泉池就是圣洁的象征,但是那些男男女女却泡在池子中只为了长生不老,这是多么世俗的欲望满足,在多米尼克看来,就是一种堕落。所以他把自己和家人关在屋子里是为了解救。另一方面,温泉池依然是一个圣洁的存在,自己无法进入池子,那么就把这个任务交给安德烈,只要蜡烛不灭,那么世界就会得到救赎,末日的降临就会推迟。“请你帮帮我。”这是多米尼克的请求,蜡烛交到安德烈手中,就是一种救赎的移交,就像屋子里那片墙上写着的“1+1=1”,在多米尼克看来,信仰只有一个,救赎的道路只有一条,“一滴水加上另一滴水,只能是一大滴水,而不是两滴。”
1+1=1的等式让安德烈和多米尼克成为救赎的同一体,一个是被当地人剥夺了权力的疯子,一个是把自己当成是圣人却“想要圣母露出一只乳房”的乡愁者,他们首先要拯救的其实是自我的信仰——多米尼克选择在大街上自焚,是一种疯狂,也是一种极端,而安德烈和他不同的是,他游走在支离破碎的现实中,他活在无法翻译的隔阂中,种种的压抑和沉重,种种的禁锢和幻想,让他找不到返回的那条路。故乡对于安德烈来说,绝不仅仅是“俄罗斯”可以代替的,索斯诺夫斯基曾经在信中说:“如果我不回俄罗斯,如果看不到故乡,我就会死。”但是回去一样是郁郁而终,当回去变成单一地理空间的返回,那也是一种空无,甚至是更为痛苦的迷失。而故乡对于安德烈来说,也不仅仅是有自己的妻子,有自己的孩子,它还有永远无法回来的“无”,那就是一种“母亲情结”:安德烈在睡梦中总是听见有人喊他的名字,发出声声呼唤的,是那个躺在床上怀孕的女人,她是母亲,在另一个生命还未降生而被命名的世界里,母亲其实意味着孕育,意味着受难,而这正是俄罗斯民族的特征。
关键是安德烈在自我神圣化的过程中,他根本无法回到母亲身边,那最纯粹、最美好的记忆留存在安德烈的心中,它已经变成了一种圣洁的图景:孩子和女人走在山坡上,然后站在那里,远处是氤氲的雾气,是灵动的白马——这个意象不是现实的存在,它是安德烈的幻影,是自我神圣化的一种延伸,就像他总是面对镜子,镜子里是一个自己,而镜子中还有镜子,还有另一个自己,安德烈,另一个安德烈,另一个安德烈的安德烈,它以一种增殖的方式完成了安德烈对于自我的命名,如果按照凯瑟琳的说法:“你不是你,而我即是存在。”那么这镜子中的我,镜子中的镜子中的我,是不是永远不是真正的存在?安德烈梦见自己走进的是迷雾中的教堂,听到的是母亲梦幻般的声音,即是在他心脏病突发死后,最后的场景里他和那条狗坐在水塘前,身后是那个修道院,这是他最后回归的地方,如梦如幻,宛如奇迹一样发生。
无论是多米尼克还是安德烈,在无法通约的现实中只能建立自己的梦幻王国,在信仰陨灭世界堕落的罪恶中只能以牺牲的方式创造奇迹,自我神圣化当然是他们寻找“故乡”的一条歧路,但是当安德烈·塔可夫斯基以如此悲壮的方式注解了“乡愁”的意义,在另一个层面上他当然在反思着人类离开故乡的那种异化存在,安德烈为什么永远无法返回故乡?是因为故乡本身已经不存在了,母亲也被无情地解构了,诗歌无法翻译的隔阂,进入温泉池权力的剥夺,自焚中的冷漠,自我禁锢的不自由,还有什么对话,还有什么纯粹,还有什么信仰,还有什么奇迹?——尤金妮亚进入修道院,司事问她:“你是不是来求子或者其他?”尤金妮亚说:“我只是来看看。”司事反问道:“如果大家都这样,还会有什么奇迹?”他提供了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下跪,这当然是一种最世俗的方法,而这种世俗所消解的是信仰的真正意义,而司事所说的奇迹也只是为了生孩子,“一个女人注定会有孩子,养育他们。”母亲是对于孩子而言的,而当母亲只是生育,她又回到了工具式的存在,于是修道院正在发生的仪式变成了“虔诚祈祷的都是女人”的异化现实,“所有母亲的母亲,深知母亲之痛的圣母,所有母亲的母亲,深知母亲之乐的圣母;所有孩子的母亲,深知怀孕之乐的圣母,所有孩子的母亲,深知母亲之痛的圣母;全知的圣母,帮助你女儿成为人母……”于是,圣凯瑟琳的温泉池成为长生不老的澡堂子,于是,圣母露出了一只情欲的乳房,于是,用来救赎的奇迹最后剩下灰烬和骨头。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5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