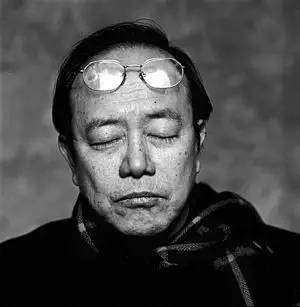2024-08-30《雷声与蝉鸣》:从遗忘中救出一些句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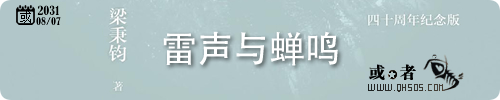
我抬头看见我远离
沙地上逐渐的白
毫无尘埃的清晰的影子
移向我
——《未升》
未升的是太阳,它就在那里,不动,仿佛时间的停滞。但是,在太阳未升的时候,是谁在“清白的等待中成型”?我们为什么要等待?要成型?而且是一种清白?后来我们走过了街衢,后来我们有了欢悦的脸,后来还看见了写着午餐的牌子——都到了午餐的时间,我们在清白的等待中已经成型了吧?可是太阳是不是还未升?——是我们比太阳更快地行动,是我们比太阳升得还快,于是,我们一下子就走到了“远离”。“我抬头看见我远离/沙地上逐渐的白”,是我远离了本来毫无尘埃的影子,也是我远离了在未升的太阳中的我,更是我远离自己的写照,即使最后的影子移向了我,即使看起来是“同样的人”,一切也比时间流逝得快,我成为了“泅泳者”,我大约找到我和影子,于是我成为了“他”,而他所看见的是“那些/尚未成为太阳的”——依然是未升的太阳,依然是远离的影子,就这样一首一九六八年的诗成为梁秉钧一种“成长的烦恼”。
第一次读梁秉钧的诗,但是对他早有耳闻,只不过知道的是他另一个更为有名也更有诗意和哲理的名字:也斯。也斯,yes的音译,但是却带着中国古典意境:是从《他们在岛屿写作》的纪录片中认识了也斯,也是从许鞍华的《诗》中更多了解了也斯,先闻其名再读其书,有一种疑惑是:为什么诗集的作者是梁秉钧?这是也斯的一个习惯,他创作的诗歌只署名梁秉钧,也斯属于他的散文和小说:梁秉钧是也斯?也斯是梁秉钧?是不是就像在“未升的太阳”中,也斯是梁秉钧的另一种成形?是不是“尚未在太阳之下”,梁秉钧也会看见远离的也斯?看纪录片的时候,那个叫也斯的小说家和散文作者已经真正离开了,当拿起诗集,是不是梁秉钧未曾真正离开?
仿佛人生的双面,而这本梁秉钧最早的诗歌集子《雷声与蝉鸣》就是在写“我抬头看见远离我远离/沙地上逐渐的白”的状态,成形和远离,我和影子,都构成了“同样的人”,却在泅泳者归来而不见中成为一种缺失。收录在诗集中的第一首诗完全展示了梁秉钧的功力,《树之枪枝》,树枝和枪支在这里合二为一,这是两面人生的合一,“这是佩枪的白杨/这是佩枪的基督”,从春天而来,为什么会有“树之枪枝”?因为愤怒,当那只鼹鼠在冷风与热风之间丧失了愤怒,一株树的发芽却是寻找到了愤怒:那挣脱束缚而“急急爆出”的芽,不正是会成为愤怒的树枝?而且成形之后“就这样子的愤怒下去”,面对施栖佛斯的大石头,“不管存在和不存在/就这样子的愤怒下去”。梁秉钧在诗集中的发声就是带着“树之枪枝”的愤怒,这是他发出属于他自己的“雷声与蝉鸣”。
| 编号:S29·2240519·2121 |
愤怒的背后是什么?是一种成形的渴望,是一种成长的自由,是对于命运的抗争,但显然这第一首的愤怒比未升的太阳跑得更快,当回过头来会发现时间还尚早,甚至时间从不和你成长的节拍一致,于是在《未升》这一辑中读到了太多在时间中流逝的东西。《夏日与烟》,标题就是时间的流逝,“至于烟 烟并不永恒/夏天也不是的”,夏天的冰激凌已经属于“昨日/的昨日”,现在变成了冷,冷冷的泉水,冷冷的化石,冷冷的草,而夏天的逝去最后化成了“洗衣铺的蒸汽机上/以烟的手以烟的脚”,夏季就是一阵烟,它的到来就是为了逝去——这首写于一九六五年修改于一九七〇年的诗,写作和修改横跨了五年,似乎是梁秉钧对流逝岁月的某种怀念,修改具有的重写意义是不是也是在缅怀?
“发怒”的“树之枪枝”和重写的“夏日与烟”,都是一种成形的态度,激情也罢,无奈也好,未升的太阳总是未升,远去的影子也在远去,而这是不是也是另一种必然的成形?《夜与歌》中思想的绿叶早在去年的院子里就有了,《浪与书》中的书就像是“流水般流过所有的构成”,《夜行》中的灰墙湮没了墙上的标题和“记忆中人面的杨柳”……时间曾经在哪里?时间又去了哪里?“下一段/所有关于时钟的描写/跳过它/略去所有围巾的风貌/略去栗子与巷道(《犹豫》)”那童年的街道、荒屋里的咖啡和糖,是不是都在时钟的略去中远去了?遥远的存在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对于我/犹如你的名字/对于我/犹如他们的名字”,因为我之存在也在时钟的略去中变成了你或他们,因为我抬头也看见了远离我的那个影子。《缺席》很明确地写到了时间的缺席:时间有一张鬼魅的脸,没有脸孔,笑也空无一片,一开始是看见的,但是,“当我再抬头时/已经没有他踪迹”。
这就是梁秉钧的《未升》状态,本是在未升的太阳之前让自己在等待中提早成形,于是愤怒,于是爆出,于是重写,但实际上是在成形中流逝了太多的东西,远去的是自己和影子。当然在这本诗集中,梁秉钧写得最好的就是《突发性演出》这一辑:为什么会突发?为什么会有演出?“可是演出计划里的某些部分/应该开始的还未开始/出现的还未出现”,计划所对应的是应该,但是应该只是一种理论上、预设上的存在,现实却是:应该开始的还未开始,应该出现的还未出现。这是一种错误,这也是难堪,“独自笨瓜地卧在那里”,而且说好的意大利粉变成了雨。梁秉钧设置了这样一个场景,就是突发性,就是演出,无疑,“突发性演出”强调的是某种猝然的改变,这种改变是对计划的颠覆,是对应该的否定,但是当现实变成“突发性演出”,不正是精彩的、具有戏剧性的好戏上台吗?
|
| 梁秉钧:就这样子的愤怒下去 |
《寒山及其他》,寒山和拾得,是不是就是那种避世和隐居的生活?再也没有了,于是进入到了现实戏剧性场景中:没有了诗人,只有刻在“灭绝人性的岩上”的诗,没有了泉水,只有变成了灵丹和济众水广告的水,“面对黄昏杂沓的风景/我的朋友说/你以为你是那不系之舟么”;《面包店》里发生的突发性演出和爱情有关,他和她,一起走过理发店、脚踏车店、中药店和“门缝里露出灯光的小铺”,在一条破烂的路上行走,只有有温软的笑就足矣,但是突发性演出开始了:一直走到了面包店,他竟傻傻地把书还给了她,然后就分手了,“你以为这是甚么/一出面包突发剧?”面包不是用来吃的,面包店也不是只是经过;当然,突发性演出来了个更大的反转,“这时他走过了面包店/灯影晃荡/向潮湿的地面移过去一两寸。”戏剧性张开,移过去干嘛?留下的是无限想象的空间;《听歌》也是如此,在一场派对中的他和她,羞涩地没有说什么,后来唱片机坏了,后来大家都离开了,后来她也走了,“他甚至没有说:‘再等一会……’”只有他一个人修理坏了的唱片机,拿着螺丝起子、把零件砌回原位、按下掣,似乎在等待什么发生,“门在他背后/砰一声关上/这时唱片才开始旋转/歌声再一次传出来”,从无声到恢复声音,对于他来说是“突发性演出”,而在唱片机的歌声传出来后,他的内心也经历了一次“突发性演出”。
“突发性演出”具有的戏剧性是梁秉钧对于生活的发现,它是意外,它是偶性,但更是另一种可能,也许这样的演出也是一次创作,《写一首诗的过程》就是一次“突发性演出”:女孩打算喝掉面前的咖啡,然后写一首诗,喝咖啡和写诗是她这个晚上的计划,但是咖啡是苦涩的,窗外总是想起打牌的声音,还有舞女和夜归男子的吵骂声,当然妨碍了她的写作;她继续自己的计划,“她给咖啡再加颗糖/加一点牛乳为了衬上杯子的颜色”,又想到未来的诗会在哪里,这时外面有警车开过,她看见醉汉在拍木料店的门,于是她决定写一出“生活的戏剧”;但是外面什么也没有发生,而在房间里的她感到了疲倦,于是画了一只胖胖的猫,于是再喝了一杯咖啡,于是再看窗外,“看寂寞起来的街道/想最好有一点微雨/滋润这街道,并且闪光/如一朵朵在黑暗中绽开的花”;想着想着自己却睡着了,恶如此时,街上开过来洗街的车子,“终于把街道变成潮湿”。从计划写诗,到外面的干扰,再到决定写生活的戏剧,再到想象街上开出闪光的花,这一切构成了女孩的“突发性演出”,写作的过程在这突发性事件的影响下到处是计划外的情况,但是真正属于“突发性演出”的则是她在梦中而现实却实现了她的想法:是现实变成了戏剧,还是戏剧渗透到了生活?
女孩《写一首诗的过程》,当它变成一首诗,也是梁秉钧“写一首的过程”,这个过程被“突发性演出”所支配,而不管是写诗还是生活,在梁秉钧看来都充满了突发性和戏剧性,它从来不是完全的计划,不是应该的现实,而是处处呈现了意外和可能,处处彰显了戏剧性——如此是不是也对时间流逝现实的一种重构?从第三辑“香港”、第四辑“澳门”到第五辑“广州肇庆”、第六辑“台湾”,梁秉钧开始了空间上的游离,这本该在不同地区的旅行中发现更多意外和可能,但是梁秉钧却将它们都写成了走马观花的诗作,既没有发掘其中的深度,也没有将自己作为他者的身份表达出来,看见是单向度的看见,遇到也是简单型的遇到——除了在一些破败中感慨,基本上没有其余的情感,就像他在《旅程》中写到的一样,“我们倚着靠背椅睡去/又再醒来/唱歌、谈话、喝一杯茶/找寻更壮大的树木/更巍峨的石崖/找寻更高耸的瀑布/更漫长的海滩”。
空间完全变成了移动的平面,梁秉钧的诗或者真的只能在时间的变迁中看见发生的事?《浮苔》这一辑诗歌像是他的回归:再次审视时间的流逝,再次观察影子的离开,再次面对记忆的缺席,也再次构筑“突发性演出”:《青晨》中热腾腾的东西逐渐冷却,《除夕》中在人们琐碎的话语中看见的是“没有挂钟的墙壁”,《青蛙与蜗牛》相关的一幕又回到昨日空酒瓶的记忆,两人的矛盾最后变成“玻璃的寒冷”……这是一个“未央”的世界,一同背诵辛迪诗歌的人不见了,一同走过水边断岩的人不见了,一同醉酒和唱歌的人不见了,只留下了我们,我们醒着,我们看着,我们回忆着,“我们留在这里/守着一方清凉的灯光”,为的是什么?那就是“从遗忘中救出一些句子”,所谓未央,就是没有在众人离去和睡去中画上句号,就是没有在时间成“封上的窗口”中消失,从遗忘中救出句子,是因为还没有完全遗忘,并且以拯救的方式抵抗遗忘。
“救出的句子”就变成了梁秉钧的《雷声与蝉鸣》,一种抵抗遗忘的“声音叙事学”:雷声使人醒来,雷声之后是大雨的声音,当大雨化作檐前的点滴,蝉鸣又响了,还有鸟的啁啾、鸡啼、钢琴的试探和安慰……从雷雨到蝉声,声音构筑了夏日的景象,而和外部世界的声音相比,“室内是安宁的”,“书籍、画片、信札和锁匙/能把芜乱的世界隔在外面?”就像内心世界,安宁而寂静,和外面的世界构筑了某种对立,但是,“一旦回头/又仿佛听见门边有喘息的声音”,里面也有声音,声音也在叙事,在打通了内和外的隔阂之后,声音成为了一种新的开始,“雷声隐约再响/蝉鸣还在那里/在最猛烈的雷霆和闪电中歌唱”,而且梁秉钧赋予了不绝的蝉鸣一种再生的诗意,“蝉鸣是粗笔浓墨间的青绿点拂/等待中肌肤上一阵清凉/因为雨滴溅到身上/而发现了那温暖”——这雨滴的温暖是不是就是在声音中最后的成形?经历了这成长中的烦恼,一种声音叙事学就在“从遗忘中救出一些句子”中完成了新生:
它又会再带着温柔的心
在中断的地方再攀爬
当你怀疑,你见它停在尘埃里
等你相信,又见它从伤口
怯怯地伸出手来
——《盆栽》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45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