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08-31《蔬菜的政治》:用筷子拨动晴雨山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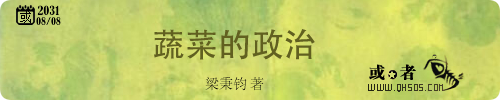
后来的人把这道菜煮得太干,忘记了
原来的主题,我们在搅拌中
逐渐失去了自己
太模糊、太软弱、太妥协
难以达到朝思暮想的形状
——《家传食谱秘方》
“后来的人”是谁?是“我们”;后来的人忘记了什么?忘记了主题,忘记了做法,忘记了味道;后来的人又做了什么?“在搅拌中失去了自己”……后来的我们也还在做着和食物有关的事,但是在“太模糊、太软弱、太妥协”中难以达到朝思暮想的形状,这就是平庸。所以在这样的平庸中,需要从后来返回到从前,需要找回失去的记忆,寻回家传食谱秘方。
“寻回”变成了告别平庸的一种必然途径,很明显,梁秉钧构建了从过去到现在“家传”的必然轨迹,正是要让记忆和味道成为后来的人的一种必须,正是要让家传的东西继续保留并发挥应有的价值,所以需要寻回。那么和后来想对立的过去到底有什么东西?那是童年的脚步经过的小巷,那是殖民地大屋中传出的香味,那是市镇“休憩我们的欲望”的零食,那是成长中咀嚼微甜的苦酸——一切都和味道有关,最有味道的当然是老祖母的鱼饼,那是“无法分辨的咸与甜的混合”。过去的记忆,过去的味道,是那么美好,当后来的我们面对平庸的烹饪,如何寻回那张家传食谱的秘方?要寻回就要知道它在哪里,在某一个阁楼或一道关上,在南欧风味的木窗下,甚至或者在大床被褥的夹缝间——但是,这张发黄褪色的纸已经被虫蛀掉了,或者再也无法找到了。
在过去和现在构筑的关系里,“家传”在某种程度上体现着断裂的可能,“寻回”就是这种断裂的写照:如果保存得很好,如果有人继承了祖母的手艺,何必寻找?但是在这里,梁秉钧对于这种断裂采取的态度,一方面是在回忆中寻找,试图将“家传”以另一种方式传承,记忆或者就是这种传承的表达;而另一方面,梁秉钧将其看成是“神秘仪式”,在“姊妹们曾经记下、亲友反复抄写”中可能已经变成了在“众口间流传”,也就是说它突破了家族的限制,成为更多人知道的仪式,也成为更多人在记忆中的美好,那么在这个意义上,只是丢失了自家的那个秘方又有什么关系?“我们到处访旧寻新/搅拌锅中种种,不知能否寻回那丰富”,它流落于别处,不正是另一种继承?
梁秉通过《家传食谱秘方》凸显了过去和现在的断裂,但也提供了从个体走向大众的可能途经,而着眼于食物的《蔬菜的政治》,不正是梁秉钧用诗歌传播饮食文化、探究美食记忆甚至寻回食物历史的目的所在?在这本诗集中,“蔬菜”所表达的美食文化是其中的重点,包括《蔬菜的政治》《亚洲的滋味》《异乡的餐桌》三辑,就是直接写食物的。在梁秉钧的笔下,美食散发出独特的味道,《汤豆腐》让我们达到了“非常禅的境地”,从《京渍物》中看到了一种渴望,“我知道,整个夏天你一直在等待/成长为京城里最美味的肌肤”,而普通的白粥,不比鲍鱼那样的极品,却在平淡中尝出众生的味道,梁秉钧于藤井、山口及林教授共饮,感受到了“新滤酒”在酒和醋的混合中,“且尝模棱的味道焕发的美浆”。“蔬菜的政治”是饮食背后丰富的文化,但绝不是大吃大喝,绝不是饕餮盛宴,也绝不是满足简单的食欲,它背后有着丰富的“政治”。
政治是什么?梁秉钧的“政治”显然也是一种丰富而多义的语义,它是《家传食谱秘方》中过去和现在的断裂,“寻回”成为弥合这种断裂的方法;它也是“不能吃”的禁令和“我想吃”的欲望之间的博弈:不能吃鸭鹅因为它湿毒,不能吃鸡因为禽流感,不能吃鲗鱼因为会哽骨,不能喝酒因为会乱性,但是越是不能吃,却也是想要满足吃,因为吃超越了吃本身,“它会在春天给我盖被/它会在夏天令我全身舒畅/它会在秋天令我头脑清明/它会在冬天把我包裹得暖和令我做甜蜜梦(《戒口》)”;它也是《鮟鱇鱼锅》中,食物对自身的超越,当食客们吃下了鮟鱇鱼锅,是食物在自我消灭中满足了人类,但是,“你带着我的一部分/我成为你的一部分/溶入更广大的汪洋”,这是人类和食物之间的对话,这也是一种从物走向艺术的创造。食物是文化传承的一部分,食物是人类美好欲望的写照,食物构筑起了“溶入更广大的汪洋”的可能,显然,“蔬菜的政治”在梁秉钧看来,也不只是这些。
《金必多汤》是“蔬菜的政治”特殊的一个文本,梁秉钧在与罗贵祥的对话中介绍了创作这首诗的背景,广州和香港在40年代的时候发展出了一种叫“豉油西餐”的食物,就是用豉油代替西餐中的牛油和芝士,这种切合中国人肠胃的创举可谓中西合璧,但是在当时来说,推出这一食物的事置身在中国和西方商人之间的“买办”,所以这种汤见证了历史。后来梁秉钧在加拿大温哥华一家怀旧餐厅点了这道汤,服务员端上来的却是奶油蘑菇汤,它的英文名字也改成了Cambridge Soup。在访谈中,梁秉钧认为40年代的“改造”是一次创举,温哥华餐厅的改变是另一种创举,食物在旅行中变异,就是为了适应新的环境,适应食客的期望,“食物由一个文化到另一个文化的流传总是发展出种种有趣的故事。”但是在这首诗里,所谓的“有趣”似乎没有了,对于当时变身为“豉油西餐”,梁秉钧的发问是:“如何在价格的差异间?赚取美味的利润?”昨天是咸鱼栏里的剩货,今天是待价而沽的珍馐,这是一种变异,背后是“把感情的买卖玩弄于股掌”的经济权力,而现在也一样,口袋里的软尺伸缩自如,算盘的各子上上下下,已经没有了统一的标准,重要的只有市场,只有买卖,“赌这一回所有财物如过山快车/突然坠落谷底/尽似无底深渊的富贵浓稠/可是蝇头小利粉末和了开水?”
| 编号:S29·2240519·2122 |
这是蔬菜另一种政治,蔬菜政治是就是相对于蔬菜本身的一种变异,梁秉钧认为,蔬菜代表的食物具有营养,营养变成我们的一部分,而我们对于蔬菜有选择权、改造权,“选择怎么样的食物,变成选择怎样的生活,选择我们变成怎样的人。”在这个意义上,蔬菜已经超出了食物的简单定位,它关涉的是口味,是伦理,是价值,是政治,“我们常常以为自己是自由的人,可以选择一切,其实我们未必完全可以自由选择放进口中的食物,有时是由于政治的禁忌、商业的霸权,有时源于我们自小受他人影响形成的歧视和偏执。”这就是梁秉钧所说的“蔬菜的政治”,而对于这样的政治,梁秉钧也提出了自己的政治观,“以食物为对象,不一定是要把我的意念投射在它身上,也可以是被它的特色吸引,尝试了解它,与它对话。”这就是梁秉钧将这些看做是现代“咏物诗”的一个出发点。
《亚洲的滋味》是梁秉钧对于亚洲具有代表性美食的一种书写,这里有“在异乡重造故乡的鲜嫩/安慰漂洋过海的父母?”的《新加坡的海南鸡饭》,有在肉汁自然留下中,“最底下的萝卜以清甜吸收了一切浓香”的《香港盆菜》,有“把所有日常的破碎黏合/预备一道菜所花的时间/点点滴滴收获无穷的美味”的《老挝菜肉饭》,有发现了米饭独特意义的《雅加达黄饭》:“米饭是我们共通的言语/米饭是我们安慰的母亲/米饭包容不同的颜色/米饭熨贴肠胃里旧日的伤痕”……但是“亚洲的滋味”不是单纯关于亚洲地方特色美食的味道,而是梁秉钧与美食的一场对话。从1997年开始他写和美食有关的诗,后来在温哥华举办了一个名为“食事地域志”的诗与摄影展览,其中的诗就是由香港文化出发,既是对“亚洲滋味”的一次寻访,也是向海外的华人介绍“亚洲滋味”。展览在2004年的时候回到了香港的文化博物馆,梁秉钧这次和装置艺术家陈敏彦与摄影师李家昇合作,将“亚洲的滋味”更为艺术化的展示:开出虚拟茶餐厅,墙上镶嵌了18世纪殖民地茶喝咖啡种植园的版画,墙上还印上了梁秉钧吟咏一种混合茶和咖啡的饮料“鸳鸯”的诗作,“并在诗的字位挖空,填上咖啡粉、茶以及茶与咖啡粉末的混合,观众凑近可以嗅到不同气味。”
从单纯的美食变成了艺术,而且是让观众融入其中的装置艺术,这是梁秉钧和蔬菜对话的一次升级,在他看来,不仅仅是人和蔬菜的对话,也是以亚洲为代表的东方与西方的对话,“我对亚洲文化的兴趣,令我想避免纯粹由民族主义的角度看问题。”而且是“亚洲的滋味”过去和现在的对话,“我发现很多食物的故事都连起历史。”这种多维度的对话也是“蔬菜的政治”多样化的表现,他认为其中的渗透和矛盾是另一种“东西”——诗集《东西》之外,地域之“东西”之外。但是和装置艺术展不同的是,梁秉钧在诗歌中呈现的是另一种“亚洲的滋味”,在那首同题诗中,他写到了朋友遭遇了一场地震,他却收到了朋友寄来的瓶子,在对噩耗表达悲痛的心情之外,在密封的瓶子中他尝到了腌制的蒜头的味道,却品不出滋味,“是泥层中深埋的酸涩、树木折断的焦苦?/还是珊瑚折尽鱼翻白肚的海的咸腥”,味道已经不再属于食物本身,而是混杂着更多的现实和命运,“从阳光普照的午后传来,你可是想告诉我/如何在黑暗中酝酿,在动乱中成长/千重辗轧中体会大自然的悲悯与残酷/如何以一点甘甜衬出大地人世无边酸楚?”
在这个意义上,这种滋味和艺术展览没有任何关系,甚至和“亚洲滋味”的地域性文化以及历史也没有什么瓜葛,梁秉钧将其看成是心和物的对话,“这种相遇可以是思考的、戏剧性的、幽默的、讽刺的、论述的、幻想的、公共的或是私人的。”这种多元化也许就是《异乡的餐桌》所传递的主题。当诗人远离故乡,当诗人暂居异地,他如何寻找对话物,无疑餐桌上的食物就是一种咏物的存在,就像《啤酒馆》里的每一种啤酒“都有一种性格在背后”。但是,餐桌只是异域勾起思绪的一种触发物,在异国他乡,食物反而渐渐被遗忘了,《在雪美莲家吃晚饭》这首诗里,他想起和朋友的点点滴滴,“一眨眼时间过得很快/我记不起我们吃过什么了”。于是,异乡的餐桌上不只是摆放了食物和菜肴,而更多是对于历史、文化的思考:他和朋友行走在巴黎的街上,对香港的历史不太清楚,却想起了“南西姑姑”,“她知道巴黎最时兴的去处/她出现的都是最好玩的派对/南西姑姑是我的偶像”;在《柏林的四月》中,想要见面的朋友已经搬了家离开了城市,于是想起了曾经一起对饮的时光,于是四月的河水还是流动,于是“窗外/飘下白色的雪絮溶进四月的诗句中”。
相遇或不相遇,想起或不想起,异乡到底带来的是生疏还是重逢后的亲切?在这里其实梁秉钧笔下的“异乡”并不是地理意义的,而是历史意义的,它在另一个维度里就是变异。在莱茵河畔看见兵马俑会有怎样的感觉和思考?这是“东西”之间的对话,但是对话不是由空间带来的而是时间意义上的,空间只不过对这种时间的变异有了更广阔的背景,“葬入深远的历史又再挖掘出来/不能说没有各自的神貌/但是在异乡观看的眼中/怕都只是没什么表情的中国人吧?”那秦俑的背后是什么?是扭曲,是血腥,是饥荒,是灾祸,“你的帝王/比别人埋葬更多儒士和书本”,对历史的审视变成梁秉钧最后面向现实的疑问,“从河边吹来的和风/可会熨帖你重重挫折的胸怀?/心中陵墓重门扣藏的千年暴戾/可会有一日在阳光下融化?(《莱茵河畔的兵马俑》)”可谓是历史的一种沉重,这是梁秉钧从饮食到文化再到历史的一种思考,那些关于美食的诗歌既像打油诗,又像口水诗,传递的都是一种轻松的感觉,“打油”和“口水”的风格似乎也成为了梁秉钧对食物的一种注解,但是透过食物,梁秉钧和物的对话却触及了更多的“蔬菜的政治”。
《北京戏墨》仿佛是对历史和文化的一次“戏墨”,胡同是北京文化的代表,但是,“我走过胡同/你已从墨尔本归来/帮老外在桥边弄了酒吧/并且热烈投入了房地产生意(《胡同》)”长城是北京的地标,游客遇到的是什么?“孟姜女劝你买长城纪念品/昭君才刚出塞/包车的师傅/老早就想回去再兜一转生意(《长城谣》)”还有那些故居,“还在画几笔墨虾,看蝌蚪的稚趣?/劈柴胡同变了辟才胡同/在一条很多盗版DVD的街道上/我找来找去找不到你的故居(《故居》)”从北京到香港,一样是一个逐渐变异的城市,这是“我们与昨天碰个满怀/却怎也想不起今天”的香港,这是“我们不断在换衣服衣服不断在换我们”的香港,即使在食物的层面,猪肉引起了涨价,生猪买手、供应商、民主党、报纸的社评、街市的阿婆各有评说,只有“躺在屠房的猪”表示,“目前的猪肉减价战/只是人类单方面的行为”;还有“生鱼引起的恐慌”,最后变成了一场国际贸易战,“不惜一切向敌人宣战!/不惜一切向生鱼开战!”这似乎就是一个经历了非典而“非电影时期”的香港,“你的非典型地扩张的热情/一下于公开在冷漠的眼前/戴上口罩,不见羞愧或鄙夷/自嘲的眼睛也自悯,隐藏了/但也同时显露了那么多(《非典时期的情诗》)”
实际上,“香港2,3事”是梁秉钧的诗歌,也是另一场关于香港的装置艺术展,2003年底,梁秉钧、李家昇和艺术家“我是山人”在城市大学做了这个展览,诗歌一方面是展览的内容,另一方面展览也成为了诗歌的主题,“香港2,3事”是发生在香港的故事,也是香港人书写的故事,但是这其中有着强烈的香港历史记忆。“我是山人”用红蓝白胶袋为材料设计了展览,这种红白蓝的胶袋就是过去回乡探亲时人们常用的一种袋子,里面可以装很多东西,而现在这种胶袋自然不多了,当它们变成了艺术品材料,甚至整个展览的墙、床和剪纸都用了这个材料,这是怀旧?这是批判?这是创新?梁秉钧写了《红白蓝》的诗,“红红红烈日下褪色/白白白话愈来愈少/蓝蓝蓝老在灰尘里”,在对于“红白蓝”各自命运书写的同时,也提出了疑问:“可否重组红蓝红蓝可否可否/裁剪蓝白蓝白成为新的衣裳?/说出说出白红白红新的语言?”无疑从过去的工具到消失的记忆,再在艺术中复原,梁秉钧在诗中提出的问题在展览中变成了回答,而且他们还将“香港2,3事”的诗歌和映像,都剪裁成了红白蓝胶布,最后展示出来成为艺术展的一部分,这就是梁秉钧所说的《红白蓝示范单位》。
以艺术为示范,红白蓝终究是艺术的符号,装置艺术也罢,行为艺术也好,在某种程度上被抽离出来而艺术化也正是文化际遇的形象表达,或者很多成为记忆的东西只能在这一层面上能够复活,它已经无法融入真正的生活,无法成为日常叙事,甚至更多了一些遗憾。所以梁秉钧的对话最后不得不回到物本身,回到蔬菜本身,“带看你的文稿经过查尔斯桥/想今天该买什么菜”,在《为叶辉的食经写序》中,梁秉钧把叶辉的文稿又变成了一道道美食,“用筷子拨动晴雨山水/从热汤里可以看见云霞/什么时候再共赏一尊好酒/细论嫩芯的茄子老去的黄瓜?”这也是一种回归,而这种“用筷子拨动晴雨山水”的回归不正是对食物的尊重?写诗和做菜、艺术和烹饪,不是同为品味?不是一样咀嚼?不是同样对平庸的拒绝?“避开庸手自煮满桌的新味/细爵散文的厨艺与诗的火候/让我从劳帮忙细切葱蒜/带出你调理的真味?”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59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