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08-30《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六次讲座》:触及的只是一个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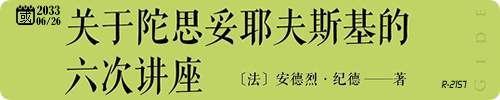
无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物多么具有代表性,我们却从来看不到他们脱离人性,而成为所谓的象征。
——《在老鸽棚剧院纪念陀思妥耶夫斯基诞辰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纪德想要写的那部《陀思妥耶夫斯基传》终于没有完成,战争是他无法实现夙愿的一个原因,按照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和《米开朗基罗传》的榜样来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传,纪德其实就是想把他从“最伟大的一位”小说家还原为一个人,一个疾病缠身个、贫困交加、终日劳累、为生活所迫、又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三年苦役的人,“人们期望找到一个神,但触及的只是一个人”。在某种程度上,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阅读,就必然会从两个方面入手,一个是他作为一个人的存在,另一个则是他创作的伟大小说,个体之存在和小说之存在构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双面文本,而对纪德来说,不管哪方面,都体现了一种人性,而不是象征,不是典型,“他们始终是个人,跟狄更斯笔下最有特点的那些人物一样特殊,与任何一种文学中的任何一个人物肖像一样,被描绘得同样有声有色。”
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信集》的解读,是基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个体经历而言的,纪德说是在“为他画一个肖像”。这个肖像当然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疾病,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因放荡生活而还债的拮据生活,有他因彼德拉舍夫斯基事件而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苦役经历,有他后来娶了寡妇玛利亚·德米特里耶夫娜·伊萨耶娃的安定……本身和别人进行通信就能看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活的原生态,纪德在这些书信里的确看到了一个真实、具体的人,而和他创作的文学作品不同,纪德认为他的书信是“糟糕的书信”,“这些书信的文本通常很混乱、笨拙而又欠通顺”,而且按照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的说法,“对写信感到一种可怕的、无法克服的、难以想象的厌恶”,“信是一种愚蠢的东西,根本不可能用来倾诉什么”,但也许正因为书信呈现了更本真的个体,纪德从这些信件里看见了更多人性的流露。
在书信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发出了呼喊,“他精疲力竭,他请求,不,是呼救……这是一种哀号,无止境的、单调的哀号。他的请求既不巧妙,更缺乏自尊和嘲讽。”疾病、贫困让陀思妥耶夫斯基几乎成为了“处于绝望状态中的写信的绝望的人”,在他五十岁的时候他写道:“我一生都在为金钱写作,我一生都在穷困潦倒中度过;而眼前比任何时候都更穷。”虽然是绝望状态中的绝望的人,但是在面对苦难时他又爆发出坚韧的生命力,在28岁即将发配去西伯利亚时,他写道:“现在我知道,我身上原来储备着取之不尽的生命力。”结束苦役生活,他娶了伊萨耶娃,“现在,已经不像以前了,在我的工作中充满了那么多的思考,那么多的努力,那么多的活力……”他还回顾了这六年的经历,认为自己虽然带着无比的痛苦,但是有更多的活力和勇气来斗争,“算了吧,没有人知道我的力量有多么大,我的才能有多么高,而我靠的正是这些!”
纪德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信并非是和创作的文本毫不相干的,甚至书信中的这一肖像为解读他的作品创造了条件。陀思妥耶夫斯基经历了疾病、贫困、流放,但是他对生命的执著表现的是他的乐观主义和网窝精神,陀思妥耶夫斯基喜欢引用泰伦乌斯的话,“人没有权利回避和忽视世上的一切,在这一点上,存在着最高的道德理性:Homo sum, et nihil humanurn,等等。”引用的这句话的意思是:“我是人,人类之事没有不关乎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把自己当做一个人类之中的人,把自己经历的事看成是人类之事,这恰恰是要在个体的偶然性中寻找关乎人性的必然,恰恰要在持续不断地苦难中找到“天性中的一种秘密需求”。一方面,他的那些书信是糟糕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似乎更适合在小说中“谈论别人”,但其实纪德从他文理混乱的书信中看出了流动的思想,而且是“一下子同时涌出来”,“表达时肯定要擦伤自己,同时也会把一切都钩破,而这混乱的一大堆,一旦被掌握,就将服务于他小说结构的有力的复杂性。”另一方面来说,小说似乎在写他人“谈论别人”,又恰恰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真心的流露,在某种程度上,纪德把他所创造的文学奇迹归结为:
他的每一个人物——他创造了整整一大批人物——首先是依据自己才存在的,这些富有内涵的人物的每一个,都带着各自特殊的秘密,为我们展现了他们复杂的内心问题;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奇迹还在于,他的每一个人物所体验、所经历的,恰恰正是这些问题,我或许应该说,这些问题恰恰是依靠了每一个人物才得以存在的——这些问题互相碰撞,互相斗争,形成了人的模样,然后在我们的眼前走向死亡,或者走向胜利。
| 编号:E38·2250804·2333 |
书信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展现最本真自我的文本,而他的小说则是思想最丰富、最富有生命力的文本,由此构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双重文本。当然,纪德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画肖像,更是为了从他身上找出法国文学界乃至欧洲文学存在的问题,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保守派但不是传统主义者,是保皇派又是民主派,是基督徒又不是罗马教廷的天主教徒,是自由派又不是“进步分子”,矛盾的身份带来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问题”:“陀思妥耶夫斯基始终是一个人们不知道如何使用的人。”西方对他的误读,对他的贬低,对他的不解,正是这种“不知道如何使用”,纪德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深信的事一种“思想的综合”,就像他所说,“俄罗斯未来作用的特点,应该是在泛人类的最高层面上,而俄罗斯思想兴许将是欧洲在其不同的民族中持之以恒努力发展的所有思想的综合”,这是一种“人类普遍的同情心”,伴随它的是热情的民族主义,所以他真正反对的就是所谓的“进步主义者”,“那些政客,他们期待促进俄罗斯文化的进步,但不是通过民族资源的有机发展,而是通过仓促地吸取西方教导”。那么,法国文学乃至欧洲文学是不是应该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肯定和否定、坚持和反对中窥见不是作为象征的人性力量?
《在老鸽棚剧院纪念陀思妥耶夫斯基诞辰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是1912年纪德发表的讲话,第二年在学术研讨会上又重新宣读了这篇讲话,在开篇时纪德就指出了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误读,“为什么如今还有人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杰出作品那么反感。因为,要战胜一种不理解的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它看成是出自真心的,并努力去理解它。”在他看来,法国人创造出了对于人性解读最好的作品,比如帕斯卡的《思想录》,比如波德莱尔的《恶之花》,它们是法国文学中“严肃而又孤独的作品”,但是在关于焦虑、激情、关系的问题,则完全留给了伦理学家、神学家、诗人,而没有小说家的位置,所以从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一位“所有小说家中最伟大的一位”身上,能不能找到对生命、苦难、人性的书写方式?能不能创造一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奇迹”?提出这些问题,纪德在接下来的六次讲座中深入解读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本,发现了其中的人性力量,如何从个体的具体性、偶然性中看见人类的普遍性,从真实的经历看见作品中的生命力,“他正是通过赋予人物以生命,才找到了他自己。”
“谦卑”是纪德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个关键词,它从书信中得到体现,1869年11月23日他写道:“他为什么会拒绝我呢?我根本就不是在强求,我只是在谦卑地恳求。”1869年12月7日他说:“我不强求,我谦卑地恳求。”1870年2月12日他写道:“我发出最谦卑的请求。”而在作品中,谦卑更是成为他塑造人物的一种普遍性格。一方面,纪德认为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谦卑就是他的性格,“的确,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从来没有过矫揉造作,也没有过装腔作势。他从来不把自己看成是一个超人;再没有比他更谦卑、更富人情味的人了;我甚至认为,一个高傲的人实在是无法完全理解他的。”另一方面,谦卑和道德有关,和心理有关,和痛苦、罪以及忏悔有关,而这就体现了俄罗斯人的宗教和感情,《白痴》中梅什金公爵四次路遇就写到了这种宗教感情:“我们不能把宗教情感的实质归属到任何推理或无神论中去,它与任何的罪行和错误都毫不相干;这里有别的东西,永远会有别的东西;这里有一些无神论永远也说不对头的东西。”正是这种“别的东西”才是俄罗斯人的信念,才是俄罗斯人的特殊使命,那就是谦卑:谦卑不是侮辱,“谦卑打开了天堂之门,侮辱打开了地狱之门。”谦卑者也和高傲者截然相对,高傲者最聪明,他们却被傲慢之魔缠住,永远陷入在斗争之中,所以,“最卑贱者比最高贵者离天国更近。”
谦卑是一种自愿的屈从,是被自由地接受的,纪德从谦卑看见了《福音书》中的真理,“自甘谦卑者,必高扬。”而在西伯利亚的时候,陀思妥耶夫斯基遇到的女人就给了他一本《福音书》,在监狱里陀思妥耶夫斯基阅读《福音书》,“他后来所写的所有作品,全都渗透着《福音书》的教理。”谦卑指向生命的通达,指向自由的高扬,这就表现为某种坚韧和乐观,“他的人物毫不顾及性格的一致性,他们乐于向其天性尚能容忍的一切矛盾、一切否定面让步。”这种对矛盾的乐观、宽容态度,就是赋予了人物以生命力,而且是在双重性的撕裂中被赋予的,《罪与罚》中拉斯柯尔尼科夫的一个朋友就说:“人们真的会说,他身上有两种相反的性格轮流地表现出来。”
本身这种任性的双重性就体现着灵魂的复杂,纪德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将灵魂划分为不同的类层,首先是知识类的,它在灵魂中所激越出的是最恶劣的欲望,奸诈邪毒的成分就在这一层;第二类是爱欲类的,这是一个被激情的风暴劫掠一空的区域,虽然如此,人物的心灵却不为之所动;因为有一个更深的区域,爱欲无法搅合进去,它是“再次诞生”的区域。三个层面互相渗透,而最深层次的区域不是心灵的地域,而是心灵的天堂,这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思想的“神秘中心”,纪德从《福音书》中找到了这个中心的启示关键词,那就是“Et nunc”,意思就是“从现在起”,“个体通过放弃个体性而取得胜利:谁若爱自己的生命,若保护他的个性,谁就将失去它;谁若放弃自己的生命,将使它真正地活着,将保证他有永生;不是未来中的永生,而是从现在起的永生。”“从现在起”回答的是“一个人能做什么”的问题,一方面它是一个无神论的问题,是在对上帝的否定中引入了对人的肯定,《群魔》中说:“没有上帝吗?那么……那么一切都是允许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写道:“假如上帝存在,一切便取决于他,我不能做任何有违他意愿的事情。而如果他不存在,一切便取决于我,我必须肯定我的独立性。”而另一方面,“从现在起”的真正意义是思想,是思想的行动,伊凡·卡拉马佐夫、斯梅尔佳科夫、斯塔夫罗金,思想促使行动,思想在行动中接近上帝,“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
“从现在起”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福音,永生不在未来而在现时,永生不是上帝存在而是在魔鬼参与中,永生是从苦难的深渊中跃起的行动,就像自杀的基里洛夫,“但是我会表现出我的独立。我必须相信我是不信神的。我将开始,我将结束,我将打开门。我将拯救。”而回归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个体生命,癫痫又怎样?苦役又怎样?为生活所迫又怎样?“我将开始,我将打开门”亦是他“从现在起”不断行动的见证。所以纪德在分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苦难经历、永生思想之后,在解读了书信中的自我和作品中的人性之后,在阐述了谦卑的性格和生命的力量后,讲座又回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问题”之中:“陀思妥耶夫斯基要把我们引向何处?他到底教导了我们什么?”而这个问题也恰恰是纪德在“谈论别人”中回到自身,“俄罗斯在以基里洛夫的方式作自我牺牲,而这一牺牲,兴许还有助于拯救欧洲的其他国家,拯救人类的其他民族。”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47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