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08-31《马丘比丘之巅》:让时间完成它的高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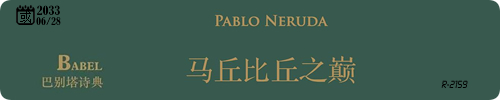
你们会问,为什么他的诗歌
不与我们谈论梦境,谈论枝叶,
谈论他故国的宏伟火山?
——《我来解释一些事》
诗歌不谈论梦境、枝叶和宏伟火山,诗歌里也没有丁香的味道,没有虞美人的形而上学,没有填满了孔洞和鸟雀的雨水,在“你们会问”的疑问中,聂鲁达用“我来解释一些事”来回答:因为街上到处是鲜血,“请你们来看看街上的血,/来看看/街上的血,/来看看街上的/血!”血从何而来?从“一切都在燃烧”开始,火堆钻出地面、吞噬生灵,火便成为了血;火是谁来点燃?是那些强盗,开飞机的带着摩尔人的强盗,带指环的携公爵夫人的强盗,正在祝祷的黑衣修士的强盗,他们从天而降杀害了儿童,于是街上血流成河,“连豺狼都会拒绝的豺狼,/干刺菜咬一口也要吐出来的石头,/连蛇蟒都会痛恨的蛇蟒!”
从疑问到回答,从解释到悲剧,聂鲁达讲述了“我身上发生的一切”,这是一个从美好到罪恶的世界,我的家曾被唤作鲜花之屋,到处都是怒放的天竺葵,美丽的房子里有狗也有孩子,但是一切都被摧毁了,连同诗歌。当聂鲁达讲述身边发生的一切,他也在对死去的“兄弟”讲述,而这个兄弟就是西班牙诗人、剧作家、散文家加西亚·洛尔迦,作为“27一代”的重要成员,洛尔迦也吟咏了生活的美好,也描绘了和睦的家庭,也把梦境、枝叶和宏伟火山当做诗歌的主题,但是,他的诗歌连同生命也在流血的土地上死去:1936年,洛尔迦被发动政变的国民军杀害,“叛徒/将军们:/看看我死去的家吧,/看看破碎的西班牙”,当“叛军”制造了破碎的西班牙,对于洛尔迦的某种哀悼也是对于诗人的哀悼,对于流血西班牙的愤怒也是对于秘鲁这片土地的愤怒,对于“第三居所”的感情也是对于祖国的感情,“费德里科,你在地下/可曾记得,/你可曾记得我的有阳台的家,记得那里/六月的日光曾将鲜花淹没于你口中?”
对于诗人、罪恶、居所的同一性,也是对于愤怒、战斗和新生的同一性:每一个死去的家中都会长出金属,每一个西班牙的孔洞都会长出西班牙,每一个死去的孩子身上都会长出带眼镜的步枪,而每一罪行也都会长出复仇的子弹。“第三居所”选自聂鲁达写于1936年至1937年的组诗《西班牙在我心中》,而实际上在洛尔迦被杀害的前一年,聂鲁达出版了他的另一部诗集《大地的居所》,其中就有一首写给“兄弟”的诗:《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迦颂》,这是一个面对死亡之河哭泣的斗士,这是一个属于蝴蝶的年轻人一样的自由灵魂,这是一个戴上桂冠的诗人,同样,在对诗人的赞美声中聂鲁达一样发出了拷问:“如果不为晨露,诗句该为何而生?”这是一个关于诗人何为的使命性问题,它同样面对的事灾难、罪恶和鲜血之下的这片土地,同样唤醒的是经历痛苦后站立起来的人,“假如我可以在一栋孤宅里因害怕而哭泣,/假如我可以抠出双眼并将它们吞吃下去,/我便一定这样做,为了你哀恸橙树般的嗓音,/为了在诞生时发出吼叫的你的诗句。”
这无疑是诗歌和诗歌的共鸣,诗人和诗人的对话,无疑指向“诗句为何而生”和“诗人何为”的问题,“生活就是这样,费德里科,在这里你拥有/我,这个忧郁的阳刚男子的友谊”,当然兄弟般的情谊所立足和战斗就是同一片土地——“大地的居所”。诗集出版于1935年,那时的洛尔迦还活着,但是已经完成了《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的聂鲁达,完全从情诗的缠绵中走出,即使唱出的是“绝望的歌”,爱情的坟墓里依然能看见燃烧着的火焰,“被鸟雀啄咬的串串果实仍在炽烈烧燃。”但是在《大地的居所》中,爱情的缠绵和绝望已经被死亡的压抑所取代,《大地的居所》也成为聂鲁达面对死亡最晦涩的诗集,它如疾驰的火车扑面而来:
如灰烬,如漫涌滋衍的海,
于下沉的迟缓,于一片无形混沌,
或如在道路高处听到
十字交错的钟声
荡着已脱离金属的声响,
困惑着、沉重着,以被记住的
或不被看见的杳渺方式,
在同一磨坊里,幻化为尘,
而滚过地面的洋李弥泛清香,
在时间里腐烂,恒久青绿。
——《死去的疾驰》
生机盎然的一切,在迅猛的死亡之中宛如马达之轮转,疯狂地吞噬一切,它是暴风雨的黑色行动,它是汪洋般广博的无序,它碾碎了一切的时间,“我默然工作,环绕自己,/如盘旋于死亡上空的渡鸦,哀丧之鸦。”(《聚合》)但是,死亡带来的是停止,也是感知,是死亡,也是新生,“大地的居所”所具有的意义是关于命运的二重性:它在土地之上诞生而成为居所,它又在死亡之中埋入土地——如每一株植物,在生生死死中构建“土地的居所”:“复日圆环内,、硕大的笋瓜伸展动人的/枝叶,侧耳倾听:/那些,那些反复求索的,/那些饱满的,因沉重液滴而晦暗。”聂鲁达在这大地的居所中看见了生命的矛盾,“我的造物诞生于绵长的拒绝”,也看见了一种转化的可能,“一种休憩中的元素,一汪生机盎然的油:/一只不可或缺的鸟儿看护我的头脑:/一位恒常不变的天使居于我的剑端。”
| 编号:S64·2250804·2334 |
(《味道》)在《货船幽魂》中,它就表现为一种关于轮回的时间性,“幽魂用没有眼睛的脸看着海:/白日的轮回,货船的咳喘,空间中/唯一且浑圆抛物线上的一只鸟。”沉没的货船到处是死去的幽灵,它们沉寂在时间内部,但是一只鸟的轮回又“降落回货船的生活”,在死寂的时间和朽木中,如迟缓的空气“滑过黝黑的厨房与船舱”。
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诗人“诞生”的启示录,“现在的情况是我厌倦了做人。”这就是一种死亡,在“大地的居所”中安睡,“独居地下,如与死人为伴的地窖,/在冻僵的躯壳内伤心欲绝。”(《游荡》)但是大地的居所同样提供了土地和养分,“向下,在大地潮湿的脏腑/吸收、思考,终日进食。”一个“游荡”的魂灵,只有让灵魂“深入林木”,才是一次新生:坠入阴影之中,被摧毁的事物环绕,撕扯下“一磅一磅的潮湿”,行走在丧葬旅程之中,之后便是梦境的降落,然后是破裂的羊水,然后是诞生——一切都是在死的意义上开启,是死的完成中醒来,“让我们点起火,造出安静,发出声响,/让我们燃烧,沉默,阵阵钟声。”对洛尔迦的颂歌无疑是聂鲁达从“大地的居所”的二元性中认识到了诗歌的使命,也从诗人洛尔迦真正的死亡中寻找到了更具视野的诗人之诞生:从压抑和阴暗的死亡中钻出泥土,看见的是新的大地,是新的世界,是新的西班牙,是新的秘鲁,而且新生之诞生,是立于挺拔的高度,是对土地的俯视,是“马丘比丘之巅”上的放歌。
马丘比丘,位于秘鲁库斯科省西北,是秘鲁著名的前哥伦布时期印加帝国在15世纪建造的遗迹,也是世界新七大奇迹之一,马丘比丘在克丘亚语中即为“古老的山脉”,也被称作“失落的印加城市”。马丘比丘遗址高耸在海拔约2350米的山脊上,作为是南美洲最重要的考古发掘中心,聂鲁达站在“马丘比丘之巅”所要完成的是对于地理、文化、历史的命名,它就是从生命之新生的“大地的居所”变成了以高度照亮世界的“大地上的灯盏”,而这盏灯能成为大地上的标志,就在于它有着永远不死的种子,“人用被白雪冻伤的手指/抚摩着种子。”(《人》)在漫长的时间之河里,人摧毁了山巅,人也用冻伤的手指抚摸着种子,这是人和马丘比丘建立的关系,但是独属于马丘比丘以及“马丘比丘之巅”的又是怎样一种诞生?在组诗《马丘比丘之巅》里,聂鲁达重构了在时间中淬炼的马丘比丘之历史,而这也正是一种人的死亡、诞生和高耸的过程。
“鲜活明耀的日子,在风雨无常的/身体里:化成/寂静浓酸的钢:/被撕成粉末的夜:/新婚祖国被蹂躏的雄蕊。”身体被撕碎成粉末,它却埋入了“大地生殖力最强的所在”;当生命呈现出一种下沉状态,它所沉淀的却是“永恒的矿脉”;而生命的悲苦,就像是每次饮下的黑浆——这些都是时间中必须经历的死亡:
当人们逐渐开始拒绝我,
慢慢锁上通道和门窗以免
我清泉般的双手去碰触他不存在的伤,
我便转身来到街和街,河与河,
城市与城市,床铺和床铺,
我咸涩的面具穿过沙漠,
在最后几间卑微的屋宅中——没有灯,没有火
没有面包,没有石头,没有寂静,孤身一人,
我因自己的死滚落向死亡。
死滚落向死亡,却也打开了灵魂的缝隙,它是生命的另一个进口,是时间的另一种开始,是大地的另一段高度,“山石的母亲,康多兀鹫的泡沫。/人类曙光高耸的礁石。”如同人类一样,“你们曾是的一切都坠落了:种种习俗、被磨损的/音节,散发耀眼光芒的面具。”石头还在,词语还在,生命还在,“人类曙光之巅:/装载着寂静的至高容器:/那么多生命之后石块的生命。”它是文明的象征,那个叫“亚美利加”的文明就是“我的爱”,“请同我一起上来,亚美利加,我的爱。”一起从陡峭的夜站立起来,抵达黎明,望见兀鹫,展开高度,星辰的飞鹰、失落的堡垒、繁星的腰带、庄严的面包……这一切都构成了“石头”的叙事,它们是石头的花粉,是石头的面包,是石头的玫瑰,是石头的源泉,是石头的书籍,是石头的光,石头就是世界,石头就是历史,石头就是生命,“我的爱,我的爱,不要去碰触边界,/也不要仰慕被淹没的头颅:/让时间完成它的高度/在它破碎泉源的沙龙。”
当马丘比丘将“石头放入了石头”,所完成的就是时间中的高度,它是属于石头的叙事,但是聂鲁达在石头的叙事中所提出的是另一个问题:人在哪里?“石头曾在石头里,人,曾在哪里?/空气冒在空气里,人,曾在哪里?/时间曾在时间里,人,曾在哪里?”石头放入了石头,而在这片土地上,和石头一起被放入的还有碎步,还有泪水,还有鲜红的血滴,还有亚美利加,“还有,还有,被埋葬的亚美利加,在最深处,/在最涩苦的脏腑,你是否,如一只鹰般,保留着饥饿?”对人的发问,对亚美利加的命运的关注,聂鲁达在“马丘比丘之巅”所看见的是另一处“大地的居所”,所构建的是另一种大地的诞生,“请给我安静、水、希望。/请给我战斗、铁、火山。/用你们的身体粘住我的身体如同磁铁。/来吧,钻进我的静脉我的嘴。/说吧,透过我的词语我的血。”
这些大地之上有更多的兄弟,“兄弟,请上来同我一起出生。”他们是维拉科查之子胡安·凿石者,是绿星之子胡安·食寒者,是松石之孙胡安·赤脚者,之所以“胡安”是一起出生的兄弟,就是因为,“胡安是我用来赴死的名字。”也由此,聂鲁达从“马丘比丘之巅”看见了更广阔的土地,更悠远的时间,它们是在兄弟的死亡和诞生中连接在一起,它的名字就叫“亚美利加”,诗集《漫歌》便成为聂鲁达在时空意义上对“大地的居所”的一种命名。在时间和空间的“漫歌”中,有着《征服者》,他们是“睡着的战士”,拥有“贝尔德兰·德·科尔多瓦”这样的普通西班牙姓名,作为征服者最后也“倒在了藤蔓与叶片间,/倒在了覆羽的大神脚下”,是西班牙殖民者《希梅内斯·德·克萨达》,他发现了新格拉纳达即今哥伦比亚的“发现者”,“他们已经进入密林:/已经开始劫掠、开始噬咬、开始杀戮。/哦,哥伦比亚!请捍卫/你神秘红色雨林的面纱。”“殖民者”更是以“红线”伸进了“秘鲁的灵魂”。在这片土地上,也有“解放者”,中美洲阿兹特克帝国末代统治者夸乌特莫克扯起解放的大旗,“你的旗帜上没有任何阴影”,但是“一只冷酷的手如石化的世纪/扼住了你的喉咙。”在对西班牙殖民者的抵抗中被俘,最后受绞刑而死,“如一位令人心痛的见证者,/直到一根粗绳缠住/纯洁之柱/并将他的躯体悬挂/在这不幸土地的上空。”(《夸乌特莫克(1520)》)在亚美利加的土地上,更有“逃亡者”,他们是在江河边生活的人,在火山下生活的人,在铜矿的硫磺阴影下生活的人,是渔民和农夫,是蓝色印第安人,是反复钉补皮面的制鞋匠人,而他们也是“所有人”,“我属于、感激、赞颂所有这些人。”(《对所有人,对你们》)
征服者、发现者、解放者、逃亡者,构成了这片土地的“所有人”,他们离开他们回来,他们征服他们反抗,这就是“亚美利加”永恒的故事,聂鲁达在把自己放入“所有人”行列,就是在这种永恒中回答诗人何为的问题,这是一个关于土地的宏大问题,却也是关于个体的选择问题,“一切都是我的黑夜,一切/都是我的白昼,一切/都是我的空气,一切/都由我经历、挨受、高举、消灭。”而个体之所为也将构成土地之所有:
梦中我被广阔的黏土环绕,
活着时顺我的手,有
丰沛的泥土涌流。
我喝下的亦不是美酒而是泥土,
隐藏的泥土,我口中的泥土,
轻负朝露的农业的泥土,
明耀豆荚的疾风,
谷粮的品种,黄金的粮仓。
——《亚美利加》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50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