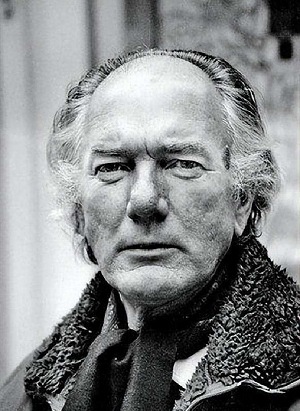2025-08-31《波斯女人·制帽匠》:粗暴地奚落了人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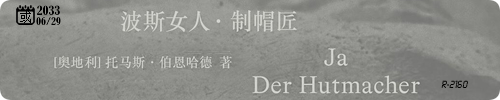
人们做的事情,很多都是错误的,他说,几乎人们做的一切都是错误的,如果深思熟虑地动脑子想,人们所做的一切都是错误的。
——《制帽匠》
这是鞋帽匠对住在隔壁的律师“我”所说的话,两天后,我从报纸上得知,有一个人从四层阁楼上载下来自杀身亡,“自杀者是个制帽匠。”鞋帽匠是从四层的阁楼上载下来,却是一次自杀,为什么两天前还在对我说起家里的事的鞋帽匠会突然选择自杀?他所说的“错误”并非是导致他自杀的原因,罪魁祸首是在他说完“错误”之后所说的“不幸”,“可能不幸特别看好我这个人。”错误是属于人们的,它不意指某一个人、特殊的人,而不幸却属于个体,当不幸降临,在无法逃避也无法解决的情况下,唯有自杀才是对错误和不幸的解脱。
但是对于制帽匠来说,他所遇到的事的确是错误,但也不能说是不幸,甚至只是一件生活中的小事:他一辈子就是制帽,生了个儿子,也继承了制帽这门手艺,“我十七岁时已经掌握了制帽技术,我的儿子像我一样,也在十七岁时满师出徒。”而且在制帽匠看来儿子天生就是制帽的灵工巧匠,因此家族的手艺变成了远近闻名的精品帽店,还出口世界各地。这本是一件家族的荣光,也是家庭的幸事,但是儿子却和一个不好的女人结婚了,之所以不好,就在于儿子不再属于他,不再听他的话,结婚后他们好几个月没有碰面,“这就是问题的根源,我的愿望是怎样的呢,我总想,我的儿子要么不结婚,要结婚,那应该是带来幸福的婚姻,可是随着这个儿媳的到来,我们家就交上了厄运……”制帽匠把这桩婚姻看成“不幸”,而且不幸也延伸到了他的身上:结婚后儿子生了孩子,就劝他从二楼搬到了三楼,后来又生了孩子,直到第四个孩子马上要生,他们让他搬到四楼。从一楼到二楼再到四楼,制帽匠不停搬家,是因为属于自己的空间不断被儿子占有,不断被儿子背后的女人占有,不断被儿子和女人所生的孩子占有,本来制帽匠也可以做出牺牲,但是四楼根本不适合人居住,“那些不宜人居住的小房间,低矮狭窄,以前可以安排仆人住在那里,今天连仆人你也不能让人家在那里住了,人家会因为条件太差而跑掉的……”
连仆人都不住的四楼,却让制帽匠去住,制帽匠认为不幸不是地位的下降,不是生活条件的改变,而是属于自己的东西一件一件被拿走了,“生意再好,店铺再兴旺又有什么用,一切都没有意义……”但是即使如此,一个制帽匠也不至于在生活中没有遇到过比这更大的困难吧,在他看来这也是一个“说它复杂是特别复杂,说它简单也简单得很”的家庭琐事,即使是错误,甚至是不幸,怎么让他义无反顾地选择了自杀?制帽匠自杀身亡,同样选择的还有《波斯女人》中的波斯女人,做科研的“我”在莫里茨那里遇到了瑞士人和他的伴侣波斯女人之后,他们有过两次散步以及几次交谈,后来好久没有波斯女人的消息了,在我生日后的一天偶然读报纸时,就读到了一条报道:一个外国女人在米尔地区“扑倒在载有数吨水泥的大货车轮下”,按照莫里斯的说法,整个人被货车碾得粉碎,“惨不忍睹”,而且在瑞士伴侣并没有处理后事的情况下,波斯女人被草草埋在了林茨市公墓的竖井式集体墓穴中,“莫里茨,在波斯女人下葬只过了两周后,向有关的公墓管理处询问,已无法得知具体埋在哪一处墓穴里。”
| 编号:C38·2250720·2332 |
制帽匠因为被搬到了四楼而选择自杀,波斯女人朝向水泥货车而自杀,两个人选择了同样方式告别这个世界,《波斯女人·制帽匠》两篇合在一起的小说,就是合在一起的死亡,死亡看起来是如此轻易地发生,但是托马斯·伯恩哈德不是说过:“想到死亡,一切都是可笑的。”制帽匠和波斯女人的死,难道也是一种可笑?他所说的“可笑”意味着什么?当一个人选择自杀结束生命,一定是勇气的表现,甚至是一种向生而死的决然,但是无论是制帽匠还是波斯女人,他们最后自杀,一定不是勇气,而是没有勇气,没有勇气面对错误的人生和不幸的生活,没有勇气再忍受不公和痛苦:对于制帽匠来说,四楼之后也许还会将他赶出房子,连最后的自尊之地都不将拥有,所以从四楼载下去也是保留了最后的地盘;而对于波斯女人来说,情况似乎更为复杂,但是自杀也变成了无法活下去的必由之路。
波斯女人出身于民你们王族,家族属于伊朗上层社会,她自幼接受了良好的教育,还在英国和法国上学,认识了瑞士先生之后,她为他开辟了业务上的很多道路,他们也在世界各地游历,一直生活在温暖、阳光充足的地方。但是当他们渐渐老了之后,瑞士先生越来越频繁违背波斯女人的意愿,甚至他肆无忌惮的我行我素让人匪夷所思,就是在和我第二次散步时,波斯女人说她的余生会生活在失望和沮丧之中,因为瑞士先生“粗暴地奚落了她的人生”,她只能实施自我毁灭的过程,“瑞士先生,她的生活伴侣,她说,憎恨她拿他的事业前程做赌注,她的原话如此,在公墓和树林后边建造了这座房子,为的就是要摆脱她。”他们找到莫里茨要买墓地后面的那块地作为居所,不是别的,真是为了在她快六十岁的时候离开她、抛弃她,这块地根本无人问津,就像墓地一样阴暗,而瑞士先生这样做就是给她选择了墓地,所以,“她所接触的人太让她厌恶了,与人打交道太让她失望了,让她在失望中成为孤家寡人。”我曾经以的肆无忌惮的方式问她,“她是否有一天也会自杀”,波斯女人听完我的话笑了起来说,“是的。”
|
| 伯恩哈德:想到死亡,一切都是可笑的 |
所以波斯女人似乎和制帽匠一样,因为家庭的琐事而无法再忍受孤独、痛苦和逐渐丧失了尊严的生活,最终选择了自杀,但是这里依然有一个问题,家庭生活造成的困境让他们无法摆脱,以结束生命的方式结束这种痛苦,代价是不是太大了?或者说,伯恩哈德创造了一种夸大的死亡?在两部短篇小说中,伯恩哈德似乎在表达他的死亡观,当他说出“想到死亡,一切都是可笑的”这句话的时候,是在1968年奥地利国家文学奖颁奖仪式上,伯恩哈德是获奖者,致辞中他表达了对死亡的嘲笑,更是批评了奥地利,说“国家注定是一个不断走向崩溃的造物,人民注定是卑劣和弱智……”结果在场的文化部长拂袖而去,各界名流也相继退场。他从1970年代中期开始公开宣称不接受任何文学奖项,据说他曾被德国国际笔会主席两次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伯恩哈德也明确表示如果获得此奖他将拒绝接受。
“想到死亡,一切都是可笑的。”伯恩哈德表达了死亡观,更是为了批评了社会,他对死亡的嘲笑就是对造成死亡的社会的讽刺,而在《波斯女人》而和《制帽匠》这两篇小说中,自杀身亡当然也成为伯恩哈德对社会嘲讽的一种表达,这也使得他被称为灾难作家、死亡作家、社会批评家、敌视人类的作家的原因所在,所以在另一个意义上,这两篇小说写的是波斯女人之死和制帽匠之死,但还有第三种死亡,那就是我之死——伯恩哈德就是在死亡叙事中完成对社会的死亡批判,“我”是死亡的听说者,也是死亡的探索者。在小说中,我都是自杀事件的见证者,但是这种见证非常奇怪,波斯女人和制帽匠自杀的消息都是我从报纸上读到的,死亡被印成了文字,变成了一种公开的报道,进入了公众视野,我当然是作为其中的“读者”而存在的,在这个意义上,我就是社会的一部分,我是死亡的旁观者;但是我住在制帽匠的隔壁,当制帽匠从四楼自杀,我应该能听到响声,甚至可能是在场者,同样波斯女人也曾和我散步聊天,共同喜欢音乐和哲学,讨论舒曼的音乐和叔本华的哲学,两个人比波斯女人和瑞士伴侣走得更近,因为他们甚至都保持着沉默,而且我也曾问过波斯女人关于自杀的问题,我完全能够察觉出波斯女人的情绪变化,甚至波斯女人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还会向我倾诉,但是她还是选择了自杀——仿佛波斯女人和制帽匠远离了我的存在,他们的自杀是在绝对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做出的。
这是社会隔阂的体现,这是人们“错误”做事的原因,这也是个体不幸的隐喻,“现在我知道了,我们许多年甚至数十年从一个人身旁走过,却不知道这人是谁,现在我知道了,我二十年之久从一个人身旁走过,到头来却不知道他是谁。”在这个意义上,我的存在注解了这个冷漠的世界,这个不幸的社会。但是在另一个方面,我的见证正说明我也是他们中的一员,社会对我的压抑和异化也使我必然走向死亡这一步——他们只不过是先行一步的影子,而这种被社会异化而决然的态度,也正是伯恩哈德的社会观:拒绝接受社会的荣誉,保持和社会的距离,否定社会的规则,甚至批判国家、权力、制度、秩序等既在的一切,“只有真正独立的人,才能从根本上做到真正把书写好。”
没有任何分段的《波斯女人》就像是死亡本身,它压抑着生活,它让个体不断扭曲:我是个科研工作者,写了几百封寄给朋友、熟人和科研工作者的信,但没有一封寄出,我就是一个完全不和人来往的人,“我实际上是有意识地这样做,疏远所有与我能做思想交流的人,最后完全将自己封闭起来,放弃一切与外界的交往,只保留着那种最必要的、所谓土生土长的联系”,所以我生活在孤立·、封闭的世界中,这不仅仅是一种个性体现,更在于变成了一种精神疾病,如果极端的话,无疑就是自杀。但是和自杀者唯一不同的事,我还在寻找一种出口,去找莫里茨,向他说出自己在精神上和情感上的疾患症候,一方面于我来说也是在一意孤行中把莫里茨当成发泄怨恨的对象,另一方面也是缓解自杀压力的办法。也就在那里认识了波斯女人,在和她一起散步后生活发生了改变,那就是一种真正的“交谈”,“我们默默地交谈,我们的谈话是一种可以设想出来的最热烈的谈话,说出声来的词语,为听觉组合排列着,是不可能具有如同沉默交谈这样的作用的。”
所以在这里,波斯女人的痛苦就成为了伯恩哈斯社会观的一种投射:喜欢舒曼的音乐,喜欢叔本华的哲学,这是生活在压抑、失望、沮丧中的一种释放,“每逢我要把阅读纯粹当作一种乐趣,一种全面洗涤自己心灵的乐趣时,我就拿它来读。”而另一方面,音乐和哲学,甚至和他人的交谈并不能彻底释放压力,这种压力来自个体,更来自社会,这就是“无政府主义”:
多年来我所观察到的对精神的敌视达到了新的高潮,统治者要求人民,或者更确切地说,要求民众去谋害精神,煽动他们围剿精神和头脑。突然一夜之间一切又在独断专行,数周、数月里我深受其害,亲身体会到人们如何在谋害有思想的人。那种把一切不适合于自己的都要铲除掉的平庸、狭隘的民众意识,尤其是在思想和精神方面占了上风,突然受到政府,不是个别的某个政府,而是欧洲所有政府的重视,为它们所利用。
这是我对波斯女人所说的国家和社会,作为个体,生活在这样一个充斥着暴力、阴谋和卑鄙无耻的世界中,只能选择和社会的隔绝,只能在封闭中活着,而波斯女人从名门望族到被瑞士伴侣抛弃,这也是社会症候给他带来的痛苦,所以她更走向了一种极端:她说,无政府状态是注重精神境界的人头脑中的一切;她说,无论是哪一个社会,都必须被推翻和废除;她说,这里的人恶毒、粗暴,这是个到处都危及个体、不人道的国家;她说,“如同我毫无希望,您也是如此,不管您逃避到哪里。您的科学是荒谬的,任何科学都是荒谬的。”把个体的问题归结为社会的原因,把个体的死亡也变成被社会扭曲的悲剧,在这个意义上讲,个体毫无希望的生活正是实践着整个社会的绝对荒谬,没有所谓的人生,更没有所谓的理想,没有人与人之间的爱,也没有相遇之恩、邻里之情,死亡在别处发生,死亡被写进报纸,就像一个笑话,“就把我当作一段插曲吧,权当您听了一个故事……”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46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