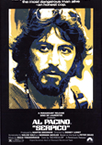2024-10-09《冲突》:只有行动者在行动

片名“Serpico”翻译成“冲突”,早就有人指出是一种误译,尽管电影的确表现了一种个人信念和规则甚至是潜规则之间的“冲突”,但是原名“Serpico”并不指向任何戏剧性冲突,它是主人公法兰克的名字,沙比高或者谢皮科。当西德尼·吕美特用名字来命名这部电影,这其中有着“立传”的思想,的确法兰克从一个移民到普通的警员,从警员到揭露警界贪污黑幕的英雄,就是一个重要人物的存在,甚至具有了扭转歪风的历史性作用——不仅那枚至高的“金色警徽”是对他惩恶扬善的褒奖,而且法兰克几乎用一己之力改变了美国警界的规则,在他的努力下建立了处理警察贪污问题的独立调查部门,而吕美特最后以介绍的方式也体现了历史人物的存在,“1972年6月15日,法兰克辞职,他获得了‘英勇过人’的荣誉勋章,现居于瑞典……”
片名和最后的介绍,都将法兰克置于历史名人的地位中,都把法兰克的故事变成了“扬名立万”的传奇,这种立传式的故事讲述凸显了一种真实性和高度,但是,吕美特的叙述却和在《突击者》一样,完全将主角变成了偏执型人格的体现,很多时候他们容易从动,易于愤怒,甚至丧失了最基本的理智,如果说《突击者》中的警察约翰逊是被20年的邪恶影响而导致了内心扭曲,最终走向了异化,成为了消灭罪恶的另一种恶者,至少吕美特在叙事上还是紧紧围绕约翰逊的异化过程展开,主题还是比较集中,而在《冲突》中,法兰克作为一个孤胆英雄,只身挑战权威,挑战规则,挑战制度,却完全是一种神经质的表现,尤其在叙事上,完全抛弃了前后逻辑的铺垫性运用,把法兰克仍在了无数次的行动中,最后只剩下了行动中在行动这样一个简单、机械式的叙事存在。
入职成为警员,法兰克的内心只有一个理想:惩恶扬善,这无疑让他从一开始就成为了一个理想主义者,当理想主义者面对复杂的社会环境,尤其是作为正义者代表的警察,面对罪恶,根本无法看懂发生的一切,更不要说适应,但是吕美特将他的这种理想主义赋予了力量,正是因为理想的存在,才可能向强大的恶势力发起冲击,并摧毁这个固若金汤的存在:一方面是警察对立面的坏人,这是警察的职责所在,而另一方面更为可怕和隐蔽,那就是警察内部的罪恶,贪污受贿无处不在,甚至有警察声称:“谁会相信不收钱的警察?”除了警察内部的罪恶,还有延伸出去体制内的包庇,这就是法兰克所说的“蛇鼠一窝”,从警长到局长到督长,再到市长,形成了一个环环相扣的利益链,当所有一切的恶变得司空见怪,仅仅靠一个人的力量如何引发地震,如何解构规则,如何打击罪恶?
| 导演: 西德尼·吕美特 |
在这个问题面前,吕美特就是将法兰克安全脱身出来,在出淤泥而不染中将他塑造成一个孤胆英雄,而孤胆英雄面对强大的恶势力,不怕牺牲,他所能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采取行动,于是从一个行动到另一个行动,法兰克一直在奔波,一直在努力,一直在斗争,当所有的情节几乎都在行动者行动这个单一叙事结构中展开,人物的丰满性、故事的因果性、叙事的逻辑性被弃置一旁,当抽离了这一切,最后只剩下了骨架,电影也成了为立传而立传的流水账。法兰克的行动就是惩处罪犯,从一开始面对外部的罪恶,他身先士卒展现勇气和智慧,街头打击强奸者是他立下的第一个功劳,而在案件破获之后他发现这只是表现,真正的团伙还没有落网,当他只身一人抓获了其他成员,却并没有获得应有的褒奖,反而认为他“擅离岗位”,被抓获的罪犯也被专案组带走,功劳自然归属于专案组的名下。
就是从这里开始,法兰克感觉到了警察局里丧失了最基本的公正,而且发现警察内部也存在着诸多问题,于是一方面是上级对他的连续打压,他从一个部门调到另一个部门,很多部门对他冷眼相待,甚至不接纳他,而另一方面,他发现警察的问题越来越明显,不仅和犯罪团伙有着利益关联,而且而和政府之间也存在着某种非法的勾结,所以他真正开始了行动,目标就是贪污已成习惯的第七组:他将上级和他的通话记录录音,他不断向督长报告情况,他深入犯罪团伙内部,他也加入小组搜集信息,在“蛇鼠一窝”的现实面前,他并没有放弃,而是积极寻找曝光的机会,制造舆论压力,使得警方成立调查委员会,而最后在扫毒行动中,法兰克的脑袋中了一枪,这样一次付出的代价终于引起了高层的关注,最后他获得了金色勋章,揭露了警察黑幕,并提出了建立独立调差部门的建议,这一问题才最终以制度化建设的方式得到了解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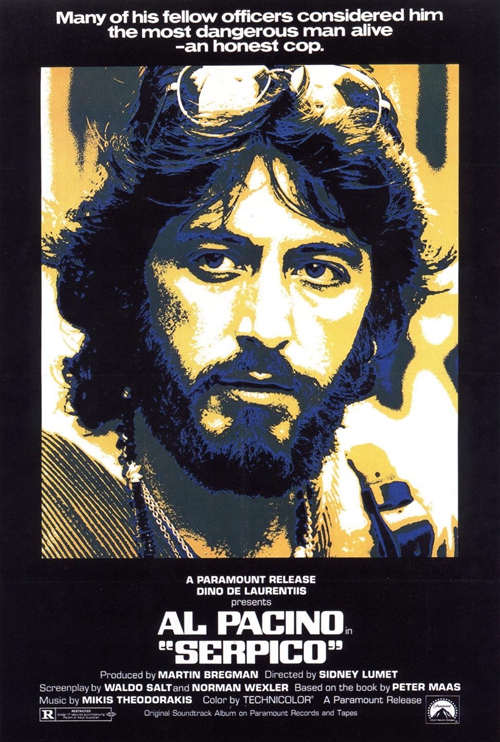
《冲突》电影海报
在法兰克的行动中,他的工作岗位不断轮换,他的工作任务不断更新,吕美特就不厌其烦地变换场景,而从一个场景到另一个场景,几乎在没有交代背景的情况下快速闪过,在镜头前,只是法兰克不断地奔跑,不断地追击,不断地斗争,这种几乎抽离了叙事的行动本身变得单薄,而那些和法兰克有关的人也似走马灯一般。在行动意义上,展现的是法兰克孤胆英雄的一面,但是人物的塑造也由此变得单一和机械,另一方面来说,法兰克为什么有惩恶扬善的信念,在各种打击面前他的信念为什么坚如磐石,其实才是电影需要交代的,但是吕美特显然放弃了:电影中有过法兰克入职时的仪式,在这个仪式上上司提到了警察的意义就是对抗罪恶,镜头扫到了法兰克,他的目光是坚毅的,这种坚毅体现的就是一种信念,就是一种理想,而在之后和女友萝莉在一起的时候,法兰克也说过当警察是自己从小就有的理想。对法兰克行动背后信念的交代,只有这两处,但显然,只是让这片言只语赋予法兰克坚如磐石的信念,未免太过简单:面对种种不利自己的舆论压力,法兰克为什么还会坚持自我?面对各种打压自己行动的强力,法兰克为什么从不妥协?在面对死亡威胁的时候,法兰克为什么还会做出牺牲?显然,入职时的“对抗罪恶”和从小立志当警察的理想,都无法真正回答这些问题,当吕美特放弃了回答,法兰克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由于缺少了情感、理性的支撑,所以变得不可信,甚至最后完全变成了偏执的个人主义者。
法兰克有过两任女友,一个是跳舞的莉施娜,另一个则是邻居萝莉,在法兰克不断行动中,他和她们的爱情当然更没有叙事,只是相遇相爱的快速演进,但是在法兰克的信念和她们的理念发生矛盾,法兰克的行动和她们的想法发生冲突,作为个人主义的法兰克根本不在乎他们的想法,莉施娜只想和他结婚过安静的生活,他没有答应,或者并不爱莉施娜,或者行动才是至上的,所以莉施娜离他而去。法兰克认识萝莉的时候,他正搜集揭露贪污的证据,在面对各种打压力量的时候,法兰克身心疲惫,但是他依然在坚持,而萝莉劝慰他,希望不要担惊受怕,没想到法兰克对她发火,不断重复着“滚”,最后萝莉哭泣着让他“自由自在去战斗”而离开——在吕美特的叙事中,爱情完全变成了行动的绊脚石,甚至法兰克的个人主义完全将爱他的人当成了泄愤的对象,于是个人主义走向了一种极端。
法兰克完全是一个偏执的个人主义者,他不在乎规则,他不向权威妥协,他听从内心的召唤,但是他同样不考虑他人的感受,他顾忌人心的复杂,更不会用智慧来解决矛盾,他单一的理想、单一的行动就像他留蓄的胡子,这是信念的象征,孤立、孤独而孤绝——当然,当最后法兰克“居于瑞典”并不是成功者的最后归宿,吕美特给了这个行动者最后寂寞的背影,在某种意义上,当抽离了一切人情冷暖,当个人主义在偏执中成全了理想,它也意味着失去,就像法兰克得到金色徽章时所说:“真有趣,是因为我是个诚实的警察?还是因为我面部受伤?”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31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