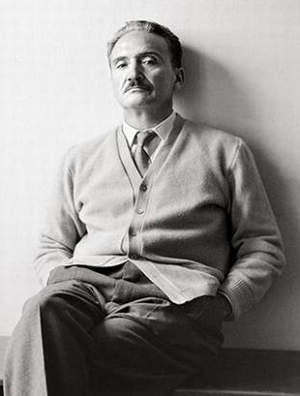2024-10-08《山上的狐狸,山下的狐狸》:它们不知道如何哭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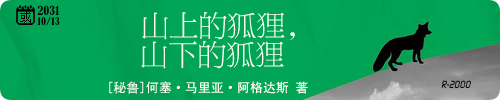
我已经试过了。可以用。真好。挑个日子来做这事并不容易。
——《尾声》
写给唐贡萨洛·洛萨达的信里,何塞·马里亚·阿格达斯说自己会前往利马,但这是“最后一次”,他把小说《山上的狐狸,山下的狐狸》和《最后一篇日记?》交给了洛萨达,而在“又另”的附言中说自己在智利搞到了一把点二二口径的手枪,这是一把已经试过的手枪,而且“可以用”,接着就是挑个日子的事了;之后阿格达斯写给自己工作的“农业大学”的校长和同学们的信中,则直接说到了自己已经考虑成熟的决定,“我要在这里做一件被众人视为残虐之事——自杀。”他希望学校的师生们不要悲伤,而是要有信心和决心,“努力解放那些一直以来被人为强加的重重限制导致无法自由飞翔的人,尤其是秘鲁人。”而死之前的阿格达斯也表达了自己的信心,虽然无法主持“克丘亚语口头文学”的编撰,但是都灵的伊诺第出版社已经接受了阿格达斯的建议,出版一部六百页的《克丘亚神话和故事集》;之后阿格达斯给大学校长和学生写了最后一封信,希望自己最喜欢和钦佩的大学教授阿尔贝托·埃斯科瓦尔能在自己的葬礼上朗读《最后一篇日记?》。
从1969年8月29日写信给洛萨达开始,阿格达斯其实已经进入到了死亡的最后阶段,他将身后事都交代清楚,甚至准备好了葬礼出席人员,然后用那把“可以用”的点二二口径手枪对准了自己——在11月5日返回利马修改了《尾声》之后,阿格达斯在大学公共厕所中开枪自杀。自杀是一场预谋,自杀更是一次行动,当阿格达斯期望用写作来对抗死亡的时候,他还是没能抵挡死亡的“诱惑”,作为自己最后留下的文字,《尾声》既是小说中的一部分,也成为了死亡的见证,或者说,他希望用写作抵抗死亡,却被死亡吞噬了。在这个意义上说,阿格达斯真实而又残酷地书写了死亡本身——死亡不是写作的客体,而是写作本身。
《尾声》之前是阿格达斯《最后一篇日记?》《最后一篇日记?》之前则是“第二部分”的小说,或者说,“第二部分”包括了小说、《最后一篇日记?》和《尾声》,如果小说指向写作、《最后一篇日记?》指向自我、《尾声》指向死亡,那么“第二部分”作为一个文本则包含了写作和自我的死亡,它们如何结合在一起,成为了阿格达斯的“死亡之书”。就像对于生命,阿格达斯用点二二口径手枪画上了句号,小说的创作,他则在《最后一篇日记?》中用文字画上了句号:他提到了唐埃斯特万去世之后,“疯子”蒙卡达没有立刻举行哀悼仪式,而是继续在渔民中布道,他的最后一次布道将在铁路市场的焦土上举行,“市政府已经下令用推土机把那里铲平,地上尽是老鼠的骸骨。”他认为迪诺克最后的结局是“阴茎因巫术变得僵硬”,想爬上十字骨沙丘顶的他希望能被治愈,但是最后被沙子掩埋了;乔卡托的故事很长很血腥,阿格达斯似乎还没有想好他的命运走向;相反,奥尔法则是在埃尔多拉多山顶投海资自尽,她没有找到战神战神图塔伊奇勒,也没有发现金银所织的网,只有海岛上的鸟粪;麦克斯韦的最后结局是被割喉,他生命的最后一刻“就像鹈鹕一样猛烈地扇动着翅膀”,他的死是因为同性恋穆多无法容忍他继续活着,而穆多的毒辣性情是被乔卡托激发出来的……
焦土、骸骨、沙子和鸟粪,都是死亡的象征,当阿格达斯在《最后一篇日记?》中以简介的方式安排了他们最后的命运,实际上就已经宣告了写作的无能为力,他无法详述迪诺克最后的结局,他放弃了对卡多佐和绿眼睛神父灰暗人生的故事,他用省略号代替了乔卡托很长很血腥的故事,在无能为力的时候为故事人为地句号,这一定是“未完成”,在给洛萨达的信中,阿格达斯就表达了小说创作中的问题:本来希望在第二部分里将故事串联起来,让情节变得有声有色,但是在写作中还是发现了第一部分章节和第二部分之间的不连贯,甚至认为缺失的部分可以再写出一部篇幅更长的小说了;在人物塑造上,阿格达斯希望让“自由”的蒙卡达和“被束缚”的乔卡托形成鲜明的对比,但是现在发现书里的人物都属于“半成品”,“我所创造的一些意象和一场混战正准备开始点火的时候被终止了。”最重要的当然是结尾,但是当最后阿格达斯只是介绍了人物各自的命运而匆匆作结,他认为小说“戛然而止”了……故事叙述上的问题,人物塑造上的不足,最后结局的仓促,阿格达斯认识到了这些问题,但是在整个人陷入死亡之中的时候,他认为是死神在不断叫唤自己,“被一个半盲、畸形(虽然说还可以行走)的躯体叫停了。”甚至《最后一篇日记?》也是因为死神的到来而加速了。
但是,阿格达斯为什么对自杀“情有独钟”?为什么无法用写作真正抵抗死亡?这就涉及到小说的主题、阿格达斯的理想以及小说和现实之间的同构关系。在小说的第一章最后,就出现了两只狐狸的对话,一只是山上的狐狸,另一只是山下的狐狸,山上和山下就这样分成了两个世界,山下的世界无雨而炎热,暖谷被挤压在山丘之中,临近大海的部分山势豁然开朗,河流里流淌着蠕虫、苍蝇、昆虫和会说话的鸟,这是原始却多产的土地;山下的世界由山上的世界发源,但是那里出产的东西更多:钢铁、幸福和鲜血,有着世间最深邃的山和崖。但是在两千多年前,山上的狐狸一直向山下走,山下的狐狸则一直向山上去,他们之后就相遇了,在神的家族唱歌、跳舞和饮酒中,相遇的狐狸制作出了小鼓,然后打出节奏,让群山一起舞动、歌唱。这就是第一次相遇带来的和谐,“高山湖泊中的黑鸭在啼唱,那冰冷的湖水是融化了的雪水。它的歌声回荡在千岩万壑的山谷之中,最终沉入深渊之底。它遍及整个高原,使隐藏在羽毛草丛里那些坚韧的植物所开的野花也跳起舞来,不对吗?”
| 编号:C66·2240720·2156 |
山上的狐狸和山下的狐狸的故事来自克丘亚语传说,两只狐狸在拉达乌萨克山相遇,它们代表的是高原和海岸,这是秘鲁历史上的两个中心,它们既是空间意义上,也是时间意义上的:在西班牙殖民者征服美洲之前,它们相遇了,而且一起喝神共舞、歌唱,“遍及整个高原”的就是融合之音,这是两个世界、两种文化的相遇,但是在美洲被征服之后,山上和山下的世界就被分开了,但是他们也有过第二次的相遇,山上的狐狸说“现在情况既更糟又更好”,山下的狐狸想要彼此交谈,让一切可能互相靠近,但是很明显第二次的相遇并没有发出融合之音,而这就是秘鲁的现实。面对这个问题,阿格达斯借用狐狸的口道出了自己的理想无法实现的困境,“写这本书的人想要自杀,他是从山上来的,‘伊玛撒普拉’至今还在他的胸口摇曳。他现在属于哪里呢?他现在是什么呢?”
但是对于阿格达斯来说,他的写作就是要让山上的狐狸和山下的狐狸再一次相遇,这种相遇对于秘鲁来说,就是交谈,就是共舞,就是歌唱。1968年,阿格达斯被授予印加·加西拉索·德拉维加奖,他在领奖时发表了演讲,他认为自己就是这种相遇的产物:年幼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和克丘亚人生活在一起,“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被扔过了那堵墙,被扔进那个家,在那里,善意要浓于仇恨,因此仇恨不会扰乱人心,而是推动人们前进的火焰。”他受到了克丘亚人歌谣和神话的影响,之后进入全马尔克斯大学他也都用克丘亚语对话,之后去往世界各地,阿格达斯也让语言成为一条“鲜活、强劲、可以被普及的纽带”,在他看来,语言连接的是“那个被圈禁的伟大民族和压迫者的世界中充满包容与人道的那个部分”。纽带即连接,阿格达斯就这样让山上的狐狸和山下的狐狸相遇、交谈,“我不是一个有文化的人,我是一个秘鲁人,我像一个快活的妖怪,我讲基督徒的语言,也讲印第安人的语言,我说西班牙语,也说克丘亚语,为此我深感骄傲。”
除了语言的实践之外,阿格达斯更是在小说中要让它们相遇,并且告诉世界秘鲁的创造力,“没有哪个国家比秘鲁更多样化,或是拥有更丰富的风俗与人的种类。这里包含世间所有的热度和色调,有爱和恨,有错综和微妙,有约定俗成和启发灵感的意象。”这就是两只狐狸渴望相互靠近的主题。小说的第一章以乔卡托带着渔民出海为开端,呈现了码头形成的多元文化,无疑这里就是一个“山下”的世界,这个世界“欲望永远不会满足”,“工厂、渔船、码头、钢铁,年复一年,工人越来越少,老板们越吃越贪,恨不得吞下整个大海。”乔卡托虽然这样诅咒,但是自己也成为了那个既得利益者,“金发、白皮肤、赤裸的女人”,既是一种资本的写照,也是欲望的堕落象征,萨瓦托这个思想家和读书人,对于秘鲁的现实形象比喻成妓女经济:“贪得无厌的皮条客,把钦博特变成了妓女,把整个秘鲁变成了妓女,这他妈的地狱。”
而在第二章里,桑博混血蒙卡达举行的“布道”仪式就是一种反抗,他曾经是渔船的装卸工,赚了不少钱,但是在骨子里他自认为是穷人,所以他背着十字架,向着即将被征用的穷人公墓而去,他认为自己的身上挂着两块招牌,一块写着“疯子、蠢货、酒鬼”,另一块则是圣母、兀鹫、蒙卡达。两块牌子就像两只狐狸,它们在蒙卡达身上相遇,而现实却被完全分开了,就像那条铁轨,把街道和市场一分为二,就像公墓的沙地也被区分为身份不同的两个区域。蒙卡达的“布道”,所跟随的就是唐格雷戈里奥·巴萨拉尔,他在游行时代表圣佩德罗区发言时就指出,将十字架埋在洼地里,就代表着对土地的拥有,“有了这块洼地,咱们不用再去约沙法谷接受审判,咱们永远留在这里。”留在这里是在内心里成为安息之地,不管教会还是政府,都无法撼动这种永恒性,“围墙会倒塌,鲜花会被烤焦,但山是永恒的,所以这里不会再有人哭泣,阿门。”而人群受到的鼓舞则是针对外国人的抗议,“美国神父,连教士袍都没穿,连裤子都没有弄脏。打倒外国佬!奔跑的公鸡,美味的鲜血!”
|
| 阿格达斯:死神加速了日记的完成 |
在小说的第三章,阿格达斯则通过鹦鹉螺渔业公司的鱼粉厂厂长唐安赫尔·林孔·哈拉米约和举止怪诞的访客唐迭戈的交谈描述了现实的丑恶,厂长唐安赫尔·林孔·哈拉米约作为布拉斯奇集团的核心成员,代表的就是“山下”,唐迭戈则是“山上的狐狸”的化身,他们相遇但只是交谈:迭戈说到了秘鲁的“血河”,“血河, 就是当狂野的安第斯山降下第一场雨时,泥土、树根、死狗尸体、石头随河水一起倾泻而下所形成的奔流……”资本裹夹着的死亡带走了生命;唐安赫尔说到了山下的发展史,尤其是乔卡托依靠布拉斯奇的发迹史,而布拉斯奇的靠山则是美国和欧洲的大都会;他们说到了黑社会团体训练沿海人和山区佬以及印第安人,就是为了煽动矛盾,“这些人四处制造混乱,他们自己舞刀弄棍的,再去教其他人如何使匕首,如何戏耍妓女……”在这场山上和山下的对话中,秘鲁成为了他们口中“七个白皮蛋对三个红皮”的对立,白皮蛋就是白色势力,他们是工业界、美国、秘鲁政府、愚昧的秘鲁人民和对秘鲁人民一无所知的教父“卡多佐们”,而教皇、共产主义以及厌恶美国、工业和政府的秘鲁人则成为红色势力,穷人和资本家,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本国民众和外国佬,当然还有印第安人和白人——它们构成了秘鲁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在这种处处存在对立的世界里,山上的狐狸和山下的狐狸根本没有相遇的可能,对于底层的人来说,唯一的命运就是死亡,身上都是煤尘的埃斯特万终于还是无法摆脱厄运,在他死之前说的话是:“该死!我的肺里有煤粉,所以快死了,但我要把这最后一盎司的煤塞给死神,妈的,保准打他个鼻青脸肿……”
面对秘鲁的现实,阿格达斯看见了高山上的光芒,他认为这种光芒会点亮所有圣灵的眼睛,能够去除世上的罪恶,这就是一个时代的开启,但是在这个时代开启之前,必须让另一个历史周期结束:结束的是“聊以自慰的云雀、鞭打、被驱赶、无能为力的仇恨、悲权的起义、对神的恐惧、作为审判者的上帝、他的仆人及兵制造者的主宰地位”,而开启的则是光,是解放的力量,是上帝,是燃烧的云雀,“解放的神即将重返。”或者说,开启之前的结束必定是一次死亡,阿格达斯几乎怀着所有的激情将秘鲁的未来称作是一场革命,“我亲近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运动,是因为它使得我从青年时期就进发出的能量找到了方向、归属和明确的目标。”这是他年轻时期立下的目标,也是在写作中实践的理念。但是写作正如秘鲁遭遇的现实一样,阿格达斯在极度的困难的情况下,一次次听到了死神的呼喊,他的革命与其说是行动不如说是信仰。在小说的创作中,阿格达斯明显感到力不从心,尤其是第二部分在不分章节的情况下,只是写到了乔卡托与“黄油”、唐伊拉里奥与“二皮脸”、麦克斯韦的决定这三个“沸点”,但是它们很快被吞噬了,阿格达斯感觉自己坠入了深井,他渴望逃离出来,但反而陷落得更深,“毫无来由,我的旧疾苏醒了,近乎吞噬了我。”
实际上整部小说都不算成功,除了“第二部分”匆匆写就之外,前面几章由于人物设置众多,而和他们相关的故事又在同一个层次发展,所以缺少侧重,而很多秘鲁山下的丑陋现象几乎都是通过对话交代的。就像对故事缺乏掌控力,阿格达斯在死神的召唤下也对生命失去了掌控力。而更为明显的一点,阿格达斯将小说变成了现实,将写作变成了生活,死亡进入了写作,写作也完全变成了死亡——小说章节中插入的日记,是现实的真实反映,是阿格达斯对于小说的注解,但其实最后完全变成了小说的一部分,这看起来是一种如山上和山下的融合,实际上裂口却越拉越大,更为悲剧的是,以克丘亚人自居的阿格达斯根本无法容忍有人称他是含有蔑视意义的“外省人”,正是在这个对立中,他和科塔萨尔展开了论争。在日记中阿格达斯评价了拉美一些作家,他认为胡安·鲁尔福把世间所有的苦难、良知、圣洁的情欲、男儿的气概都装进了文字里,他认为卡彭铁尔的智慧如闪电一般,“可以从外向内直接穿透事物”,他认为奥内蒂的文字“仿佛都以一种和谐的方式震颤着”……但是对科塔萨尔,阿格达斯则充满了嘲讽,“他在《跳房子》开篇给出的阅读建议把我吓坏了,因此我理所应当地被排除在那座宫殿之外,暂时无权擅入。”
阿格达斯说自己无权进入科塔萨尔的宫殿,实际上是都对科塔萨尔称自己是外省人感到极为不满。1967年,科塔萨尔在古巴《美洲之家》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在信中他抨击了拉丁美洲文学中存在着“地域影响论”,认为其非常狭隘与乡土气,对此阿格达斯在1968年5月的《阿马鲁》中批评了科萨塔尔的“世界主义”以及他有关“作家职业化”的观点。而在这部日记中,阿格达斯更是不断提及科塔萨尔,认为他骑在“粉红色半人马身上”,“向我投来一些铮亮的飞镖。”科塔萨尔的恼火在阿格达斯看来就是因为日记里说到了科塔萨尔的痛处,更在于自己就是一个外省人,“我是这个世界上的一个外省人,我从书本上学到的东西远不如我自己感受过、亲眼看到过的多,比如我知道一个夸夸其谈的政客和一名克丘亚司法官的区别;一名出海的渔民和一个来自的的喀喀湖的渔民的区别;双簧管、托托拉芦苇花穗、白虱叮咬和甘蔗花穗的区别;像帕里亚卡卡那样从五颗鹰蛋中诞生的人,和那些从一颗再普不过的虱卵里孵化出的人的区别(那些人的生命出现得真是唐突)。”他还讽刺了科塔萨尔小说中“技巧”,也顺带批评了略萨,说他们和自己走着不同的路,“人和人怎么可能一样呢?”
小说是阿格达斯对现实的一种反抗,日记则在对自我的记录中袒露心迹,但不管如何,这个把写作看做是生命最有意义的事的作家,一辈子都在努力让山上的狐狸和山下的狐狸再一次相遇,只是当写作无力抵抗死亡,当死亡也成为写作本身,相遇便成为了一种永远无法实现的理想,而更为残酷的现实是,在分隔的世界里,狐狸已经忘记了跳舞和歌唱,“狐狸不知道如何哭泣,只得吼叫……”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62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