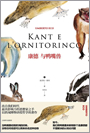2025-06-01《康德与鸭嘴兽》:连续体是一切又无所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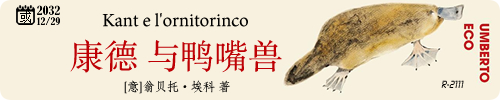
在每天都会进行的交流活动中,我们都是以信任的态度接受大量的指称。
——《关于指称即契约的笔记》
关于信任的态度,翁贝托·埃科讲述了一个上世纪五十年代意大利的一个幽默小品,他将其命名为“sarkiapone的故事”,“sarkiapone”就是“子虚乌有兽”,一种不存在的客体,一种虚构的想象之物,却是可以被指称的存在。在一列行驶的火车上,切尔利向坎帕尼尼和其他乘客打招呼,坎帕尼尼便起身然后把手伸向了行李架,上面有一个盖子布的篮子,坎帕尼尼忽然把手缩了回来,像是被里面的东西咬了一下,他说里面是sarkiapone,他要求人们不要发出声音,否则sarkiapone会被激怒。
此时喜欢吹牛的切尔利站起来,他其实根本不知道sarkiapone是什么,但他又不想别人知道这个秘密,于是他侃侃而谈了sarkiapone:当他说在亚洲见过sarkiapone,说sarkiapone长着典型的口吻,但这一说法遭到了坎帕尼尼的质疑,于是切尔利说他实际上想说的不是口吻而是喙,当他看到坎帕尼尼惊奇的表情,又马上修正说他指的是sarkiapone的鼻子;鼻子问题又遭到了质疑,然后切尔利又说起了眼睛、耳朵、鳍、下巴、毛发、羽毛等等,还试着说起sarkiapone走路的姿势、它的爪子、翅膀、鳞等,又说到了sarkiapone的颜色……实际上在切尔利描述sarkiapone的时候,他已经变成了对坎帕尼尼的反应,但没有一次是成功的。切尔利开始气急败坏,他破口大骂这种“该死的动物”,甚至他决定放弃猜测它到底是什么东西。于是切尔利要求坎帕尼尼把sarkiapone拿出来,此时其他的乘客都恐惧地向后缩着身子,而坎帕尼尼这是才告诉大家sarkiapone并不存在,而且打开了盖在上面的布,篮子里面空空如也——坎帕尼尼坦诚它只是想赶走那些讨厌鬼,好让自己独享这个车厢,而奇妙的是,切尔利似乎知道坎帕尼尼的企图一样,说他在整个过程中都知道这是一个玩笑。
那么,在这个关于“子虚乌有兽”的小品中,切尔利是不是真的知道sarkiapone是不存在却偏要在玩笑中谈论它?当然不是,按照埃科的分析,当坎帕尼尼说篮子里有sarkiapone的时候,他设定了“sarkiapone”作为谈论的语词的存在,而切尔利就是假定了相对应的客体,从坎帕尼尼的语词到切尔利的客体,他们之间就已经建立了信任,他们就已经在“sarkiapone”上进行了协商,这是一个关于指称的起点,埃科将这种信任理解为“白盒子”,它和被定义为不能打开的“黑匣子”不同,白盒子意味着即使关着也会被打开,也就是说,白盒子被打开是一个鉴于信任的预设,就像在节日或生日的时候,朋友送给我们礼物,尽管在盒子里,我们也应该猜到里面有礼物,因为谁也不会用一只空盒子让我们吃惊,这就是信任,信任是指称的条件,“我们在指称行为中合作,即使在我们对这个指称物什么都不了解,即使我们连说话者所使用的这个词的意思都不知道。”但是这种信任所关涉的指称是语词还是客体?
埃科认为,切尔利明明知道“sarkiapone”是不存在之物,所以他信任坎帕尼尼的是他使用的语词,也就是“sarkiapone”这个名称,所以关于信任的链条不是从客体到名称的使用,而是从坎帕尼尼决定使用这个名称到切尔利决定像坎帕尼尼那样使用它,所以因果链就是从名称使用1到名称使用2所表现出的因果性——埃科把sarkiapone既存在又具有实在性称为“硬性”指称,而如果是想象出来的虚构事物,那么这便是“软性”指称,和硬性指称相比,软性指称更具有仪式的“受洗性”。但是在小品中信任是在不经意间达成的,起初坎帕尼尼说sarkiapone容易被激怒而不能被打扰的时候,他已经给白盒子贴上了标签,也就是他指称了sarkiapone是一种有生命的动物,在切尔利对“sarkiapone”进行描述的时候,他其实将坎帕尼尼作为个体的sarkiapone变成了种属意义上的客体,所以他要从不同的方面给这种种属下定义,也就是说,他求助的是普遍性或一般性的客体——在埃科对认知类型的分析中,他使用了康德的图式观念,认识类型即CT,就是一个规则,一个建构客体形象而不是建构多介质形象的程序,而认知的核心内容是一种阐释的中介,即NC,CT决定了由NC所表达的阐释中介,而NC则构想一个适当的CT成为可能,也就是说,在认知中,CT具有个体性,而NC具有公共性。
回到小品,当切尔利谈论一般的sarkiapone就是试图建构关于sarkiapone的NC信息,从而形成一个个体性的CT,从NC的建构到CT的指称,在切尔利身上也体现了这种协商性。但是在切尔利都对可能属性进行描述而不能证实的时候,“连续性掏空”的过程中,他最后只能接受这个名称,即使他恼羞成怒骂这是“该死的动物”,这个“动物”也依然是一种指称行为。最后坎帕尼尼揭示出sarkiapone并不存在,切尔利才意识到自己一直在谈论的是一种并不存在的动物,一个虚构物,但是在恶作剧被揭穿之后,指称行为依然没有停止,但是完全变成了对sarkiapone名称的指称,至此,坎帕尼尼和切尔利都达成了完全一致的协议。所以埃科认为,指称就是说话者在协商基础上实施的行为,而且原则上语词实施的指称行为与对语词的意义了解无关,甚至和指称物是否存在也无关,即使是在硬性指称上,它也具有契约的初期形态,或者说契约关系正是从最初阶段开始才能建立信任的指称行为。
指称即基于信任的契约,它是一个言语行为,这种行为并不是要描述一个存在的客体,它也是在指称语词本身,这种行为也不是为了指称个体,而是一种赋予个体所属的属、种或纲的一些属性,或者说,指称是在构建一种阐释的中介,即具有公共性的NC,所以它是一种规则,“我们指称的不是任何什么个体或一组个体,而是重新确认一个文化规则,做出一个符号的而非事实性的判断,重述我们的文化定义一个概念的方式。”在这里埃科批判了结构主义符号学所认为的指称行为必须在我们知道用来指称语词的意义时才是可能的,也就是他们把指称现象看成是一种“言外”的事故,也就是指称的是一个世界的事态,但是当我们说出这样的句子:看那只鸭嘴兽,去把我放在桌子上的鸭嘴兽标本拿给我,悉尼动物园里的鸭嘴兽死了。“鸭嘴兽”在这里都不是一种个体,而是属性,而是故规则。所以埃科将指称放在本体论的意义上来阐述:强本体论指称的是可定义的个体,是某人或某物,是一种神圣心智的模型,就像电子邮件一样,@所构成的指称只对应于一个实体,而且只对应这个实体;但是要保证一种客体性,还必须构想一种弱本体论,它属于共同体心智,是通过阐释中介、不断趋向于某物的指称。
| 编号:B89·2250414·2279 |
但是,从小品的指称行为来看,指称本体论的最大意义就在于:在基于信任的契约意义上,“所有的不可能之物都是无法想象的,但是并非所有无法想象之物都是不可能的。”就像面对白盒子,我们会通过不同方式偷看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如果是不可想象之物,指称就会调和各种麻烦,也就是说,不管某物存在还是不存在,无不能阻止我们指称那个某物,“白盒子”本身就成为了可信任的指称符号,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所探讨的可能世界就是一个协商的世界,它达成的是关于指称的“共识”。将指称上升到本体论意义,埃科其实是让指称本身变成一种契约,而当契约是在相互信任之上达成的,那么协商是不是也意味着对意义的抵达,或者说,意义是不是也是一种契约?
意义是不是就是在指称行为中,事物和符号之间的相符?意义是一个复杂的多维概念,它涉及到符号与事物的关系、符号系统内部的结构、语境的作用以及符号的使用等多个方面,从符号学的综合视角来看,意义是一个动态的、连续的过程,它在符号的生成、使用和解释中不断被建构和重构。埃科举例说朋友桑德拉告诉他在澳大利亚不能忘记去看一看世界第八大奇迹的艾尔斯巨石山,但是出现在他面前的艾尔斯巨石山却可以有两种说法,从科学角度来说,它是一块石头,是一个插在地上孤立的巨石,所以它不是山,但是从现场观察来看,它也是一座山,是巨石山。艾尔斯巨石山是石头还是山?埃科分析认为,这两种认知其实反应了在指称的语言学中体现了词典表呈和百科全书知识的不同:词典清晰记录了词语特性,它记录的是语言内部的关系,所以词典能力指的是某物把自身限制在一种树形目录下的所属位置所处的记录,它却把世界的只是要素抛在一边,而百科全书则是一种复杂的描述,艾尔斯巨石山而不是山而是石头就是百科全书式知识的一种描述,它预设的是语言外的知识,按照桑德拉的说法,“人们在进行日常言说时都是遵循百科全书模式,只有有学问的人才会去查词典。”
和词典能力不同,百科性能力既涉及目录、名称,也涉及内容,而且在埃科看来,文件和目录的总和代表着一种调节性概念的百科全书,“图书馆中的图书馆,一个对不能被任何单独的说话者所实现的知识总体性的公设,一个还没有被社会共同体所探知的、永远都在增长的宝库。”这种不断增长的宝库正是意义不断被建构的过程,“鸭嘴兽的真实故事”就是对鸭嘴兽进行命名和构建知识宝库的故事:1798年的时候,大英博物馆收到了一个动物标本,澳大利亚殖民者将其称为“水鼹鼠”或“鸭喙平足兽”,它是在1797年11月在位于霍克斯伯里附近的湖岸上被发现的,动物学家乔治·肖在惊叹和好奇中认为这是把鸭子的喙“移植”到了一种四足动物的头上,说是“移植”实际上在乔治·肖看来就是一种人工伪造的动物,所以在未知而无法识别的情况下,他相信他并不存在,但是从科学的角度出发,他也不能简单的放弃,于是就在词典和百科全书之间摇摆不定;之后的霍姆根据肖的描述,认为这种动物的属可能和针鼹相同,除此之外,他还从该动物标本的生殖器、舌头等器官的特征,认为是和鸟、两栖动物相关的“族”;也有人提出这是一种哺乳动物,但是有乳房的一定是哺乳动物吗?它有卵生动物的生殖器,但是卵生动物只能生蛋,1829年人们提出的疑问是:如果它是单孔目动物,那就不可能是哺乳动物,它也不可能是鸟,因为它们没有翅膀也没有羽毛,也不可能是爬行动物,因为它们是热血动物,还有,它的肺包括在胸膜中,被隔膜和腹部间隔开来也不可能是鱼,圣-希拉里就认为有必要为它们创立第五种脊椎动物范畴;直到1884年,考德威尔在澳大利亚实地考察时有了实质性发现,他在给悉尼大学的贺电上写道:“单孔目卵生,不全裂卵”……
从被发现到确定它的种属范畴,经历了80年,也争论了80年,在埃科看来,鸭嘴兽的真实故事说明了借助概念框架、赋予句子以意义都是观察性的句子的理论形成,当观察的解构被质疑时,就需要进行调整,但是也都是在概念框架之内进行调整,最后事实战胜了理论,就像皮尔士所说,“我们所要做的就是等待,而社会共同体到最后会找到一个共识点的。”等待事实的出现,等待社会共同体找到共识点,这说明鸭嘴兽的故事就是一个长期协商的故事,而在协商的过程中,埃科提出了“连续体”的概念:协商意味着各种否定性、删除性的抵制,在抵制中切断自身然后重新组织,从而建构科学的范式;另一个方面来讲,协商要达成契约,也并非是毫无凭据的七月,不如说,契约之所以可能就是因为契约规则已经存在:从契约规则出发,通过协商达成契约,最后形成关于意义的科学范式,这就是通过符号来指称事物、认知世界以及构建意义的连续体。
鸭嘴兽的真实故事中,当我们通过对符号的使用和解释,将符号与事物联系起来,这种联系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在连续的语境和认知过程中不断被协商和确定的,连续体就体现了指称的连续性和动态性。而回到“康德与鸭嘴兽”,康德和鸭嘴兽之间也存在指称、认知的问题?当鸭嘴兽在西方出现的时候,康德已经在1798年出版了最后一部著作《实用人类学》,当人们开始谈论鸭嘴兽的时候,康德已经是耄耋老人了,当最后确认鸭嘴兽是卵生的哺乳动物的时候,康德已经去世八年了。“康德与鸭嘴兽有什么关系呢?什么关系也没有。”在序言中埃科就回答了这个问题,但是当他将这两样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放在一起,并非是真正“什么关系也没有”,他的问题是关于认知的:康德遇上鸭嘴兽,他会怎么做?按照《判断力批判》中的说法,判断是把具体事例情况作为通则的一部分加以认识的能力,如果通则已经在那里,判断就是决定性的,如果没有通则只有具体事例,那么判断则是反思性的——而如果判断来自反思性的,那么决定性的本质就会进入危机状态,“自身并不具有建立客体概念的原则”,决定性判断只是局限于把客体归属在像原则这样的给定的定律或概念下面。
反思性判断归属于未给定的规律,是一种不明前提推论,这意味着对某物的阐释是一个假设,而从某物出发,需要确定的是一种经验法则,它不是先验性给予的,而是需要我们进行建构,在这里,埃科关于鸭嘴兽的判断就从康德的图式主义中寻找答案。康德的图式是知性的能力,它不是对一个可能的客体进行简单的确定,而是制造这个客体并构建它,在这个过程中,知性不断尝试,有时还会在错误中运行。在这里埃科引入了皮尔士的“基础”,并将它的纯粹可能性和指号过程的初级条件联系起来,分析了皮尔士“直接客体”和感知判断之间的关系,使得直接可能在被阐述、被传播中走向了公共性道路,“它的确必须接受不断的考察、修正和重构。”或者在这个意义上,埃科让康德的图式不那么“空”,在介于直觉和概念之间自身拥有了第一性和核心概念,并且让感觉的东西成型,并且通过保存重新阐释它。
康德认为构建物是直觉的盲目材料,而皮尔士没有为我们提供“客观性”保证的初级像似符,但是关于鸭嘴兽的认知依然在鸭嘴兽的图式中被构建,所以图式主义不先在于自然中,不在先验中,却是不断被建构的受动性存在,在这个意义上,“正是在这种受动性的启发下连续体的本质才被揭示出来。”这一启发揭示了连续体的本质,也是埃科对符号学理论的一种“连续体”式建构,一方面,他在探讨存在、认知以及符号指称等问题时,发现难以用传统的二元对立或简单的分类来解释一些复杂的认知和符号现象,于是引入了连续体的概念,以此来更好地描述和理解认知过程和符号指称中的复杂性和模糊性;另一方面,在1976年完成《符号学理论》之后,回过头来发现欠下了很多的债务,“这些债务涉及指称、像似论、真理、感知以及当时被我称之为符号学初级入门的问题。”《康德与鸭嘴兽》就是通过康德的认知理论来解决关于鸭嘴兽的指称问题,而鸭嘴兽的身份危机又是一个动物寓言集的故事,“至少是为了使我的动物寓言有新意,我就把鸭嘴兽作为主人公引入这本书中。”康德让鸭嘴兽具有了哲学资格,鸭嘴兽又像独角兽一样陪伴埃科走在符号学不断丰富之路上,“正如早身汉一样,思考语言离不开独角兽。”
实际上,这种不断提出问题、不断修正问题、不断建构理论,不断解决现实认知的过程,也可以看做是埃科“连续体”思想的一种寓言式表达,而在这本整饬符号学理论的文本中,埃科其实最重要的部分是谈及了语言作为连续体的意义,“我就意指、文本和互文本、叙事性,以及阐释的条分缕析和限度这些问题进行了论述。”因为这个问题触及的就是存在,是语言学意义上的存在,或者是“在限制我们说话自由的时候谈及的存在”。一个存在是存在实体,另一个则是存在,语言的存在就是其所是,但是涉及这个存在本身的“是”又是什么?他引用莱布尼兹激烈的设问“为什么有某物而没有无物?”来开启他的“存在”之旅:存在的含义是某物?符号学的问题之一是我们是否以及如何使用符号去指称某物,但是在埃科看来,符号学无法回避的是另一个根本问题:促使我们去生产符号的某物是什么?
这是符号学比指称行为更本原的起点,因为生产符号更是一个起点,它所指的就是:“是什么在促使我们说话?”这个起点其实在说话之前,在符号指称之前,它是一种事物的前语言状态,在皮尔士那里,这个对直接客体的生产者就是动态客体,动态客体就是“我们从中生成某物”的存在,埃科认为,这个动态客体就是永远在场却不能捕捉到,“它总是物自体”,是原初指示性或注意力,它发生在好奇心之前,发生在把一个物体感知成一个物体之前。如果某物是形成指示性符号而朝向确切的事物的某物,那么在好奇心之前形成的注意力或原初指示性符号就是莱布尼兹所说的“无物”,“为什么有某物而没有无物?”这种无物性在期盼中被打开,也就意味着它已经处在存在中,它是前语言状态,是在场却不能捕捉的动态客体即物自体,“因为有着。”就像从母亲的子宫中出来的婴儿发出的第一声啼哭,他朝向着这个世界的某物打招呼,“这种原初指示性现象向我们表明朝外触及某物的意图”,它的目的是触及“某物”。
所以在埃科看来,存在可以被思索就是作为语言的效用向我们展示自己,或者说,存在被说及就已经被阐释了,“为了让存在存在,就必须去想也必须去说。”去说是说某物,更是说“无物”,去说这一行为就是存在本身,所以它不在乎说什么,“没有言语就不再有实体:由于实体逃遁了,就产生了非实体,换句话说就是无物性。”在这个意义上无物性就是就是存在,语言和存在具有同质性,“于是存在的自我揭蔽在语言内部得以实现。”就像荷尔德林所写:“但是留下的将会由诗人凭直觉知道。”埃科认为,存在着一种能够单义性地命名实体的话语,也存在着一种允许我们言说“不可知者的否定神学话语”,而对于这种无物性进行言说的人就是诗人,就是隐喻大师,就是神秘主义者,他们的阐释是在摧毁坚固的确定性,而存在就是给予更多阐释的东西,真理就是经诗意性地阐明“一支由隐喻、借喻和拟人组成的机动部队”。
可以体验,可以言说,可以思考,这就是语言的“连续体”,“如果你同意的话就是那个在、已在和将要在的出于需要和权宜的无限的界域。”在这个连续体里,一切无所是又逃避了任何定义,所以存在从来不是一条单行道,而是多车道的高速公路,即使还会有死胡同——存在着不能说的事物,而这是不是藏在篮子里的“sarkiapone”?在认知上信任开始了协商,协商诞生了契约,鸭嘴兽被编写进了百科全书,这是科学走过的路。但是不存在之物一样在无物性上创造了符号,创造了语言,这是诗人的语言,它占据着自由的区域,它超越限制的东西,鸭嘴兽也可以飞翔,“诗人们真正对我们说的是我们需要用快乐与存在相遇。去质疑它,测试它的抵制,把握它的敞开处和它的蛛丝马迹,这些都从未明晰过。”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7503]
思前:流动的盛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