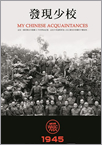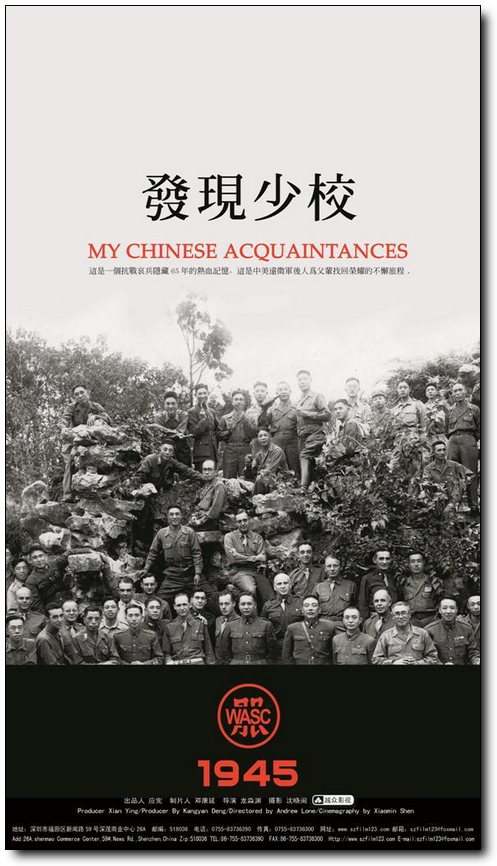2015-10-16 《发现少校》:历史,以民间的方式被唤醒

1937年爆发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这是历史;1943年中国军民打通缅甸公路,抢救中国物资补给的生命线,这也是历史;中美盟军携手在密支那战役中取得决定性胜利,扭转了东南亚战区的局面,这也是历史;1945年9月9日,中国战区的日本投降仪式在南京举行,这更是历史。在这一段历史中,有生死,有荣辱,有聚离,但最后是最伟大的胜利,是应该成为最辉煌的时刻,但是这样的胜利会以怎样的方式写进历史,这样的伟大带给亲历者是一种铭记在心的荣耀?历史中的时间、地点,历史中的过程和结果却仿佛只是一个大写的符号,仿佛只是一个不能深入探究的段落,而在大写的符号和段落里,那些亲历者、建在者甚至无法触摸真实的细节,仿佛被一种历史必然形成的规则阻挡在外面,像一个旁观者,远远地隔着玻璃凝望,最后发出一声叹息。
2005年,是中国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85岁的赵振英老人穿行在中国壮士广场,向国民革命军新六军十四师十四团团长廖耀湘的雕像献花,寻找在抗战老兵手印广场上自己当年的手印,对于他来说,这是时隔60年后再次走进那段血风腥雨的历史,那段硝烟弥漫的历史,也是走进自己一生最荣耀的时刻,但是有些寂然和凄然,那些和自己并肩作战过的壮士,都以雕塑的方式出现在他面前,死去的烈士和活着的英雄,以如此迥异的方式走在了一起,对于赵振英来说,或者并不是历史被揭开一页的惊喜,而是一种无奈,甚至逃避。
|
| 导演: 龙淼渊 / 沈晓闽 |
 |
晏欢,这个在深圳从事设计工作的工程师,发现了那一段被渐渐湮灭的历史,他的外公潘裕昆,曾任中国远征军驻印军第五十师师长,先后参加过淞沪会战、粤北战役、缅甸战役,是战功卓著的抗日名将。正因如此,晏欢一直耗费大量的业余时间,致力于远征军研究,并寻找滇缅战场的亲历者。他是远征军民间学者,在他的努力下,他联系到了当时参加盟军的美国少校约翰·葛顿南的儿子尼尔·葛顿南,在他的寻找中,他搜集到了尼尔一直保存下来当时盟军告别时签名的小红本子,在他的关注中,年老的赵振英也终于向他开启了一段尘封的记忆。在尼尔保存的小本子上,有廖耀湘、武天龙、宁伟等一大批国民党军官的亲笔签名,当然也有赵振英的签名。这是珍贵的档案,有字迹已经模糊的签名,有画面已经发黄的照片,也有记载着历史荣耀的纪念章,当这些物件被发现被公开,那一段历史才被连接在一起,才在具体的细节里变成珍贵的史料。
|
|
| 《发现少校》海报 |
这种发现当然是欣喜的,而对于这段历史的发现,有两种途径,一个是约翰·葛顿南曾经生活过的美国纽科克镇,约翰·葛顿南那些小红本、照片和纪念章都由他的妻子薇丽和儿子尼尔·葛顿南保存,所以当在网上看到相关的线索之后,他们联系了晏欢,并且尼尔亲自来到深圳,来到南京,来到中缅边境的云南腾冲,不仅将这些档案带到了中国,还在腾冲的国殇墓园、来凤山遗址感受当年的激战岁月,感受为胜利的献身精神。而从美国这条线索,又发现了乔-韩恩士、甘蒲中奖等盟军将领的相关情况,以及关于那段历史的珍贵史料,这些照片、档案对于丰富那段历史具有重要的意义,而这些盟军将领对于赵振英来说,却也是熟悉的,不仅对于个体意义,还是对于国家意义来说,都是举足轻重的。
但是在美国这条线索之外,在赵振英这条线索中,却遭遇了尴尬。赵振英是当时国民革命军新六军十四师四十团第一营的少校营长,在中印缅战区和盟军将领、士兵生活、战斗在一起,所以在那张照片和小红本上都有他的身影和名字,而当抗战胜利举行的南京受降仪式上,他还是现场的亲历者和见证者,作为警戒工作的负责人,他出现在照片里左上角门边上的位置上,正因为亲历者的身份,赵振英还能够详细回忆起当时签字仪式的种种经过,中方和日方如何陆续进场,日方如何签字并提交中方代表,中方如何最后宣布胜利,但是这一切却都是隐秘的,在现在的受降仪式旧址,赵振英指着那些蜡像说,这些军官似乎年纪还要轻一点,服装颜色似乎也不对,两个人站的位置似乎也有偏差。实际上,在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举行的受降仪式属于历史,属于官方的历史,但是在这官方历史之外,却还有赵振英个体的历史,两者似乎有着偏差,甚至有着相异,而其实这种相异也使得赵振英成为这一段历史另外的见证者,成为另外的隐秘者。
1945年日本签订投降书,宣告抗日战争胜利,这本应是中国百年间最荣耀一刻,但见证这一幕的赵振英却说:“对于我,这根本谈不上光荣。我的孩子也不知道我的事情。”他甚至把这一段参与和见证的历史叫做“丑历史”,他多年来闭口不言那段经历,而在之后的30年间,他搬家两次,街坊都只知道老人当过兵,却没有人晓得他具体干过什么,平时见人,他总是低着头,连自己的子女,也从来不知道父亲亲历了受降仪式。为什么这一段光荣的历史,在赵振英看来是个人的丑历史呢?参加中印缅战区作战、参与日本投降签字,之后奔赴东北参加内战,本来是想通过军官考试避免直接进入战场,但是随着战事的扩大,赵振英失去了这次机会,而从此开始,他的人生也发生了重大转折。
之后结婚,在南京上大学,毕业之后在南京工作,之后又转到天津工作,似乎人生在过了战争之后趋于平静,但是这只是暂时现象,因为自己的国民党身份,1969年,两个警察突然出现在他面前,将他逮捕,罪名是:历史反革命,赵振英被判刑20年。为了生活的平静,他亲手毁掉那些战场上的照片、徽章,以及能够证明自己军官身份的文件,但是还是陷在历史的漩涡里,自此,赵振英承受着身体和精神上的折磨,变得精神恍惚,有一次洗脚时,竟然穿着鞋子就把脚伸进了盆里。劳改期间,不服气的赵振英把申诉书从天津南开法院写到国务院,最终等来的,却是自己缺席的离婚判决。他知道是妻子在无奈中保全家庭所做的牺牲,1975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对国民党县团级以上军官特赦令,赵振英也在其中。次日,他便让单位开了份证明,与妻子复婚。
“由于我判过刑、坐过牢,所以自己一直认为这是丑恶的历史。”赵振英这样说。似乎个体历史的特殊性改变了整段历史性质,所以赵振英沉默,隐秘,而饱受风雨的几十年里,赵振英似乎只要在和老伴的共处中找到一丝安慰,2005年爱妻离去,给这位老兵带来的是沉重打击。他把妻子的骨灰留在家中,5年时间里,他每天到妻子遗像前说话:“我知道你在苦苦等着我,我也在每天怀念你,我们就快些到一起去吧。”那段历史,他不仅选择沉默,更选择遗忘,他甚至希望早早和妻子在另一个世界相会,“我不愿意留在这个大地上,这大地对我太坷了。”
荣耀的历史,对于个体来说却是受伤的岁月,这是谁制造的不公平,这是谁制造的伤害?而其实正是由于像赵振英这样的个体选择沉默和遗忘,所以历史被无情地覆盖上了尘埃,甚至被书写成有偏差的一页。而尼尔·葛顿南以及那些美国军官的后代的档案才在有限的范围内重新使这段历史付出水面,“我们只能借助异国的资料为本民族的英雄找回荣耀。”这一定是一种尴尬,当约翰战胜回国迎来的是荣耀,是掌声,是尊敬,但是对于像赵振英这样的胜利者来说,却面对的是痛苦、伤害和侮辱。
其实,在赵振英个体的命运里,一直选择封闭,这是历史的缺席,但是即使被那些异国的资料、档案揭开历史的一角的时候,对于赵振英来说,也并非是彻底的袒露,他接受了尼尔赠送给他的奖章,却也是战战兢兢地戴起来;他行走在壮士广场,看见老兵手印广场上自己的手印,却依然深埋着某种担忧。历史被唤醒,似乎从来都是以民间的方式,制作网站寻找线索的晏欢是远征军的民间学者,最后尼尔将纪念档案捐赠给四川建川博物馆聚落,而这也是一个民间博物馆。
“献给捍卫民族荣耀的人。”这是记录片最后的一句告白,大写的历史里是荣耀,个体历史里却是伤害,所以对于个体的沉默,历史一定是缺省的,而民间学者寻找历史线索,民间博物馆保存最珍贵的档案,对于这一段历史来说,民间的力量是弥补和唤醒,是一种重新书写,但也有着沉重,有着尴尬,有着悲哀。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4013]
思前: 空两格,冒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