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10-25《监狱里的图书馆》:神圣之处在于分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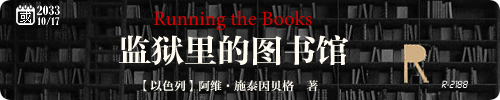
这天晚上,我看到的那张字条,是某人扔弃的一封信,是某个悲惨的普拉斯在馆内留下的残言破语:亲爱的妈妈:我的生活是
——《书不是信箱》
没有结尾,没有落款,它悬搁在那里,这是没有完成言说的一段告白,这是一封不曾寄出的信,“我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是埋怨?是无奈?是悲泣?还是快乐?但是它一定是某个寄信人写下的,也一定有一个收信人,寄信人和收信人通过这封信被连接起来,这是属于他们私密的对话,但是当这封信变成没有穷尽的言说,变成无限空白的表达,是不是也是对人生的一种态度?
“这也是纪念监狱的一种方式。”阿维·施泰因贝格这样说,在监狱里信被叫做“风筝”,它从寄信人的手里放飞,它最终落到收信人的手中,就像风筝,两端永远被不同的手握着,就像图书馆那套《联邦判例汇编》丛书第57卷,它们是希勒和马尔斯·芭尔这段雨中鸳鸯表达暴风雨般爱情的信箱,他们不可能在狱中重逢,却通过这个特殊的信箱传递情感;就像十九岁初犯的斯蒂克斯,在信的结尾处总是写下:“下周我会再放一只风筝。”但是“风筝”却断了,那个想对妈妈讲述“我的生活”的犯人,没有写完这封信,或者即使他写完了信,将风筝发送了出去,也可能不会知道收信人是否收到,所以风筝放飞也好,断线也罢,对于监狱这个特殊的地方来说,“一封不曾寄出的信,写不尽无限空白,写不尽人生况味。”
图书馆作为监狱里的一个特殊存在,它就是为无法相见的人构筑起那个叫信箱的东西,就是让无法重逢的人放飞手中的风筝,但是当不曾寄出的信落在我这个图书管理员手上,这种“纪念监狱”的方式又意味着什么?监狱和图书馆,这两个处在不同语境下的词组合在一起,它带来的问题是:监狱里的图书馆到底有什么用?或者可以用另一种视角来思考:当犯人有了属于自己的图书馆,有了可以传递信息的信箱,有了倾诉情感的“风筝”,这是不是一种进步?监狱在过去是令人畏惧的罪恶象征,有铁门钉,有阴森的铁栏杆,有瞭望塔,有沉重的大门,这一切存在于霍桑笔下,但是当那些文字现在只是被存放在图书馆书架上,监狱已经变成了平淡无奇的建筑,甚至它默默融入了周围的环境,“从高速路上就能看见”,这是时代的进步带来的变化,但是监狱的本质是不是也由此被改变?
当阿维成为了监狱档案管理员之后,他去鹿岛参观了波士顿的古老监狱,这座古老建筑就是古代时代监狱的象征,“监狱和墓地,证明了乌托邦之虚妄,而鹿岛两者兼备。”这是新欧洲移民居住地以外的地方,被称为“法外之地”的这座监狱也是“魔鬼领地”,海盗、恶棍、罪犯、灾民和被流放者将这里变成了猖獗之地,也成为了被人遗忘的人间炼狱。阿维提到美国诗人西尔维娅·普拉斯就是在离岛最近的居民区长大,她并不是以遥望的方式看见这座人间炼狱,“风景不是大地,而是大地的尽头,如山峦般绵延起伏的大西洋波涛,冷冷的,咸咸的”,在她的诗歌《雪莉角》中,她描写了这座破败凋敝的监狱,它被“汹涌的海水”围困,被“肆虐的海浪”侵蚀,在“大海的冲刷下”一点一点被蚕食。普拉斯描写鹿岛的破败和可怕,也是对于自我命运如监狱般存在的书写,八岁那年父亲的猝死成为她人生的最大创伤,直到1959年她才有勇气和泰德·休斯去了温斯罗普的父亲墓地,在墓地她感到“受到了欺骗”,墓碑和墓碑都挨得很近,“仿佛死人们脸贴着脸,睡在救济院里”,她甚至希望“将他挖出来”,只为了证明活过的父亲“真的死了”。
那一次,他们被鹿岛监狱的狱警赶走,而四年之后普拉斯在厨房里用煤气自杀,她甚至把她和孩子们之间的门窗全部封死。普拉斯感受到了“冷冷的,咸咸的”大西洋波涛,感受到了墓地的丑陋和死亡,更感受到了如监狱一般的隔阂与孤独——丈夫的背叛或者是她走向死亡的催化剂,但是当她在日记中写道“他会离我多远呢?”的时候,更强烈的还是像死人们脸贴着脸的恐怖现实。这种现实也成为鹿岛的写照:它曾是人间炼狱,而现在它已经变成了土墩,变成了遗址,普拉斯感受到的“死人们脸贴着脸”的纪念方式何曾远离?阿维说,监鹿岛监狱已经没有了,但是那里却出现了一家豪华四星级酒店,酒店的名字叫“自由”,酒店的餐厅叫“囚室”,酒店的酒吧叫“不在场证明”,酒店保留了监狱的痕迹,但是它却将痛苦、暴力和心碎包装成了高档的庸俗艺术,这难道也是纪念监狱的一种方式?“一所监狱留下的遗迹,哪怕被成功地辨别出是监狱,也不能带来更加清晰的答案,反而加深了监狱存在的根本矛盾。”监狱的功能是对罪恶的“报复”?还是对善的回归?它是对犯人的改造?还是更为可怕的惩罚?
| 编号:C46·2250914·2358 |
但是不管变与不变,阿维唯一觉得有进步的只有一点:曾经的鹿岛监狱没有图书馆,而现在的波士顿监狱却拥有了一座图书馆,那么回到关于进步与否的问题:监狱图书馆到底有什么用?它真的代表着一种灵魂拯救意义上的进步?“不管你是重刑犯,还是短期关押者,你一定会走进监狱里的图书馆,惬意地徜徉在书架之间,呼吸着浓郁的书香。”但是对于很多囚犯来说,来图书馆不是为了看书,在属于他们的休闲场所里,他们只是给了自己放风的机会,或者东张西方,或者不自觉成为别人偷窥的对象,按照黑人狱警的说法,监狱图书馆“一点用也没有”,即使有像马尔科姆这样的重刑犯,他来这里读书是为了培养政治意识,像白毛这样的唯物主义者,读书则是为了研究如何使用更暴力的手段实施更残酷的犯罪活动。而阿维之所以成为图书管理员,也并非是为了拯救他人。作为一个公然违背犹太教义的犹太人,竟然在赎罪日喝得烂醉如泥,然后解开了一个大三女生高贵而神圣的文胸,从此他再也不被邀请去参加朋友的聚会、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仪式,只能通过自由撰稿或者帮别人写讣闻的的方式维持生计,“我既没有失业保险,也没有医疗保险,跟破产没两样。”
就是在这样几乎走投无路的情况下,阿维看到了一则波士顿监狱的招聘启事,于是他前去应聘,最后接到了人事部的电话,成为了监狱的图书管理员。对我来说,这不仅仅是让我摆脱“脱产”的工作,更是人生转向的开始,因为我从这里看到了实现一个疯狂而远大梦想的机会:“做一个图书馆馆员,佩戴着警察徽章,却散发着街头老大的气息,以书为械,既是书呆子,又是大坏蛋。”也就是说,我从此将拥有一个黑白通吃的复杂身份,“必将助我平步青云,跻身上流社会的各大酒会。”这就是我从这个工作获得的所谓成就感,它不也是改建成为酒店而散发的庸俗味道?而前任图书馆馆长阿马托是最炫的图书馆馆员,银灰色双排扣西装、一丝不苟的油头和闪闪发光的精致袖口,他就像是黑手党的老大,实际上他也是一个强调秩序和权力的“张扬的独裁者”。所以尽管监狱的形态发生了改变,监狱拥有了图书馆,但是它大风本质并没有改变,它就像是霍布斯笔下的“利维坦”,看起来不再有强大的中央集权,但是那里依然上演着“人人相互为敌的战争”,而这里的每个人都是孤独、贫困、龌龊、野蛮的短暂的存在,“书中描绘的那些人就聚在同一间房间里,就坐在我面前:孤侠、穷鬼、龌龊鬼、蛮女和矮冬瓜。”
监狱里上演着“人人相互为敌的战争”,每个犯人都处在孤独、贫困、龌龊、野蛮之中,但是当阿维成为图书管理员之后,却发现了图书馆存在的真正意义,那就是放飞“风筝”,让无法相见、无法重聚的人通过这一特殊形式对话,让他们成为被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寄信人和收信人。在小说中,阿维试图从监狱犯人的群像中寻找到放飞风筝特殊的人,但是对于群像的描写过于杂碎,很多人物只是被粗线条勾勒,却没有真正触及他们的世界,一种俯瞰式的描写让整部小说显得松散。而具体、细致推进情节的人物只有两个,一个是杰西卡,另一个则是楚尼。杰西卡是阿维作为女囚犯的创意老师上课时关注到的,她总是朝向窗口之外,我以为她对创意课不感兴趣,但其实她是通过这扇窗看见在篮球场上打球的克里斯,十八岁的克里斯不是别人,是她两岁时遗弃的儿子,“他们的人生际遇将他们带到这里,这个自我封闭的世界里,只隔着一扇窗户,就能看见彼此。”
杰西卡的目光其实就是风筝,她以母亲的愧疚和期盼作为“寄信人”,发送到其实并不认识她的克里斯,但是这一种单向的传递就像没有写完更没有寄出的信,所以我想要发挥图书馆的功能,让失散的母子相认,以此“重建母子情深”,而这才是真正纪念监狱的方法,“即使是在监禁的情况下,只要给囚犯一扇窗,视野就会更开阔。”杰西卡从铁窗望出去,操场的中心就是她构建的焦点,在这个焦点里,只有她的儿子——她十八岁的时候遗弃了儿子,在儿子十八岁的时候她望见了儿子,时间已经流逝了,但是她的目光重拾了这段时光,这对于她来说也许就是一种赎罪。但是阿维试图通过图书馆构建母子感情的计划并没有取得效果,因为克里斯根本不知道他的母亲在这里,也没有阅读杰西卡写的信。而且,之后的杰西卡因为无法戒毒,需要被转移到州监狱,在临走之前,杰西卡想要给克里斯留下最后一封信,在信中她会写下她的家人和自己的成长经历,她想要给他送上自己肖像的礼物,希望他从此记住那个叫“母亲”的人。但是直到杰西卡离开监狱,阿维都没有收到转交给克里斯的信,玛莎告诉阿维的是,在转狱前不久,杰西卡把一半的信撕了。而后来的情况更是走向了悲剧,杰西卡不到一个月后就因为吸毒过量死了。
克里斯没有受到母亲的信,杰西卡没有留给她自己的肖像,风筝终于断了线,但是,就像那些信箱里的信一样,没有写完,没有落款,没有寄出,但是,风筝总会被人牵在手里,牵着的风筝成为了象征,“也许画肖像这件事,并不是为了她儿子。或许,就和那反复出现的与儿子有关的梦一样,这是一个转瞬即逝的美好瞬间。”这也许是风筝最本质的意义,母与子天各一方,但是那根线曾攥在手上,这就是一种对话,一种打破隔阂的对话,一种重建情深的对话,“监狱里的图书馆”通过书和书的关系、信与信的交流,达到了人与人对话的目的,它所消解的就是“人人相互为敌的战争”和永远的孤独。杰西卡的故事以死亡终结,楚尼的故事同样是一场死亡,楚尼入狱之后想要重写自己未来,所以他在监狱图书馆钻研菜谱,并创造了属于他的第一批菜谱,但是在他出狱之后,却被人杀死在转角处,重写的未来变成了一场避之不及的扼杀,当阿维开车经过楚尼中弹的地方,他把汽车的里程表归零,然后想起了楚尼写给儿子充满了问号的诗:
你来自什么地方?
哪里有那样的地方?
“我住的地方,和楚尼中弹的街角,距离3.4英里。”这距离是生者与死者的距离,是自由和暴力的距离,也是楚尼无法逃离这场战争的距离,那些菜谱、那些诗歌其实也都变成了放飞的风筝,但是它却有收信人,那就是阿维,或者还有更多读到楚尼故事的人。而在这个意义上,监狱图书馆和风筝、信箱就具有了象征意义。阿维想起自己的叛逆人生,他回忆在中东政局动荡的时候,和几个犹太孩子不经意闯入了巴勒斯坦农民的地盘,遇到了几个农民的孩子,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就这样遇到了,那时有个叫摩西的孩子急中生智将一本书送给了巴勒斯坦的孩子,他们接过书之后露出了笑容,但是回来后却心有余悸,因为对于虔诚的犹太人来说,送书就是犯了大忌,“一本书只要带着上帝的名它就是神圣之物:每次合上它,或者不小心将它掉在地上时,都要亲吻它;当它破旧到难以修复时,要厚葬它。”而我们却将它送给了阿拉伯人——我们的敌人。
楚尼的死就是一种被“敌人”打死的死,而童年的这些回忆却开启了关于书的另一种意义,“为了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所有人民,亚伯拉罕创立了一个共同的宗教。那天,就在同一片土地上,就在某个洞穴边上,他的交战已久的两支后裔,搬出了他和真主的名讳,实现了真正的和平。”在阿维看来,这才是《圣经》的精神,不是亵渎圣物而是神圣之举,因为书的神圣之初就在于分享,不管是在民族和宗教纷争之中,还是在破坏社会的犯罪里,不管是在监狱里,还是在监狱外,“图书馆”让分享变得神圣,这种神圣去除了隔阂,消除了对立,即使没有直接对话,没有相互握手,但是当风筝真的放飞那一刻,触及灵魂的神圣性就已经建立起来,“我意识到了所有的白天的图书馆都有一个共同点:它们是孤独者和边缘人的天堂。”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49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