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10-25《穿着毯子的人》:一个人的“变形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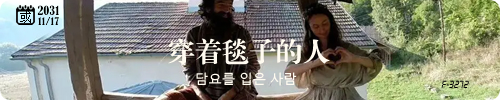
这是朴正美“现在”的状态:住在韩国偏远森林中的她,一个人砍柴,一个人生火,一个人吃住,一个人的生活没有纷扰,也没有牵挂,只有那只小狗陪伴她。从英国穿越欧亚大陆回到自己的国家,对于朴正美来说,这不仅仅是一次地理意义上的回家,也是内心真正找到了家的感觉,而这也许真正达到了“穿着毯子的人”的无念状态,但是从寻找到获得,从喧闹到沉寂,从焦虑到解脱,精神意义上的“回来”真的让她找到了曾经迷失的自己?
关于“回家”一个细微的、但属于本质的变化,体现在也许不经意改变的视角上:一路而来朴正美实践自己开启的项目,她用随身的Gopro摄像头在拍摄,这是对这趟心灵之旅的纯粹记录,她所遇见的每个人、每件事,都录入了这个设备中,跟踪、记录的意义在于让自己永远在场,更让影像呈现为一种沉浸的体验中,而沉浸的体验也让观众和朴正美一起在场,当朴正美通过这个第一人称视角记录、体验整个过程,世界是被她看见的,观众也看见了整个世界,但是这个世界又是完全主观的,观众在沉浸的同时又仿佛被这种主观性钳制了,更为不适应的是,这样的广角视角是变形的,而当朴正美回到韩国,隐居山林,这是视角发生了改变,不再是通过朴正美的主观变形镜头看见世界,而是变成了客观的镜头,更重要的是,朴正美自己成为被看见的对象,她也成为了这个世界的一员,而真正看的主体回归到了观众本身。
从第一视角的主观镜头到客观画面,这也许才是对这部电影“看见”的正常状态,而朴正美大部分时间的变形视角,也让这趟心灵之旅变成了一种存在偏差的变形记。首先的“变形”体现在对地理空间的探寻上,朴正美用几乎两年的时间穿越了欧亚大陆,从一开始的英国境内,到之后穿越英吉利海峡到法国、德国、波兰、斯洛伐克、匈牙利、塞尔维亚、希腊,在希腊的美丽海岛上朴正美迎来了计划实施的一周年纪念日,但是她的旅程并没有就此结束,她继续前行,从土耳其到伊朗,最后从伊朗抵达印度,最后飞回了韩国,见到了久别的父母。从工作的城市伦敦到最后回家的韩国,朴正美创造了一个人的历史,这趟“奥德赛”之旅对于她来说,首先就是地理空间上的改变带来的人生体验,它构成了第一重的“变形记”。
| 导演: 朴正美 |
为什么朴正美的计划会不断修正和改变?这就是旅程本身赋予的“变形”意义,它总是在遇见中不断丰富,在惘然中不停探寻,在挫折中不断调整,这就是第二重的“变形记”。朴正美是在伦敦工作中陷入了困境,而这种困境直接表现为财务危机,所以她大胆开启了一个计划:在英国能不能不花一分钱生活一年?“没钱就没有资格活着?”她曾经这样发出疑问,“这个项目始于一个绝望的问题:我将如何生存?”所以从一开始,朴正美的计划指向的是生存问题,而她也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反驳没有钱就不能活着的荒谬观点。没有钱但要生存,就需要食物,就需要住处,这是活着最基本的两点要求,于是她在朋友的帮助下从垃圾桶里寻找店家扔掉的食物,又找到了朋友一处船屋,当然也是从朋友那里得到了一辆免费的自行车,就这样,她的两个基本生存问题都得到了解决。如果按照朴正美的计划,她完全可以按照这种模式生存下去,每天都能找到食物,住处也不会构成问题,这样生活一年就可以完成自己的计划,她的挑战也会获得成功。
就像她从城市对食物的浪费想到了“消费主义就是浪费主义”一样,从计划实施的过程来看,朴正美收获的不是项目的成功,而是认识到了财富带来的分配问题,认识到了消费社会的不合理问题,甚至从无处不在的生存恐惧想到了世界面临的气候灾难、生态破坏、战争和冲突等宏大问题,这可以看做是朴正美问题思维的一次跃升,也正由于此,她的计划出现了变动,她不再只是为了挑战自己一年不花钱,而是有了更大的目标。当她骑车离开伦敦来到农场的时候,她的心灵之旅“变形记”正式开启。农场里的一切都是对现代生活的背离,自己种植蔬菜,自己发电,当然不再有所谓的消费主义;之后朴正美又来到了威尔士的一处村庄,村庄也是一个重返原始社会、体验原始生活的项目,在这个实验的乌托邦里,生活就是自给自足。从伦敦街头的垃圾桶里寻找食物,到在农场和村庄里体验自给自足的生活,这是朴正美计划的一次重大转变,个体的生存问题已经变成了人类如何摆脱困境的问题。朴正美对此的阐述是,“在相连的世界里,万物皆为一体,如果你我合为一体,那么就没有什么可畏惧,竞争消退,也没有必要过度攫取或占有,我们可以相互保护,彼此珍惜,像家人一样没有边界或歧视。”
按理说,朴正美在这种自给自足的模式中能找到属于自己想要的东西,但是她却选择了离开,大约是过惯了城市生活,当面对连洗澡都成问题的生活,朴正美充满了怨言,而那一锅错把秋水仙当韭菜而煮熟的汤,像是一个隐喻,大家以为是美食却纷纷中毒,这也宣告了一种“误读”的存在,自给自足的乌托邦生活对于朴正美来说,就是一种关于理想的误读。所以她再次踏上了旅程,而从这里开启的旅程更多了一种未知性,最开始“我将如何生存”的物质性问题变成了对灵魂的拷问:她在陪伴了她一段路的朋友离别之后,不知道自己该去何方?在捷斯洛伐克“彩虹节”聚会中,她总感觉自己无法融入,在一个月的活动结束后她更是感到茫然;遇到了开着卡车旅行的嬉皮士,她加入到了这19个人的团队,一路伴着欢笑,但是朴正美似乎也并没有找到归宿感,最后嬉皮士们又分道扬镳,而她则在和一位灵修者对话中,提出了关于人的自由和精神意义的问题,灵修者告诉她的是如何让灵魂安息下来,如何让自己看见被隐藏的真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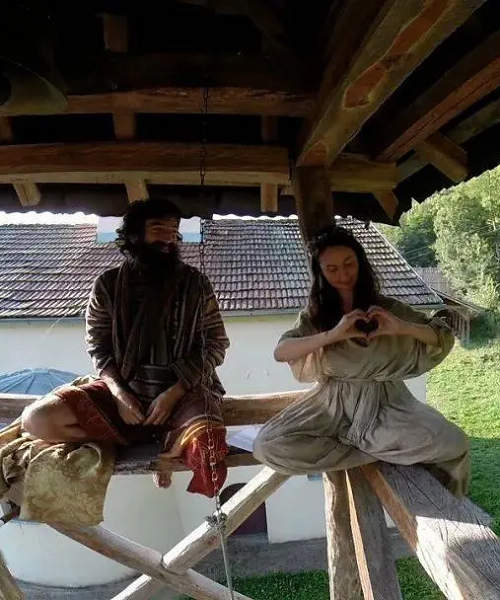
《穿着毯子的人》电影剧照
这似乎是朴正美心灵之旅的第三个阶段,在她一次次对于“我将去哪里”这个问题的发问中,也一次次想起灵修者说出的话,在不断的体味中,朴正美似乎领悟到了什么,于是在不断延伸的路线中,在不断丰富的体验中,朴正美似乎找到了她想要寻求的答案,“我们存在的方式始终是意识,当意识汇聚时便变成了爱。在充满爱的场域中不必过分在乎物质的得失,一切都会有一种声音来带领我们慢慢向前走。”只有在这种爱的作用下,才是真正的回家,朴正美终于找到了内心的家,也在内心回家的同时,她最后搭乘飞机飞回到了自己的家。精神世界的家和现实意义的家,在最后汇合成一体,但是对于朴正美来说,这不是结束,而是真正的开启,从此她隐居山林,从此她独自生活,从此她把世界当成家,从此她成为了“穿着毯子的人”——完全是在精神意义上的“苦行僧”。
“穿着毯子的人”,他具有的苦行意义就在于“毯子”具有的象征意义,在白天他穿着毯子,在晚上他盖着毯子,毯子成为与自己相伴的永恒存在,它去除了一切多余的存在,在白天和黑夜、穿着和盖着的状态中成为真我的标志。当朴正美归隐山林,似乎就是这种生活的写照,但是朴正美真的摆脱了一切物质的束缚,真的完成了自我回归的“奥德赛之旅”?并不是要怀疑什么,只是在这个客观视角真正打开之前,所有此前所做的铺垫真的不是某种意义上的行为艺术?一年不花钱而生存下来,这个计划被朴正美称为项目,就有着某种形式主义的嫌疑,之后体验自给自足的生活,总感觉自己无法真正融入,而所谓灵修者对她的解说,似乎并没有真正打开心灵之门,那种对家的感悟也并没有大彻大悟的境界感,反而在第一视角中,在第一人称叙述中,主观主义所呈现的可能就是一个变形的世界,自由、自我也可能只是概念的有限拓展。
而当朴正美用自己的视角带领大家“看见”对面的世界,除了主观主义的变形之外,更重要的是选择性过滤:朴正美开启不花钱的计划,并非真正不花一分钱,比如朋友提供的自行车、船屋,都是朋友友情提供,但是在某种意义上它也是一种物质保证,为朴正美解决了本需要钱来解决的问题;她在一年多时间里横跨了欧亚大陆,真的没有花一分钱?没钱真的能顺利过境?没钱如何给手机充话费?也许朴正美所说的不花钱,是不花大钱、不花不必要的钱;在一路的旅程中,除了在伊朗境内遇到了图谋不轨的摩托车男子,她所遇见的所有人都是友善的,都是慈爱的,都是有着人道主义精神的,无论是嬉皮士,还是普通路人,都表现出人的真诚和善良,这又如何可能?也许朴正美通过信息的过滤,留下这些美好的瞬间,就在于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家人感,但是,一路上遇到的困境、危险和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对立,也许在另一个意义上更能让人回归内心,更能成为“穿着毯子的人”。
变形的视角也许就是那张毯子,为了记录而记录,为了行为而行为,为了自我而自我,当真正不需要作为标志的毯子,人就是那个“苦行僧”了,而在最后把自己作为世界一部分的客观视角中,朴正美重新与自然连接,敞开心扉,追随内心,寻找着真正的自由和内心的平静,也许那个时候,连“苦行僧”也只是一个无用的称呼而已。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3570]
思前:《三联画》:书写与差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