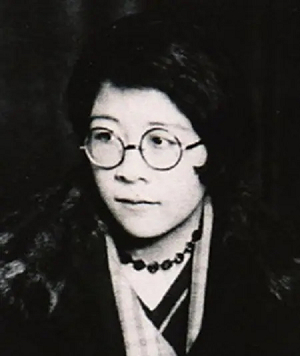2025-10-25《我是宿命的放浪者》:心焦无名欲书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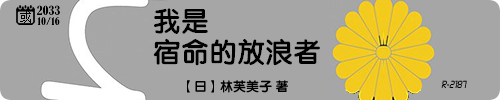
下辈子投胎,我真想变成花。如果要当花,我想化作鱼腥草。
——《生活》
狭小的书桌上,除了那些杂志和书本以及自己创作的笔记本之外,还有一只小杯子,杯子里插着小雏菊、油菜花、矢车草和康乃馨,“它们衬着桌灯的模样,展现出花朵真正的美,让人望而入迷。”花朵是安静的、美好的,甚至是浪漫的写照,所以林芙美子想要自己成为一朵花,这是她下辈子的理想,如花一样的存在。之所以发出如此的感慨,并不仅仅花是安静、美好和浪漫的象征,更在于林芙美子对人生的某种感触。
“女人的青春便短暂多了。”那时的林芙美子三十二岁,身边那些年龄相仿的男人们“个个都还像个苍绿青年”,所以对比之下,女人的青春就像是杯子中的花儿,虽然安静、美好和浪漫,但是如青春一般,短暂开放之后也许就是凋零。三十二岁对于林芙美子来说,是个美好的年龄,她在二十七岁时出版了自传体长篇小说《放浪记》,从此确立了文坛地位,但是她也许不会知道,16年后她的生命会戛然而止——由于过度劳累导致心脏旧疾复发,1951年6月28日她在家中病逝,年仅48岁。一个人无法预料自己生命的终点,但是看上去对生活充满美好期待的林芙美子的确从杯子里那些如青春盛开的花儿看到了某种悲剧性的存在,而且是关于女性的悲剧性人生。
这种悲剧性人性来源于林芙美子自身的遭遇:关于她的出生有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法是她于1903年出生在门司市大字小森江,另一种说法则是1904年5月出生于下关,还有说法是出生于当年6月,这种说不清不是别人对她的模糊认识,而是林芙美子自己觉得“没有故乡”的表达,因为她出生后就不被父亲承认,她是以私生女的身份跟了母姓;7岁时便随母亲和后来的养父四处更换住所,对于林芙美子来说,童年就是漂泊的回忆;中学毕业之后的林芙美子和初恋情人来到东京求生,她做过帮佣、餐厅侍女、小贩、广告员,看尽了社会底层的人生百态,一年后又被男友抛弃,而之后经历了几段失败的感情和婚姻,虽然让她积累了写作的素材,淬炼了她细腻、柔和的写作风格,但是命运并没有眷顾于她,48岁就因为劳累导致疾病复发,永远离开了这个对她不公却她却充满激情和依恋的世界。
“昭和时期日本女性文学第一杰作”,集子封底的这句话注解的是林芙美子在日本文学史上的卓越地位,小小的集子选录了她的四部短篇小说和四篇散文,没有代表作《放浪记》,也无法管窥一代作家的真正写作水平,从这几篇文章来看,这一赞誉显然还是言过其实。但是“女性文学”这一定位还是比较符合林芙美子的创作主旨,在这篇《生活》的散文中,林芙美子之所以想要自己下辈子成为花儿就是希望女人的青春能够延长一点,能够和男人一样永远是“苍绿青年”,而这种希望的背后在某种程度上也是通过生活的美好来忘却那些不快的人生遭遇,她用“心焦无名欲书写”来形容自己创作,“我不仅无名地感到心焦,更是几乎每到深夜便坐在书桌前,在这般游手好闲的生活中写着小说。”在和女佣一起完成家务之后,在和家人互道晚安之后,在把家里的锁都栓上之后,林芙美子就开始进入自己的时间:她说自己不关心政治,她说自己曾自暴自弃过几次,现在则专注于埋头苦写,“像是进入了无我的状态一般。”而且她还把写作看成“像宗教一样的东西”,声称自己就是一个万年不变的文学少女。
喜欢写小说,喜欢记日记,喜欢画画,喜欢旅行,“如果有机会远行,我想一个人漫无目的地四处走走。”这就是林芙美子的“生活”,这是惬意的、安静的、自我的生活,当告别了曾经遭遇的不公和自暴自弃的自己,林芙美子沐浴在暖阳之中,实际上这种生活就是她所定义的女性生活,她所写下的当然她所认为的女性文学。在散文《恋爱的微醺》中,已经嫁做人妻的林芙美子还希望自己遇见其他男人,“否则,怎么会发生以处子之身出嫁的女性却又爱上其他男人这种事呢?”在她看来,这就是新颖的恋爱,是对懒惰且死气沉沉的恋爱的一种反叛,一方面,她认为恋爱注定是一个悲剧,“年幼时的恋爱因花朵的根部尚且短小、青涩,总是留下满心遗憾,如同餐点尚未吃尽,食盘便被收走一般,余下满是惋惜的回忆。”另一方面,她也期望着自己生活在“恋爱的微醺”的状态中,甚至希望随着自己年龄增大、阅历丰富、结交更多男性之后写出“恋爱论”,“不久后,我想写篇波澜壮阔的恋爱论。”
| 编号:C41·2250914·2357 |
在林芙美子的笔下,生活如沐浴在暖阳中,恋爱要不留遗憾更不想成为悲剧,这就是对自我的一种定义,而在散文《平凡的女子》中,林芙美子更是强调了她心中的女性,她说自己会帮家人下厨、洗衣、打扫,虽然这些并不是让人愉快的事,对女人来说也不是光荣之事,虽然她认为每一个领域中都有一两个对现实不满的女子,她们都希望自己“能留着小胡子”四处闯荡,虽然她希望自己能生两三个孩子,因为每次见到将孩子绑在背上工作的母亲,都会认为日本的女性很了不起,做家务、生孩子以及出去走走,都是属于女性的生活,甚至作为女性只能按照传统来为自己定义,但是林芙美子还是表达出了一种女性意识,她认为,“许多妇女运动的参与者,都是在生下孩子后才出现思想上的转折。”甚至她很像仿效那些通过和丈夫分居、在便餐店买饭菜或者把内衣给洗衣店的女人,因为这样的话,女人的工作会更加顺利,而这何尝不是女性对独立和自由的追求?而且林芙美子批评了所谓的女知识分子,她们并没有真正理解市井生活中的平凡妈妈,当她们轻蔑地误解了“优美与温柔”的真义,也只是在口头上讽刺和攻击,“想来真是可笑”,“所谓的温柔并不代表过于依赖男性,也一点不虚泛,因此那些一味认为生活很烦人的女知识分子们让我不得不生厌。”
没有强烈的女性意识,但林芙美子的确在重新定义女性,并且在寻找着成为这种女性的方法,这就是她“心焦无名欲书写”的一种生活态度。如果说散文中的她是温柔的、安静的,有着文学少女的痴情,有着对生活的期盼,那么在她的小说中则呈现出关于女性更为复杂的面向。《幸福的彼岸》中的信一和绢子在被媒人介绍认识之后很快走到了一起,这就是一种好感,而且结婚之后的两人也沉浸在幸福之中。但是这“幸福的彼岸”并不是仅仅靠好感支撑起来的,信一比绢子年长七岁,去年因为在战场上失去一只眼睛而返乡,但是绢子并不嫌疑独眼的信一的,相反她看到了信一的坦诚和体贴。后来信一还告诉了绢子一个秘密,自己还有一个孩子,起初绢子觉得自己结束帮佣的生活而拥有自己的家,是生活给她的馈赠,但是得知信一的这个秘密之后,她又觉得自己跌进了不幸的深渊中,但是从信一对孩子的爱,她又看到了生活的希望,甚至在信一身上也看不出他所经历的那种黑暗,于是她想着自己也要生几个孩子。这是经历波折的幸福,是女性在黑暗和困顿中重新发现的美好,林芙美子在表达这种女性觉醒的意识同时也指出了另一种女性生活:绢子曾经做过工的小姐,给她送来了结婚礼,在写给绢子的信中说自己并不比绢子幸福,“结婚后,日子过得比在娘家时辛苦数十倍。”
|
| 林芙美子:写小说像是进入了无我的状态 |
有钱家小姐和绢子生活的对比,也揭示出不同女性的生活,而在小说《婚期》中,林芙美子更是对所谓女性“命运”进行了解读。登美子的妹妹杉枝和安并安排了相亲,杉枝喜欢得不得了,很快他们就结婚了,但是登美子发现有人曾给她说媒时安排的男人就是安并,但是她没有去,现在想来,那个和安并在一起的女人也许就是我,“登美子不得不承认命运确有其不可思议之处。”而安并在见了登美子之后,认为她虽然比不上杉枝漂亮,但是气质高雅,是自己一直希望追求的女子。妹妹和安并结婚之后,登美子还是没有去找对象,不幸的是,杉枝去了中国上海之后得了败血症病逝了,而之后的登美子就收到了安并的一封信,他想要娶没凳子为妻,登美子同意了,“我,随时都可以嫁给你。为了能早点办好结婚仪式,请你去跟我母亲提亲。”她这样对安并说。从之前的错失到最后走在一起,看起来就是命运开的一个玩笑,但是在这命运背后却是女性对美好的向往,以及不让机会再次错失的勇气。
《幸福的彼岸》和《婚期》都弥漫着一种温情的气息,它们都成为了林芙美子所定义的女性生活,但是,“心焦无名欲书写”的林芙美子一定也是“心焦”的,这种心焦在《晚菊》和《手风琴与鱼之小镇》中得到体现,其中反映的是两个主题,一个是女性生活中的困境,另一个则是和“战争”有关的社会现实。《晚菊》可以说是《幸福的彼岸》和《婚期》的背面书写,主人公是19岁就成为艺伎的欣,现在已经五十六岁的她早就失去了女性应有的美好年华,青春短暂,而且一去不复返,“年龄增长后,她发现自己的美貌渐渐出现改变。”在这期间她经历了什么?经历了战争,也经历了自己的虚荣——沉溺于对金钱的追求,当然她也经历了感情,为了和小自己不少的田部见面,她那时甚至两度前往广岛拜访参军的田部。但是现在的她虽然还自认为年龄增长美出现了不同的风韵,但是当田部到来,不再和爱情有关,他是来向她借钱的,“两个丝毫不觉兴奋的男女,这般百无聊赖地重逢,让她感到失望又无奈,泪水像毫无预警、神出鬼没的恶徒般淹没她的眼眶。”
那个曾让她刻骨铭心的田部,已经变成了低俗无趣的男人,她不解田部为什么没有战死沙场,她也不后悔当初和他的分手,而看着田部离去,她才知道改变这一切的就是战争,“这场战争,让所有人的心态都为之大变。”她从战前的少女变成了老去的女人,只能发出“余心有感,如需将己似他人,不如锦簇化蔷薇”的感慨,而田部也从战前让她心动的男人变成了低俗的男人,“她被浓烟呛得直咳嗽,粗暴地拉开了四周的隔窗与拉门……”这就是被改变了生活的“晚菊”的命运。而实际上,对战争的某种谴责也在《幸福的彼岸》中,信一不就是被战争夺去了一只眼睛?但是他被战争改变的生活却因为自己的善良和体贴、因为绢子的理解而拥有了“幸福的彼岸”,但是田部和欣却在战争的摧残中失去了生活的希望。《手风琴与鱼之小镇》无关爱情,甚至也无关女性,它只是以“我”这一女儿的视角看见了小镇的凄惨生活:父亲弹得一手手风琴,迫于生计一家三口来到小镇讨生活,父亲每天出去弹着手风琴,然后喊着“一二一”卖着各种药。这是战后的生活,或者是战争造成的生活,但是父亲赚钱很大一个原因就是让我能有机会读书,在他看来这也是改变命运的最好机会。我成了六年级的学生,但是学校里同学嘲笑我,老师欺负我,我终于逃离了学校,当有一天回家母亲告诉我的消息是:父亲被警察带走了。当我透过警察局的窗户,看到父亲被巡警打着耳光,还被不停地骂着“混蛋!混蛋!”在母亲的呼唤中,我听到了耳边回荡着的齿轮声,“嘎嘎”作响就是这个社会的暴力声音。
《手风琴与鱼之小镇》是这部小说集中最为悲惨的一个故事,没有温情没有希望,更没有幸福的彼岸,这一切发生在战后,但其实更像一场正在发生的战争,生活所迫是命运制造的恐怖,学校嘲讽和欺负是社会制造的不公,巡警打人是法律制造的暴力,这就是林芙美子所说的“心焦”,“这场战争,让所有人的心态都为之大变。”而写下这一切,是一种控诉?但是林芙美子强调对政治不关心,这只是她回到个体的、女性的生活遭遇?但是她为什么对军国主义存在着更为暧昧的态度?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45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