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02-13 《骆一禾的诗》:谁的河流上飘落着墓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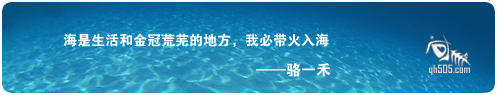
来吧,让我来说:生
对于死
是有毒的,因为他满身鲜花
在死亡中过于醒目
——《塔》
“时光的大门”一直不曾打开,世界就提早关闭了。而哪里是生存之地?曾经的,现在的,还是未来的?春天的,夏天的,还是冬天的?时间和空间都消逝在诗歌尽头的时候,谁会带一柄桨,像一个圣者,去“启示海洋”,当“依水的事物逐一地迤逦展开”,而世界也就在焚火中燃烧,没有人看见,没有人听见,没有人说话,“海是生活和金冠荒芜的地方,我必带火入海”,而留下的,终将是我们无法触摸到的魂灵。
魂灵是在暗处,是在有毒的死上面,骆一禾,这个名字总是和“海子”连在一起,连死也一样,所以在时间的一侧,过于醒目的是海子,是轰鸣中卧轨自杀,也是满身开着鲜花的寓言,而对于骆一禾,更多是海子诗歌的阐释者:
海子写下了《太阳·七部书》,推动他的“元素”让他在超密态负载中挺进了这么远,贡献了七部书中含有的金子般的真如之想,诗歌的可能与可行,也有限度的现身——长久以来,它是与世界匿而不见的。海子的诗之于他的生和死,在时间峻笑着荡涤了那些次要的成分和猜度、臆造之后,定然凸露出来。
1989年5月13日,骆一禾写下了这篇《海子生涯》,对于“光在大质量客体处弯曲”的海子诗歌进行了阐释和定位,就在一个半月前,25岁的海子在山海关附近卧轨自杀,“饥饿的胃中仅有两枚腐烂的橘子”。这应该不是一个寓言,年长海子三岁的骆一禾忽然闻到了那浓烈的死亡气息,如此经典,如此醒目,《海子生涯》是一个句号,他不小心把自己也推了进去。朱大可说:“五月十四日,骆一禾在京城广场上猝然昏迷,十八天之后,他尾随海子而去。他走过黑暗的门槛,‘眼望着家乡 ’。”是的,骆一禾曾经说过,“生死是一样的震颤”,而在“生之于死,死之于生”面前,只是一场舞。对于骆一禾的死,朱大可用了“革命性病故”这个词,他说:“并非是用疾病去推翻一种心力交瘁的个人存在,而是要以死对另一次死亡作出决然的阐释。”
以死对死作出阐释,太过沉重,而其实,我们都在遗忘这样的病故,遗忘这样的悲剧,甚至,也在遗忘文本。在所有的陈述中,对于骆一禾28岁年轻的生命都用身体的病故作为总结:1989年5月31日因突发脑溢血去世。这是一种还原,还是忽略?1989年的天空有过血迹,那个敏感的时代最后反而被历史抽去了,找不到生存之地,找不到固有之血,甚至于他们的名字。诗歌的内部,谁还能够告诉你,革命是一个多么冒险的词,它会带走你的身体,你的诗歌和你的“世界的血”。所以,海子用诗歌活下来了,尽管有毒,他的死也闪耀着光辉,闪耀着“先知的言说”,而骆一禾,始终在时间的河流里,成为一个言说的“弱者”:
我不愿我的河流上
飘落着墓碑
我的心是朴素的
我的心不想占用土地
——《生为弱者》
缺失的到底是生命的那一个部分?是真理?是上帝?还是英雄?“英雄离真理都是很远的”,那么我们在寻找的可是死亡之下必然的遗忘?而在23年之后,用简单的文本寻找那个“革命性病故”,显得有些茫然。72首短诗、长诗《世界的血》和《海洋》节选,已经用构筑了一个纯洁、简单、被生卒年月固定的人,他面带微笑,和善地注视着封面外的世界,其实没有茫然,都是向往和期待,干净的脸,干净的头发,干净的眼神,让人想起爱和生命的荣耀,“我们一定要安详地/对心爱的谈起爱/我们一定要从容地/向光荣者说到光荣(《先锋》)”,那么安详,那么光荣,谁还会想起那个被中断的时间档案和死亡坐标,就像《生日》里的那个肖像,“给我们无边的晴朗”,因为那里有“勇敢的微笑”,有“女孩子们的健康”。所以你不必奇怪西渡在《编后记》里说:“新诗之有健康的风骨,也许当从骆一禾开始。”
“也许”是一个模糊状态,除了“春天洁白如玉”,除了“痛饮流畅的水果”,除了“世世代代健康的遗忘”的麦地,除了“玉米和盐/还有一壶水”,对于骆一禾来说,他看到的意象,还有“中伤的母豹”,有“鱼群般的少女”,也有“酒一样的歌子”,和“青饲料的晚餐”,而对于一个追随生命之荣耀的诗人来说,死亡之后是更多的财富:“你们的双手更真实/因此我留下的还有旗/清水和烈火/血液的战场:爱情和生命”。我们仿佛看到了那个带着桨的圣者,告诉你爱和生命,而他自己却“带火入海”,选择一种超越文本的方式,滑向比海更深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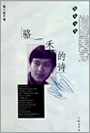 | 编号:S29·2120112·0854 |
必然要涉及一个主题:生与死。这其实并不是个体之死,而是文明、精神和世界本体的生与死,在骆一禾看来,是先死而后生,死是一个过程,也是一种诱惑,“是的,我不知道命运的突然/不知道死亡怎样来临”,所以死的形式多样中,诗歌在升华,在进入本体之前,必定是一个迷,“为了但丁/死亡也不能阻止,死亡是在到达的下面/和死亡我们只能谈论骨头”,所以对于生命的消逝,倒成了必然的探究方式,是一个追求自在高度的行动,而骆一禾着迷于那一种“焚”:“我就是大地上的 炽热的火焰/焚烧着 自焚着”,“我就是那个叫做:焚/的性命,一道自强的光明”。当死亡变成预设的一出戏,成为生命过程中必然的步骤,倒不是那么恐怖了,它抵达着生命的彼岸,但是要再能看到它回来,就是走向圣者之路,甚至在诗集的第一首诗中,在1981年10月8日的文本中,就有了这样的启示:“有一个神圣的人/用一只桨/拨动了海洋/蒙昧的美景/就充满了灵光(《桨,有一个圣者》)”而那海洋是澎湃着的力量,是最后的归宿:
所以我既不是在刑台之下
也不是在朝霞之巅
只有大海没入大海,大海变更深
万物之流一片轰轰作响
另一个世界正在轰鸣
另一个世界就是死之后的新生,“作为消失的生命,我把理想留在灯里”,而在骆一禾构筑的世界里,新生是一种强大的力量,是一种向上的信仰:是“当脚掌证实心脏的时候”的长征,是两种狱中的“舞蹈激浪翻腾”,而更多的新生是“粘土的坛子”,是“坯子嵌入黑色屋瓦”,是“心头爽朗地微笑”,所谓新生,是生长,是真实,是诗歌,是火焰,是屋宇,是生之于死和死之于生的无间,那么,个体之死就是为了完成言说的最好的归宿。“在我的一只手和一只手上/我是否在写诗,我是否活着/不是前人的,也不是后人的(《观海》)”。这句话仿佛是在否定着那些后来者对于他的诗歌“背向前人,也背向后人,同时也背向其同代人的诗歌道路”的健康阐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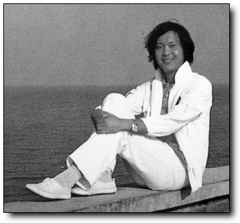 |
| 骆一禾,在水之上 |
在巨大的死亡寓言下,我一直在好奇地探究他在诗歌之外的另一种向度,那就是真正的生命归宿,那个心中的“家乡”。他的父亲是著名经济学家骆耕漠,家乡就在我我阅读这本书的城市之边,只是很早就离开家乡去往北京,所以对于骆一禾个来说,父亲对于家乡的记忆是不会传递到他的身上,他对遥远的所谓籍贯也根本没有认同感。在简历上,骆一禾就出生在北京,小时候随父母下放河南农村,可以说他没有到过父辈出生的地方,家乡也是早已是被移植的物理空间而已,而他的父亲自从离开家乡之后,也再也没有真正回过家。在2009年骆耕漠逝世的时候,我们曾收集过有关他的资料做了一个专题,或许只是为了有限地纪念,而现在,那块土地上关于他的标识越来越少,而他的子孙基本上都在故乡之外的土地上繁衍生息。其实,家乡的别离和断裂感,对于他的父亲来说或许更为强烈些,而对于骆一禾来说,则是精神上的断裂,是人对于最后归宿的茫然,“死亡葬身之地的年月/家乡的太阳必然一无遗漏(《零雨其濛:纪念两个故人》)”,读着这样的诗,我总是想到漂泊,生命的漂泊有时候无影无踪,甚至死,土地上也没有墓碑,而国家主义者则把死看成纯粹的生理现象,“叫一个人坠落就是叫一个人坠落”,有时候,真的是一种苦涩的痛。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45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