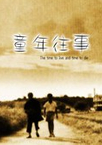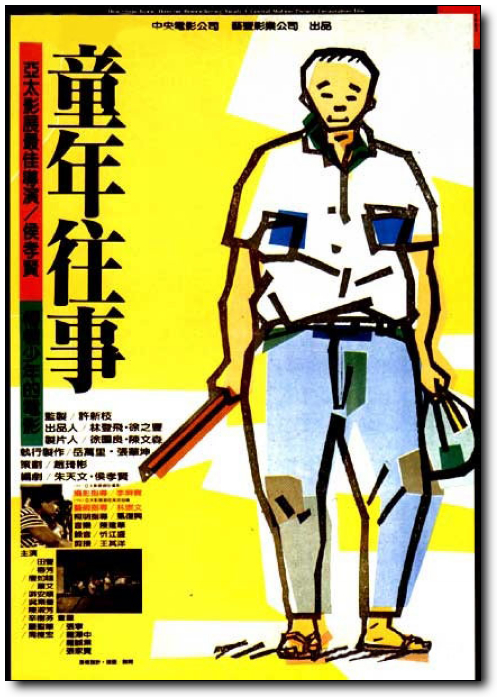2014-03-07 《童年往事》:外省移民的成长和死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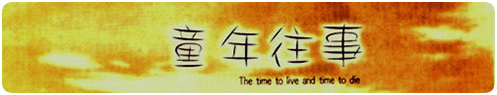
英文片名:《The Time to live and time to die》,时间是从出生到死亡的长长线段,时间是从断裂到融合的缓慢过程,从广东梅县到台湾新竹、凤山,这是一家人绘制的时间轨迹,这里有父亲从大陆到台湾的亲历,有母亲在孩子面前的讲述,有祖母蹒跚寻找回家之路的回望,而新一代外省移民在对生的模糊记忆,对死的不安见证中,完成了“台湾意识”的过渡与融合,也完成了属于自己的成长仪式。
“这部电影是我童年的一些记忆,尤其是对父亲的印象。”这是属于“我”的故事结构,而“父亲”无疑成为我童年记忆中最重要的一个符码,父亲是广东梅县人,在民国三十六年的时候,因为偶遇台中市的市长,便被邀请当了秘书,那时我只出生四十二天。而这一次的“偶遇”使一家人生活轨迹发生了改变,母亲带着全家来到了台湾,从此不管在新竹,还是父亲因病搬到凤山,一家人都没有再回去,父亲和我的出生地,以及全家曾经生活的记忆,都被地缘而隔开了。这是父亲政治生活的一个转折,但其实不管是离开大陆,还是移民到台湾,对于父亲来说,并不是为了某种政治的目的,甚至可以说,在一种被割裂的生存状态下。对于父母来说,对于大陆只剩下一些记忆,而这些记忆被激活也总是通过大陆辗转而来的信件。建元的信说到了大陆封锁,父亲便回忆起和他一起上大学时的情形,说建元的父亲生建元的时候,满屋子里都市鱼腥味,好像他家就是卖鱼的。后来又收到安姑的信,说大陆在大炼钢铁,但最后都成了一堆废铁。信息封锁、大炼钢铁,这些政治事件已经融入了彼岸的生活,但是对于父母来说,这些信件上的点滴只能是一些片段,就像他们离开的故土,已经成为一个“他者”,而母亲的那句“当初带他们出来就好了”的心里话更多是一种想象。
|
| 导演: 侯孝贤 |
 |
父亲总是坐在那把老式的藤椅上,读着辗转寄来的信,拖着气喘越来越严重的身体,而耳边听到的是充满着政治标签的口号,这不仅是他的生活片段,也是一家人生活的写照,村子里总是经过那些武装着的骑兵,公共场合禁止说起的闽南话,学校那些懵懂无知的孩子口中说出的“我们要反攻大陆”的口号,以及满是政治宣传口吻的虚假战时报道,充斥着他们的日常生活。而生病退养在家的父亲,一个月的薪水只有620元,除了自己理发零用的20元,其他都用作了全家的日常开支,这是拮据的生活,所以幼年的我会从母亲的包里偷出钱去,藏在村口的那株大树下;我和弟弟们一起去捡电力施工丢弃的铜线卖钱,或者有时候我还会去偷电线拿来买包子;而姐姐也是因为家里拮据,最终被中断了到台北读女一中的学业,早早嫁了人。姐姐总是回忆起自己报考台女中而被录取的那段往事,只是最后对于放弃是哀愁的,是含着泪的,母亲说,女孩早点工作赚钱,不用读女中,只要读师范就可以了,而一旁的祖母也说,读书了没用。
生活的拮据对于父亲来说,是外省移民身份的另一种压力,这种压抑和压力带给他的是沉默,是叹息,是疾病,而那个停电夜晚突然而来的死亡则把这个家推向更加深重的现实。姐姐的一声“爸!”是点亮蜡烛之后最沉重的一声呼唤,父亲依旧在他的那张藤椅上,头靠在那里,却已经望不见天。母亲的哭亲和祖母掐着他的额头,是最后的施救,但是医生摇头宣告父亲的死亡。从大陆到台湾,父亲见证了一家人的转折,他活在断裂的现实里,直到最后死去,他依然没有找到自己的归宿。
|
|
| 《童年往事》电影海报 |
而我作为随父母来到台湾的新一代外省移民,父母有关的记忆是模糊的,所以在父亲的死亡面前,我和那些小弟弟一样,是无声的,甚至是冷漠的,和姐姐、哥哥阿忠以及母亲、祖母的悲伤不同,我们只是看见了这快速降临的死亡,但是这种死只是父亲作为一个断裂的知识分子的死。父亲之死隐约地代表着一代人、一个时代的终结,而我也从童年的懵懂中成长起来,这种成长当然面临着一种本土化的困境。我的小名叫“阿孝”,是祖母小时在找我时喊的名字,在某种程度上祖母的语言里也含着那一段迁徙的记忆,所以小时候会被别人取笑为“大卵巴”,父亲之死是童年记忆的彻底泯灭,转身一变,我已经变成了靠在村口大树上吃着甘蔗准备实施敲诈的那个青年,这是一种本土的融入,但是这种融入又带着某种叛逆。
那个在凤山的家已经不是当初临时安顿的场所,而完全成为与自己成长有关的地方,学校里给别人抄作业可以收点零钱,纠集同学殴打教训不听话的同学,还恶作剧放老师自行车的气。混帮派、泡马子、打撞球、因副总统陈诚大敛而与老兵起冲突,并偷偷砸人家玻璃等,无不展现我在青春期的血气与纯情,也展现着我想要融入的心情。当然对于青春来说,性意识的懵懂也成为不可绕开的现实,我会在厕所里偷偷读禁书《心锁》,半夜会“画地图”,偷偷起来自己洗干净了内裤。或者和那些伙伴们去“红灯区”,穿上新衣服,照镜子,学着抽烟,这是出发前的仪式,而5块钱的一个红包反倒是对于我是处男的奖励。当然,除了这些和肉欲有关的性意识,也还有对女孩的朦胧向往,女孩吴素梅成为我寄托稚嫩情感的一种归宿,跟在她的身后,或者写一张“我心爱的人,你在哪里?”的纸条,在大雨中守望。而这样的青春故事总是伴随着某种挥之不去的哀伤,而另一种死亡的出现,把我真正拉向了成长的仪式。
母亲叫我买酱油的时候,发现石头上长了小瘤,我半夜遗精洗内裤的时候,母亲去在流泪给出嫁的姐姐写信,“医生说要切片,可能是喉癌。”生与死,成长与衰亡,总是不经意的并列而生,而母亲眼泪的时候,映照出的是父亲挂着的遗照。舌头上的瘤、可能的喉癌,其实母亲的身体之便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隐喻。虽然他和父亲一起从大陆来到台湾,也一样挂念着那边的亲人,也也有某种割裂的感觉,但是她和父亲不同,她的亲历更是一种“说话”,她是讲述者,是对于过去的言说。她回忆她的第二个女儿阿琴,因为奶水不够,女儿去除了敬神的食物,最后又吐又泄,吃了药后,第二天就死了;她回忆大儿子阿忠,小时候也是因为吃的原因落下一身的病,所以现在瘦瘦弱弱的,连当兵也不能通过体检;她回忆自己的和父亲的婚姻生活,“身体要紧,其他都是假的。和你父亲结婚时不知他有病。结婚二十年,服侍了他二十年……”她总是在讲述,讲述那些有关生的故事,讲述有关身体的遭遇,讲述的背后是另一个断裂的过去,而那降临到她身上的疾病又让她丧失了说话的权利,姐姐带着母亲去台北的医院看病,回来后姐说医生本来要把母亲的舌头割掉的,但是母亲怕从此讲不来话,所以不肯。而这其实是母亲自我安慰罢了,台北回来之后,病情每况愈下,呕吐取代了说话,最后离开了人世。
对于我来说,母亲的死比父亲更为真切,父亲都是埋葬在心中的那种压抑和忧伤,那些断裂的记忆只在他作为个体的生命中,而母亲用讲述的方式慢慢还原一个有关身体和生命的童年,所以在父亲猝死的时候,传来的只有祖母、母亲和已经长大的姐姐的撕裂的哭声,而我和弟弟们只是呆呆地站着,像是和自己无关;而母亲之死,对我来说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痛,在死亡的仪式上,我的眼中满含着泪水,意识到了生离死别的滋味。而在这种生离死别中,有关生命,有关成长逐渐清晰起来。在一家人整理母亲的遗物时,有送给阿忠结婚时的首饰,有邻居叶太太的会钱收据,也有父亲曾经住三年就想回去的愿望,当然还有母亲守着的父亲秘密:“爸爸有肺病,碗筷都和你们分开,不是不和你们亲近,是怕病传染给你们。”读罢,一家人恸哭,其实,割裂的现实后面是亲情,就像那回不去的故土,何尝不在那一代人心里成为永远的遗憾。
但是,祖母似乎有着更为根深蒂固的乡愁,和一家人来到台湾,对于她来说,反倒开始了寻根之路,给我命名叫“阿孝”,坐着三轮车到大陆去,或者叫上我走上几十里的路去找“梅红桥”,目的就是“回祠堂,拜祖先”,步履蹒跚的祖母带着年幼无知的我,行走在那条无人的路上,却不是孤寂,一路上祖母倒是兴奋的,而我从路边采摘来的芭乐,在祖母手里变成了杂技的道具,让人无限快乐。这或许就是遗失的记忆,它本来属于祖母,而祖母又以这样的方式返回到我的身上。根深蒂固的祖母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除了看着我们成长,看着父亲母亲的离世,也看着自己日渐衰老,包银钱成为她走向死亡的最后仪式,“要带到阎王那里去。”对于她来说,这是一种生命归宿的寄托,但是她属于更为久远的时代,和这样的现实几乎完全被隔绝了,所以,最后她的逝世几乎连仪式也忽略了。“直到有一天,祖母的身上爬满了蚂蚁,不知道她去世多久了,躺在榻榻米上。”身上爬满了蚂蚁,死的时候还保持着睡觉的姿势,似乎没有痛苦,没有挣扎,用一种无声的方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而这样的死亡,在我眼前已经变成了一个传说,当收尸人来的时候,祖母的另一半身体已经溃烂,他们狠狠看了我们一眼,心里似乎在骂“不肖子孙”。在这无声无息的死亡面前,在这告别旧时代的归宿面前,我却在用自己的行动融入现实,本来可以被学校保送进军校深造,但是我因为吴素梅的一句话“等你考上大学再说吧”,而最终决定参加大学联考,但这仅仅是少年的意气,仅仅是青春的冲动,大学联考失利之后,吴素梅最终搬到了高雄,懵懂的爱情从此不复存在,而现实是不是在我的成长中接受了我?祖母的死去是一个陈旧年代的结束,更象征着家庭的分崩离析与理想的破灭。
从亲历者的父亲抑郁而死,到讲述者的母亲“话语”终结,再到年迈的祖母被遗忘死去,三种死亡构筑了一个少年成长中的所见,看见的死亡其实也看见了童年的往事,看见了青春的懵懂,看见了断裂与融合,看见了梦幻和清醒。是的,有很多东西已经回不去了,有很多东西是不想回去了,在回不去和不想回去的现实里,唯有记忆才是不老的:“我总是回想起陪祖母走过的那条路,还有那些芭乐。”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51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