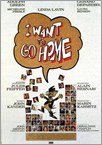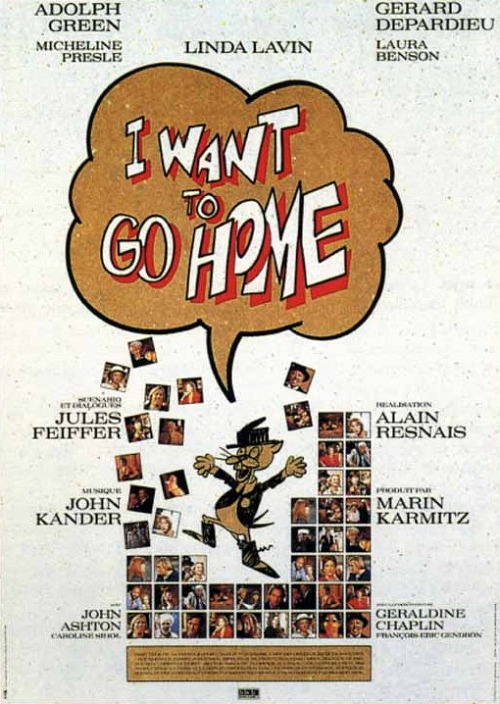2019-03-07《我要回家》:和来去的方向无关

“回家”指涉的是一个出发的起点,当“要回家”的强烈意愿指向这个出发点的时候,意味着离开可能是一场失败,当艾尔茜在无数次喊着“我要回家”变成现实的时候,她从美国到法国的求学之路或许真的是一次失败。但是,当那架返回美国的飞机开始起飞,当看到邻座的法国男子正在阅读漫画杂志,当父亲乔伊的女助手琳娜和她相拥,其实在一种融合的氛围里,在喜极而泣的结局中,“回家”已经失去了当成的意愿性,甚至失去了必然的方向,“我们都会回来”的背后其实是矛盾之后的和解,是寻找到的归宿。
而没有回家的乔伊呢?他也在一直讨厌的法国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归宿,和戈蒂埃的母亲伊琪一起骑着自行车,悠闲地骑行在乡村世界里,“如果我自吹自擂、草率,你就直接把我赶走。”乔伊这样说,在美好的世界里,在两个人的默契中,何来国籍的差别,何来观念的差异,何来文化的碰撞?当初他也和女儿一样喊着“我要回家”,但是当一种情感的归宿被找到,强烈的意愿变成了“我留下来”的现实——父女用不同的方式做出了选择,阐释了家的真正含义。
喊出“我要回家”,用目光回首走过的路,让心灵回到起点,这个逻辑的背后一定存在着这样一个事实:他们曾经先是离开了家,只有在离开家发生之后,才会遇到尴尬和矛盾时想要回家,所以一切的起点是:为什么他们要离开?艾尔茜离开美国是在两年前,当她坐在飞往巴黎的飞机上拿起那些用法语写成的书,她的渴望是如此强烈:“拉辛,我来了;莫里哀,我在向你靠拢;福楼拜,你是我的精神支柱……”这种渴望的背后就是义无反顾地离开:“我要逃离那种自大的生活,逃离克利夫兰山庄,逃离只会把愚蠢用在调笑餐桌上的文化。”
很明显,艾尔茜的自我独白注解了离开和向往的原因,那就是对于美国文化的鄙视,对于法国文化的热爱,在她看来,美国文化中充斥着自大、庸俗,甚至娱乐的东西,而法国文化则代表着高雅、哲思,这是一种对立,所以艾尔茜对于离开如此义无反顾,对于到来如此心驰神往,而她对于法国的未来生活集中在一个人身上,那就是作家戈蒂埃,拿着他的书,艾尔茜脸上充满崇拜的表情:“你是大师的后继者。”甚至把他说成是苏珊·桑塔格的“导师”——无不传递出一种对美国文化的讽刺。
这是两年前的到达,带着某种梦想的成分,而两年后,也是在飞往巴黎的飞机上,乔伊和琳娜却完全是以现实的方式抵达这个陌生城市,这是66岁的乔伊第一次坐飞机,名义上是参加在巴黎开幕的漫画展,自己的漫画形象赫普猫赢得了广泛赞誉,但其实乔伊的真正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和久未谋面的女儿艾尔茜相见,“这个臭丫头两年都没有写信。”两年没有写信,这是女儿和自己的生活断裂的象征,因为没有写信,乔伊只能编造谎言,代替艾尔茜每周给艾尔茜的母亲写信,他所有的疑问时:这两年艾尔茜在巴黎到底干了什么,为什么不和家里保持联系?
| 导演: 阿伦·雷乃 |
情感断裂,用寻找的方式重新连接起来,这是乔伊法国之行的目的,而其实,在被分隔成两地的思念中,在横跨两年的分离中,真正的矛盾并非是因为文化的差异,而是艾尔茜没有归宿感,在那个父女相见的夜晚,艾尔茜在街上喊了乔伊一句“爸爸”,但是在她住的房间里,对于乔伊的态度则是冷漠的,乔伊说起了艾尔茜母亲的事,说起了用信件编造的谎言,而艾尔茜只是很机械地告诉父亲自己学习的那些法语,几分钟之后,就急着要父亲离开房间,把他一个人丢在人生地不熟的街上。这种冷漠甚至连乔伊笔下的赫普猫都看不下去,它以拟人的方式出现,指责艾尔茜不尊重父亲。
乔伊笔下的赫普猫出声,是雷乃赋予它说话的权力,这个卡通形象也成为乔伊的替代者,但是艾尔茜对于赫普猫的态度一样是冷漠的,她总是让它“滚”,总是数落它,总是让它消失在自己的生活里——与对待乔伊的态度一样。为什么父女之间的隔阂那么深?乔伊是和艾尔茜的母亲分离了,又和助手琳娜关系不一般,也正是这种亲情的缺失,使得她远离故乡远离美国,在那次戈蒂埃乡下母亲伊琪家中的聚会上,艾尔茜就对伊琪袒露了心迹:“他不是我爸爸,他保护女人,除我之外。”所以,美国世界对艾尔茜来说,是没有家的归宿感的,她选择以离开的方式,甚至以销声匿迹的决绝态度逃离那个家,逃离父亲。
但是逃离而抵达,在两年的法国生活中,艾尔茜其实并没有找到自己的归宿,她崇拜的作家是戈蒂埃,但是自己写的关于福楼拜的论文,就从来没有送到戈蒂埃手中,而当她从父亲那里得到了伊琪的地址,知道周末有一场聚会的时候,她激动地抓住了这仅有的机会,骑着自行车来到了那里,他终于见到了心目中的偶像,终于可以将论文递交给他,但是在这一场聚会上,戈蒂埃根本没有时间看她的论文,这是一种被遗弃的感觉,就像她在巴黎的生活一样,混乱,孤独——也许在不如意的时候,和卡通赫普猫对话,尽管总是有冲突,但是像是和父亲说话一样,有一种存在的意义。
|
《我要回家》电影海报 |
当初在飞机上将两种文化对立起来,其实在某种意义上这根本不是本质的差异。无论是在漫画展上,还是在家庭聚会上,处处体现着文化差异,比如国际漫画展本来邀请了很多知名美国漫画家,但是除了乔伊之外没有任何人出席,这是不是美国文化中的自大?导演哈里来自美国,但是他受不了美国文化,他在漫画展上的结论是:“美国文化没救了。”法国文化就是高雅吗?艾尔茜崇拜的戈蒂埃,几乎没有看过她的论文,他喜欢乔伊的漫画似乎为乔伊找到了一个读者,但是在和乔伊聊天的时候,却又说自己太重要了,“我不可取代。”说自己是一个可悲而又忧郁的学者,不是一种自我贬低,而是故意拔高自己,似乎大众永远无法理解他。艾尔茜曾说美国文化是将智慧用在调笑餐桌上的文化,而在伊琪乡下的宴会上,这些所谓的学者,所谓的导演,所谓的艺术家,不也是在餐桌上调笑?甚至那场Cosplay上,几乎所有人都失去了道德约束,戈蒂埃先是和哈里的妻子躲在黑暗的屋子里偷吻,接着又在阳台上和琳娜勾搭,而一向看不起粗俗美国文化的哈里,却在发现妻子偷情之后,不由分说将伊琪房间里的贵重物品砸坏,一种暴力完全和文化无关,似乎成为人的本能之一种。
而从美国而来的乔伊,感受的也不是两国文化的冲突,而是没有真正感情支撑的空泛感。起初来到这个陌生的城市,对于乔伊来说,的确感受到了文化的差异,他不明白为什么5法郎的硬币比10法郎的要大,而且是银质的,而10法郎的只是铜制的,“为什么不是相反?”他不理解为什么100法郎的纸币分为好几种,“在美国只有一种。”他告诫琳娜不要吃没洗过的水果,他不懂为什么打电话要插入一张“信用卡”?更为悲催的是,受邀来参加漫画展,却没有人接机,在画展上也没有人接待,甚至听到了参观者说这些作品没什么深度,缺少洞察力,所以,在生活习惯不同、语言不通的陌生城市,乔伊用英语高喊着:“我讨厌这个鬼地方,我要回家。”对于乔伊来说,“我要回家”是他踏入法国这片土地之后最大的渴求。
但是,这种我要回家的渴求也是一种无归宿的写照,戈蒂埃似乎是他遇到的第一个知音,因为他知道乔伊的名字和漫画,他介绍给他的朋友,他还邀请他们去乡下母亲家,但是正是这个知音,却在阳台上和琳娜勾搭,而琳娜对艾尔茜说过一句话:“我试着爱你,但是现在我连你爸也不确定了。”在见识了这种混乱之后,躲在隔层里的乔伊遇到了一样无处可去的艾尔茜,这是父女特殊的见面,艾尔茜告诉他戈蒂埃在背后说他是个怪胎,并嘲讽他的漫画作品,在那一刻,乔伊似乎发现了虚伪的存在,而和女儿在一起,他也终于说出了自己对艾尔茜的爱:说起了女儿三岁的时候,把自己关起来,而乔伊为了让女儿开心,一遍一遍给她讲童话,讲起那只Sally猫;他看了艾尔茜的论文,对这篇文章赞赏有加,那一刻,疏离已久的父女终于找到了爱的表达方式,终于幸福地和解了,也终于用那一个吻化解了矛盾。
而父女似乎都在伊琪那里找到了自我,伊琪和艾尔茜聊天,艾尔茜对她说:“从来没有人这样和我说话。”在交谈中没有国籍差别也没有文化差异,就像母女一样随意地交谈着;而伊琪也喜欢乔伊,她对他说:“也许你是我命中注定的,你是我见过最悲伤的美国人。”而正是这种跨越文化的和解才会慢慢变成永恒的情感,在乔伊走出宴会和Cosplay现场的时候,他想要去飞机场“回家”,但是当地人听不懂他的英语,直到最后,他高声唱起了歌,而这首歌在二战时是盟军流行的歌曲,歌声消除了隔阂,歌声带来了对话,“我们是同盟”所传达的是一种融合,不管是历史还是现实,不管是宏大世界,还是微观生活,都在这回荡的歌声里汇聚成一种如家的感觉,而乔伊现场为他们作的漫画,又成为新的载体,将不同语言、不同风俗、不同文化的人结合在一起。
“我想回家”这一种强烈的愿望背后是情感的缺失,所以艾尔茜会选择两年不回信把自己当成一个孤儿,所以乔伊会离开妻子和家让女儿缺少了父爱,而在被发现的亲情、爱情里,家就在那里,它不需要转辗,不需要逃避,不需要想象,也无关高雅和低俗,也不再是一架飞机的离开和抵达,在理解的世界里,在融合的情感中,回去和留下都可能是家的方向。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37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