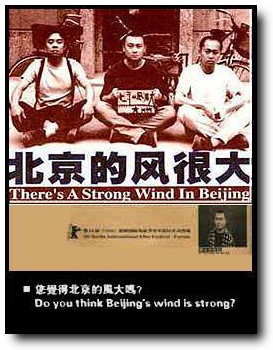2015-02-26 《北京的风很大》:反中心的苍白直觉

我的身后是江南淅淅沥沥的雨,安静、诗意,有些潮湿,作为背景之一种,它距离“北京的风”只有一个转身的距离,风在我面前,在我打开的电脑里,在雎安奇被纪录的镜头里,背面和身前,风和雨,构筑了一种只有一个身体的张力,而在被人为拉大的时间存在中,咫尺变成了遥远,就像1999年和2015年,是隔着两个世纪的镜像和现实。
13本100英尺规模的柯达,16毫米伊斯曼胶片,这包括全部拍摄素材的影片,最后剪辑成50分钟的纪录电影,而这50分钟的电影在1999年的世纪末也是过期了八年的胶片。物理影像的存在可以是无序的,可以是散乱的,可以是无中心的,但是那关于“风”的提问和回答却注定要激活这摇晃、扭曲和泛白的画面——随意的故事里总会有一个站在身后的人,那个身后的人是手拿摄影机的雎安奇,是“北京的风大吗?”的提问者,是一切出发点和回归点的那个中心。
|
| 导演: 雎安奇 |
 |
所以在一个无法“去中心”的词语之后,“北京的风大吗”的提问便成为一种叙事,一种从书面辞典变成现实对话的叙事方式。风是一阵风,风又不是一阵风,风是风俗,风是风景,风是风潮,风是风格,风是风湿,所以在被记录的“北京”街头,可以有雷,可以有雨,但是不一定有吹乱头发的风,而在整整50分钟的纪录电影里,真的没有一丝被影像记录的风,不管微风,还是狂风,都被轻易消解了其现实的意义。所以在无风的北京,关于“北京的风大吗”的提问和回答都变成为了一种行为艺术。
“你觉得北京的风大吗?”被提问者是“你”,而提问者当然是“我”,当你被置于摄像机前面,当你成为我的对象,一切的行为艺术也都是具有了中心意义。在这个匪夷所思、莫名其妙、毫无预兆的提问面前,每一个“你”都呈现出不同的态度和表情:“有风,但不舒服。”“我不喜欢北京的风,因为我不是北京人,我是重庆人。”“还没挂起来呢。”“不大,还可以。”“我不知道。”“干嘛啊你,有病啊?”……他们是街头行走的人,他们是捡破烂的流浪汉,他们是羞涩的外地民工,他们是一脸严肃的武警战士,他们是匆忙上班的普通职工,他们是学校的老师和孩子。如此等等,不同的你,面对同样的问题,有躲闪,有质疑,有猜疑,有拒绝,但是不管何种表情,何种态度,都被提问者纳入到一个预设的体系中,在这个体系中,那个从来没有出现在镜头里,从来不需要回答的“我”,才真正掌控着一切。
|
|
| 《北京的风很大》海报 |
随意而随机,在这个简单的问题面前,似乎有三个回答者在无形之中制造了属于自己的中心。一个是推着婴儿车的老人,起先是一个人慢腾腾地走,车上放置着两个纸箱子,后来的镜头里,这辆车里的纸箱子不见了,取而代之的两个可爱的小孩,他们望着镜头没有说话也不回答问题,再到后来,婴儿车上又变成了一罐煤气,而老人似乎也换了衣服,在镜头里也从正面变成了背影。这是一种取代式的消解,婴儿车里不同的人和物代表着不同的生活内容,所以这样的取代可以是自主的。而另外一个自设的中心,则是一对刚结婚的新人。镜头前起初是正在装饰的婚车,车前的新郎新娘玩偶和大红花、车门上扎着的红气球,然后镜头便转向了正在举办婚礼的酒店,一曲“我等的花儿也谢了”在现场不停地播放,而司仪那句“计划生育优生优育早得贵子”的祝福则把现场推向了高潮,而真正的中心形成则是回答问题的新郎一句话:“今天刮的是暖风,因为来的都是嘉宾。”暖风,是喜庆的风,是吉祥的风,是祝福的风,当然是对简单意义上的“北京的风大吗”的超越。而第三种去中心的方式则是“反问”,当问到“北京的风大吗”,回答的是“干吗啊,你有病吗?”而在筒子楼上,敲门,开门,当被问及“北京的风大吗”,里面的人的回答是:“你们找过居委会吗?录资料必须有居委会的通知。”而在街头练习网球的回答者,反问的一句话是:“你们不会是台湾间谍吧?现在社会这么复杂,什么样的人都有。”而对于间谍说的解释自然是这么近采访让人缺乏安全感,还详细阐述了弗洛姆关于人在社会上存在的五大基本需要,“1.5米之外我才有安全感。”
“你有病吗?”“你们找过居委会吗?”“你们不会是台湾间谍吧?”三个反问在某种程度上不仅取消了提问者的问题,而且形成了自己的叙事中心,和婴儿车的取代式消解、暖风式的超越,完成了一种反中心的架构。但是对于“北京的风大吗”的提问,这些解构还远远不够,在某种意义上,是为了彻底将自己的这个中心问题边缘化,或者说,提问者在提问的过程中需要的是对自身的解构。所以会寻找肮脏、发臭的简易厕所,那么赤裸裸将摄像机对准露着半个屁股的男人,问“北京的风大吗?”仿佛这个问题本身就是属于下半身的思考,属于最本真生理意义上的问题。而在“北京的风大吗”之外,提问者开始寻找另外的话题,比如遇到一对情侣,则问:“你们幸福吗?”遇到饭店里正在吃饭的,则问:“我可以和你们一道吃吗?”遇到警察,则是“警察叔叔,我捡到一分钱。”甚至到最后,见到街上每一个行人,都拿着一支烟,问他们:“请你抽根烟吧。”提问变成了邀请,那种由问答构成的关系发生了改变,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取消了中心地位。
但是对于北京街头的提问来说,真正需要消解的是北京作为政治中心和权力中心的意义,一个染着黄头发并不时髦的女人说出了北漂一族的想法,她来自哈尔滨,来到北京的原因,就是因为“北京的机会多”,北京代表着机会,代表着希望,虽然是奔波,是劳累,甚至是失望,但是无意义的意义支撑了他们的生活,所以,“北京的机会多”在某种程度上也变成了“北京的风很大”的中心隐喻。而在更具有政治意义的天安门,与一位外地人的对话将这种膜拜变成了讽喻。——“在天安门广场有什么想法?”——“因为北京是我国的首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心脏,可以显示祖国的强大,在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有安全感,就像在家里一样。来看看天安门广场是小时候的愿望,现在站在这里非常自豪,但也很紧张,我希望中国更加富强,生活更加美好……”
伴随着“我爱北京天安门”的歌声,镜头里其实只有字幕,不知道那个面对镜头讲出自豪感的人是谁,也不知道他说着流出眼泪的表情,天安门是象征,是国家符号,但是天安门被隐藏,像是对于中心意义的隐藏,所以在北京,在天安门,关于风的提问就是一个反中心的策略,只是当用反问、替换、超越以及隐藏等种种方式来消解中心意义时,无非是完成一种形式上的突破,甚至反中心而形成的中心也是虚设的,所以在各种不解、不耐、怀疑、拒绝、恐惧、谩骂的对话中,在隔阂、猜疑、冷漠、虚伪、拒绝的表情里,很多东西都变得苍白。但是那最后随机遇到的外地夫妻,似乎为这种反中心寻找到了一个突破点。
丈夫在街头电话机前给老家的亲戚打电话,而妻子则伤心地痛苦,面对这样的场景,“北京的风大吗”的提问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这对夫妻的讲述,他们8岁的孩子阳阳被诊断出白血病,还有肿瘤,6000千元刚用完,现在身无分文,只能把孩子拉回老家,“救不了孩子,只能回去等死。”这是父母的绝望,而在医院的病床上,高高的床栏里,躺着的孩子显得很平静,他还用手擦拭着伤心的母亲流下的眼泪,没有对话,只有镜头,镜头里是眼泪,是伤病,是无奈,是绝望。而在这个祖国的中心,这个国家的心脏,对于这个家庭来说,却意味着离开,意味着赴死式的离开。
街上依旧是川流不息的车流,依旧是行色匆匆的行人,依旧有各种陌生的人群,也或者有“北京的风大吗”的提问,有抵达北京和离开北京的个体,一切依旧,镜头里或许偶然有着人性的关怀,但是一切还是没有改变,当那两个正在玩耍的孩子,跑着要放飞手中的风筝,却怎么也飞不起来,他们无奈地看着风筝。
这是一个没有风的北京,这是最后走向“再见”的记录影像,当镜头关闭,当现实关闭,当中心关闭,“风”或许最后还只是停留在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的《现代汉语词典》第321页,停留在雎安奇1999年50分钟的胶片里,停留在2015年以江南的雨作为背景看见的电脑上,风未来,风已逝,“对于我而言,我能做的就是在有限的条件下捍卫自己的直觉。”直觉没有隐喻,直觉不是中心,直觉只是一种苍白的存在。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4675]
思前: 红色粉末状
顾后: 《好死不如赖活着》:眼睁睁地看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