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11-21 《别烦我》:层层的眼睑下只为自己而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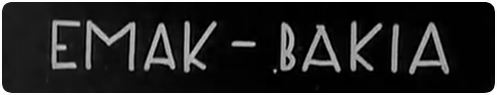
是谁喊出了“Emak-Bakia”?又有谁能听见在梦中的呓语?这是2017年深秋的某个午后,阳光并不能祈求照耀在梦境里,当一场阴雨制造了湿冷的效果,午后的安睡似乎也成为一种想象。打扰而破坏,一切的时间里都没有纯粹在一种梦境里的流动,它戛然而止,断裂在睁开眼睛的那一刻。
根本没有睡去,是假装自己躺在那里,隔绝了窗外的一切,隔绝了绵绵的雨丝,为什么一个梦还会有猝然而至的情节?其实只是合上的眼睑,而眼睑外面却贴着一张睁开眼睛的图案。是图案本身醒着,还是眼睛就在那里睁着?一层纸,其实制造了诸多可能,一种醒是为了掩盖一种睡,一种睡却在必然的醒中,所以错乱的午后,一定会喊出那个拒绝别人的“Emak-Bakia”,是“别烦我”,无论是2017年,还是1926年,在时间的改变中,有一种已睡未睡的状态却永远不变。
谁喊出了那句话?一个女人。她起先躺在那里,世界流动成某种光影,一切都被放置在了水里,如梦如幻,在扭曲变形的世界里,它们的流动恰好把她带入到一个梦中世界。那里有盛开的花,有钉子的影子,有跳跃的符号,有网状的结构,有明灭的灯光——都是不确定,却一定会成为睡梦中的意象。横的波纹变成竖的,直线旋转成圆形,而在音乐中,一切都在翩翩起舞,旋转,跳跃,都把影子变成了形体,在多棱镜的折射中变化出无穷的图案。
|
| 导演: 曼·雷 |
 |
梦境,光影,水,都是柔软的,都和女人有关。所以在归属女人的世界里,她们的跑车,她们的高跟鞋,她们的墨镜,她们的舞蹈,以及她们柔软的水,都变成沉浸在其中的梦里,梦是纯粹的,梦是独立的,梦是一切梦的原初。可是,为什么梦会倒置,梦会变形,梦会破碎,梦会成为眼睑制造的虚幻世界?因为有男人。男人在数字后面,男人在影子里,男人在她们背后,而男人代表的世界是强硬,是权威,是秩序。
|
|
| 《别烦我》片头 |
那辆车里下来的男人,进入到酒店,他打开袋子,他撕下领子,领子在跳舞,领子在消失,一种身份的证明,不是为了毁坏,不是为了消灭,而是用领子的舞蹈取代女人的舞蹈。那个在镜子前的男人,梳着头化着妆,他在镜像里不是看见自己作为男人的存在,他完全打扮成了女人,妖媚的动作,浓重的色彩,异化的表情,他不是为了取悦女人,而是为了取代女人,所以镜子前的男人作为一种象征,已经把女人变成了虚幻的影像,当男人走到窗边,他看见的是大海,大海上是浪花,大海外是沙滩,在目光所及的世界里,柔软不见了,梦境不见了。
男人是在女人的背后,他们用一种力量占有了梦境,他们用一种权威破坏了生活,甚至还有窥视,那变化的影像里,一只眼睛在背后注视,躲在暗处是阴谋,是欲望,是要把女人的一切秘密都掌控在自己的目光中。所以在女人之外的男人,呈现出一种力量的介入,一种镜像的异化,一种窥视的欲望,而所有种种,都让女人的那个柔软的世界肢解:摇晃而不稳定,扭而而不真实,沉默而不说话。男人是男人,男人是上帝,男人是体系,男人是权威,男人是纯粹的矛盾。
所以,对于这个存在着男人和女人的世界来说,眼睑成为一种拒绝,拒绝规定,拒绝体系,拒绝占有,也拒绝逻辑,而这正是1926年达达主义的主张,“哦,纯粹的矛盾,想望在你层层的眼睑下,只为自己而眠。”里尔克写到的眼睑,是为了在遮蔽中“为自己而眠”,也就是寻找一种独立性,一种自我性,就像女人,在睁开而为他人所见的眼睑之外,“作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睡梦”,而睡于自己的梦,就需要大胆地说出“Emak-Bakia”——“别烦我”,就是让我成为我,“别烦我”,就是不要让世界失去独立,“别烦我”,就是纯粹于艺术和美的生活。
于是,那些和逻辑有关的数字被倒置在那里,扭曲而流动取消了数字的意义,而成为图像本身;于是,在路上都是迷途的羊群,没有目的地,就是它们最自由的追求,和那一只猫一样,寻找自己的方向;于是被束缚在钉子世界的木头柱子变成了圆形,变成了积木,变成了一座可以自由组合的城堡;于是,花在开放,水在流动,人在运动,世界以不被规定的方式在运行——而在自我世界里,睁着的眼睑下,女人活在华丽的画案之外,在睡梦中,她看见了鱼,看见了玻璃,看见了舞蹈,看见了光影,看见了自己,“层层的眼睑下只为自己而眠”。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2519]
思前: 未知的闯入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