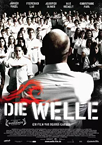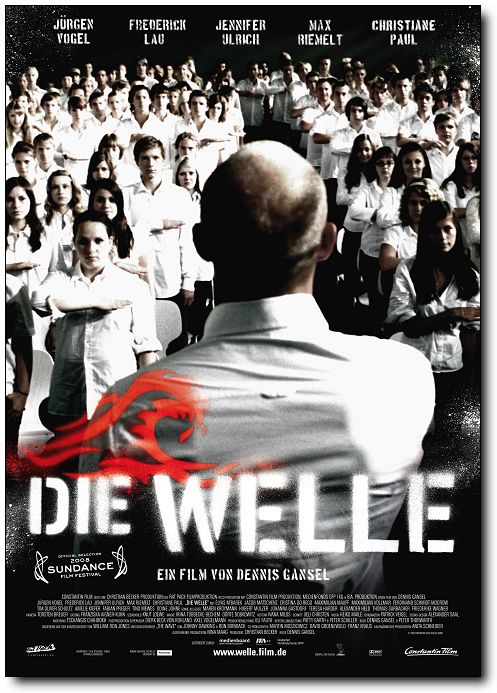2018-06-05 《浪潮》:六天,一个独裁的寓言

“什么是独裁?”“专制政府有什么共同点?”“专制制度建立的条件?”仅仅是课堂上对于理论的探讨?仅仅是活动课上获取学分的知识点?当理论和知识变成“纪律铸就力量”,变成“团结铸就力量”,变成“行动铸就力量”,在没有有效阻止的情况下,最后就变成了一场闹剧,一次自杀,一种死亡,以及一个悲伤却沉重的背影。
从理论变成实践,从行动变成悲剧,只有短短六天时间,当这个“独裁政府”的实验无法逃避现实的时候,六天便成为建立社会学样本的时间,便成为书写独裁制度的寓言。当第六天蒂姆终于高喊着“浪潮没有结束”的时候,他终于将那把枪对准了同学,“你们都不许回家!”同学在枪声中倒下,“这是我生命的全部!”那把枪朝向了自己,在沉闷的枪声中,血溅在他的白衬衫上,溅在阶梯教室的讲台上。
从开始的星期一到最后的星期六,悲剧为什么会在短短六天里发生?就像站在讲台上的老师赖纳·文格尔宣告“浪潮”结束前问同学的那个问题:“你们到底经历了什么?”学校活动周一堂“独裁政治”的课,本来或许就是老师在讲台上讲述独裁政治的起源、特点和必须反思的问题,或许就是同学认真不认真地记着笔记,然后拿到或拿不到学分而已,但是当“骰子已经掷出”,在被动教学的赖纳看来,则变成了一堂实验课。星期一,他在讲台上首先问学生什么是独裁,专制政府有什么共同点,专制制度建立的条件,当有人在下面漫不经心无所事事,当有人不想谈独裁政治,“这种事反正不会再发生了。”瑞纳反问:“你们认为独裁专制在德国不可能重演,对不对?”当看到学生点头,一个关于独裁政府的计划便在他头脑中形成。
第一节课上半场只是理论,而当课间休息之后,真正的实验开始了,“我要用自己的方式安排活动周。”瑞纳对同学们说,“一个独裁政府最核心的是什么,那就是领导。”在放弃用“元首”这个称呼之后,同学推举他为领导,于是他成为了“文格尔先生”——在课后他是“瑞纳”老师,在课堂上他是“文格尔先生”,文格尔先生就是领导,就是独裁政府的核心,于是,文格尔先生说:“把你们桌上的东西都拿掉。”于是,文格尔先生说:“你们发言时必须起立。”因为这样可以使呼吸更顺畅,当有人发言时没有起立,瑞纳提醒他们,当有人反对,瑞纳则让他们离开教室。
这是星期一,是“纪律铸就力量”的开端,而星期二,则是“团结铸就力量”,在上课起立之后,瑞纳让大家做放松运动,在“左右左”的口令下,大家开始统一步调,他要让大家体会“逐渐融为一体”的感觉,让大家感受到集体的力量,因为集体可以排除差异,可以消除个体,而当时和他换了活动周课程的维兰德,正在楼下的教室里上“无政府主义”的课,瑞纳对同学们说:“让我们的敌人吃天花板的灰去吧!”在步调一致的开场之后,瑞纳提出要统一服装,从明天开始大家都要穿白色衬衫来上课。而到了星期三,瑞纳便开始了“行动就是力量”的实践,他通过征求同学们的建议,将这个集体命名为“浪潮”,就是要像巨浪一样用统一行动制造强大的力量;有同学提议设计统一标志,还要设计浪潮的明信片和帽子,还要制作浪潮的网页。而在星期四,同学们建议浪潮团体要有问候的手势,右手在胸前如波浪一样划过,瑞纳采纳了大家的建议。
|
| 导演: 丹尼斯·甘塞尔 |
 |
这是一代人的困惑,而对于其中的个体来说,在英雄主义之外则是现实的无奈,曾经被叫做“软脚虾”的蒂姆总是被人欺负,连大麻他也只能免费提供给别人,他一直生活在边缘,没有真正的存在感,而当加入到“浪潮”之后,他感受到了平等,他把自己的耐克球鞋全部烧掉,换成了白色衬衫,当有人欺负他时,浪潮的成员则出面帮助他,他感觉到了集体带给他的存在感,他不再孤独,他浑身充满了力量;马尔科喜欢独来独行,这也是源于家庭缺少温暖,和卡罗成为男女朋友却又总是受制于她,但是在由他命名的“浪潮”里,他结识了新的朋友,自我价值被提升,也更多融入到集体中,于是在那场水球比赛中,和队友配合进攻得手。平时吊儿郎当的卡尔在浪潮中充满了动力,他为浪潮建立了专门的网页,凯文最初因为领导不推举他退出了“独裁政治”课,但是在感觉到浪潮的力量之后,又加入其中,甚至连楼下“无政府主义”课上的学生也主动转到瑞纳的课上,正像瑞纳对妻子安克说的:“我这么做是有教育意义的,他们变了。”甚至学校校长也认为这是一种积极的力量。
|
|
| 《浪潮》电影海报 |
但是,在纪律、团结和行动中铸就的力量,却以另外的方式表现出来,那就是狂热。当莫娜对“发言必须起立”提出异议,最后的结局是只能离开;当卡罗因为不好看而没穿白色衬衫,她变成了异类;没有做出波浪式问候手势的同学无法进入水球馆看球;不是浪潮成员无法玩轮滑;甚至,他们对不融入集体的人施加压力,让他们失去朋友。他们设计的浪潮主页上是一把枪,他们印制的5000份浪潮标志贴在了城市的大街小巷和格式橱窗、建筑物,蒂姆甚至爬上了在建的市政府建筑,将大红的浪潮标志喷涂在上面,不仅引来了警察,而且还作为社会新闻上了报纸头条。
“浪潮将席卷整个城市。”这是他们的目标,于是这本来囿于课堂的一次教学实验变成了一种社会行为,浪潮标志遍布城市,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当浪潮标志覆盖了那些小混混的图标,引发了彼此之间的对立和争斗,而在紧张关系中,蒂姆甚至拿出了枪威胁,在对手“投降”之后他更加感觉到自己的不同凡响。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他慢慢走上了歧途,他的狂热,他的偏执,让他无法自拔,甚至就是把“浪潮”这个团体当成了自己一生的追求,当成了生命的全部,他找到瑞纳,想要为“文格尔先生”当私人保镖,要日夜保护这个领导,甚至当被瑞纳劝回家之后,他还是在门外等了一个晚上。
把教学当成现实,当实验当成真理,这便是蒂姆走向悲剧的一个极端,当瑞纳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在星期六他召集同学上了最后一堂课,而在这堂课上他依然以自己的实验模式开展教学,他高举双手,他激情演讲:““德国近年来每况愈下,我们是全球化的输家,但政府却告诉我们,努力干活才是摆脱危机的唯一办法。那些政治家根本就是经济动物的傀儡。失业率必须下降,我们还是出口大国,但实际上,穷者愈穷,富者愈富。恐怖活动是现今最大的威胁,而恐怖活动正是我们自己,通过散布不公正而一手造成的,当我们把自己的星球一步步推向毁灭的时候,那些富人却在一旁摩拳擦掌,建造空间站,还想从高处来欣赏这一切。”他高喊着:“浪潮是改变的唯一机会,我们将创造历史,我们将席卷整个德国……”当马尔科站起来反对他的浪潮,认为这是一次“法西斯主义的重演”,瑞纳让同学将马尔科带上了讲台,说他是“叛徒”,正当他问同学们如何处置他的时候,他忽然转变了口气说:“你们刚才到底经历了什么?这就是独裁,这就是法西斯主义,我不知道继续下去还会发生什么,我向你们道歉,我做的过火了,一切结束了。”
原来这也是他精心安排的“实验”,是达到高潮的一次课堂教学,但是当经历了从星期一到星期六的洗脑和改造,当经历了一周的纪律、团结和行动的实践,其实“结束”已经不再是他可以设定的终点,站出来的是蒂姆,他沮丧地说:“这没有结束。”继而开始疯狂地叫到:“谁也不许回家。”当一个人的全部生命都融入其中,当一个人狂热地无法自拔,他必然走向极端,开枪,打倒了一个同学,然后对准瑞纳,当他意识到不能伤害“领导”文格尔先生的时候,便以突然爆发的方式吞枪自杀。一颗子弹,一声枪响,一种死亡,在教学之外,在实验之外,在课堂之外。
蒂姆是一个极端的个例,在他狂热地参与,甚至最后以生命献祭的时候,这场精心策划的教学实验与其说是失败,不如说是成功的,因为它让人看到了疯狂和偏执,让人看到了非理性的存在,让人看到了个体和差异被消灭之后的强权,而其实,蒂姆只是个案,甚至是电影艺术中追求效果的一种人为化的设定,在六天的独裁制度实践中,其实蒂姆的死是被放大的。“由真实事件改变”写在电影开始前,真实事件是指1967年发生在加州高中的教学故事,一个青年教员为了让学生明白什么是法西斯,他就提出了“纪律铸造力量”、“团结铸造力量”和“行动铸造力量”的一次教学实验,他用严苛的规条束缚学生,向他们灌输集体主义,要求他们绝对服从,遵守纪律,而令人惊讶的是,学生们非常顺从,步调一致地投入其中。他们精神抖擞,穿上制服,做课间操,互相监督,很快凝聚成一个新的团体——当最后老师告诉学生这只是一个实验的时候,大家才认识到独裁的可怕。
真实事件的最后结果是醒悟,而其实,在“浪潮”里,瑞纳开展的教学实验也并非能将人推向悲剧,从整个过程来看,瑞纳一直把握着节奏,他虽然是“文格尔先生”,是领导,他引导学生走向集体,在统一的制服、统一的手势、统一的标志中建立了“浪潮”,但是仅限于课堂上,他没有参与学生的涂鸦行动,没有参加学生的聚会,也没有进行“操控”,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说,在六天时间里,“独裁政府”根本没有建立,可以说,他的教学计划是失败的。而学生们的疯狂行动也都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当蒂姆告诉他知道市政府大楼的标志是谁弄上去的,瑞纳告诉他:“我们需要的是团结,而不是出卖。”当他终于发现“浪潮”从课堂走向了社会,并可能引起麻烦制造混乱时,他及时召开会议进行了制止,只不过,因为太追求教学效果,而在客观上忽略了集体主义的狂热,忽略了蒂姆这种极端隔离的存在。
而其实回过头来审视,蒂姆式的个体悲剧之上演,也有着不可忽视的原因,瑞纳为什么忽视了蒂姆的存在?为什么没有在他身上过早看到悲剧的影子?其实就是源于他的自我认同,瑞纳是一个自学成才的教育工作者,妻子是硕士文凭,这其中就存在着隐形的差异,所以在家庭里,在学校里,瑞纳都是压抑的,当妻子安克警告他这可能是一场闹剧,瑞纳却还在坚持,并且说妻子是嫉妒他,一直以来就看不起他,所以当他有了教学上的成就,就贬低他;而在同事面前,他更加没有地位,本来“无政府主义”是他在活动周上要上的课,不想被维兰德强制调换了,他没有办法,只能上“独裁政府”的课3,,从这个意义上,维兰德代表的也是一种强权,所以他要用整齐的步调让楼下听“无政府主义”课的同学吃灰尘,所以他希望通过“浪潮”来证明自己。也正是这一点,他沉浸在自己的成功中,而忽视了莫娜的意见,卡罗的反对,蒂姆的狂热,最终使得这一个实验走向了闹剧,走向了悲剧。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6051]
思前: 《伴我同行》:像少年一样行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