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06-05《十诫·第八诫》:只有正义能扶正墙画

《十诫》之第八诫,打出的字幕是“心灵之罪”,1943年的战争已经过去了四十多年,6岁的犹太人伊丽莎白没有成为纳粹屠杀的牺牲品,“最重要的是胎儿还活着”的历史和现实面前,谁承受了心灵之罪?心灵之罪又指向具体的那种罪?
这一疑问当然出现在大学教授索菲亚开设的讲座上,这个名为“道德炼狱”的课题讨论上,学生和教授,台上和台下形成的议题是关于道德的:关于孩子的生命和丈夫之间的取舍。但是在这堂课上坐着的是一个特殊的学生,她就是来自美国的伊丽莎白,拿着录音机的她从后面的位置换到了前面,为的是更清楚听到并录下索菲亚的观点,但是当伊丽莎白不停地用手扯着胸前的十字架项链,关于历史,关于往事,关于道德之外的考验就成为了这堂课的“闯入者”——伊丽莎白讲述了自己面对的一道心灵难题:1943年2月,一个名叫海琳娜的6岁女孩在监护人和神父的带领下,来到了莫克多区的一户人间,为的是给这个犹太女孩提供施洗的证明,但是当他们来到这里,本来同意做他们“教父”的夫妇却迟疑了,尤其是丈夫不停绕着房间,手插在口袋里显得很紧张,妻子有些镇定但也没有最终提供,还有另一个老人坐在轮椅上背对着他们,最终在“宵禁马上开始”之前,监护人和神父拉着海琳娜离开了他们。
这个夜晚发生的一切在40年后成为课堂上的一个教案,伊丽莎白举出这个例子是要寻找一个答案:当初那对夫妇为什么选择了退却?由此带来的危险是:海琳娜差点命丧纳粹之手,之后在一户人家的庇护下躲藏了两年多,最终逃离了波兰去往了美国。当然,海琳娜的最终命运还是回到了索菲亚所说的“最重要的是胎儿还活着”,活着便是对生命的尊重,便是度过了危险,便是最好的结局。但是这个最好的结局背后却是伊丽莎白所提出来的一种罪:如果没有那户庇护海琳娜的人家,如果没有最终离开波兰,是不是最后的命运也是死亡。所以活着是一件偶然的是,这个偶然的背后则指向了那对夫妇,在需要帮助的时候他们没有伸出手,这是不是一种陷在“道德炼狱”里的困境?
眼看着6岁的犹太女孩被推向不可知的命运,那对夫妇的选择在最表层上的确是一个道德问题,就像一位男同学认为的,当时那对夫妇一定感受到了战争的恐惧,所以他们选择了退出;但是课堂上伊丽莎白自己却认为,这似乎涉及的是一个信仰问题,因为女孩是犹太人,信奉的是犹太教,而那对夫妇是天主教教徒,让天主教夫妇为犹太人提供受洗证明,无疑只是一种“虚假仪式”,“他们无法对上帝撒谎,进行虚假仪式有违道德原则。”所以夫妇的动机是对信仰的尊重;但是课堂上的一位女同学否定了这个看法,“那对夫妇如果行虚假仪式,并不违反自己的信仰。”也就是说,受洗不受洗,何种方式受洗,看起来是一个宗教问题,实际上它也只是仪式,最重要的是解救生命,而上帝之存在,无论是犹太教还是天主教,救人就是一种至上的信仰,就是一种善。
| 导演: 克日什托夫·基耶斯洛夫斯基 |
课堂上没有最终形成共识,似乎索菲亚也并不希望有唯一一个答案。但是在结束课堂讨论之后,这个和历史有关的故事其实变成了现实,因为伊丽莎白就是当年6岁的海琳娜,而索菲亚就是那对夫妇中的妻子。在他们再次遇见的时候,索菲亚也认出了伊丽莎白,而伊丽莎白来此的目的就是为了找到心中疑问的答案。正因为伊丽莎白是当事人,甚至是某种意义上的受害者,所以她从历史回到现实,其实有了某种预设:那对夫妇当时没有解救自己是不是背负了一种罪,所以她告诉索菲亚这几年她很想给索菲亚写信以寻求答案,而在索菲亚将她带到当年的那间房子前面时,下车的伊丽莎白走进去之后却躲了起来,索菲亚进去寻找,却发现她不见了,甚至索菲亚走上楼梯,挨家敲响了门,但是最后还是找不到伊丽莎白,在寻找无果的情况下,索菲亚陷入了某种恐慌,而这种恐慌就是伊丽莎白故意带给她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她也体会一下找不到希望的“害怕”。
所以已经预设了一切的伊丽莎白,在心中已经有了谁有罪的答案,“为什么有人会当救世主,而有人却成为了被救者?”救世主和被救者截然分开,就是伊丽莎白对于有罪者的归结态度,自己没有成为他们的被救者,索菲亚和丈夫当然也不是救世主。但是这个故事并不只是一个道德问题和宗教难题,索菲亚将伊丽莎白带到了自己家里,说起了当初做出这一决定的背后故事:丈夫是一名波兰陆军军官,那名带伊丽莎白来找到他们的人就是一名盖世太保的眼线,“经由你,经由你的监护人和神父,盖世太保将找到我们,将会查获地下组织,所以为了组织的安全,我们才背弃了你……”虽然索菲亚说出了真正的动机,但是在内心里她一直以来还是被负罪感折磨着,认为是自己将伊丽莎白送上了死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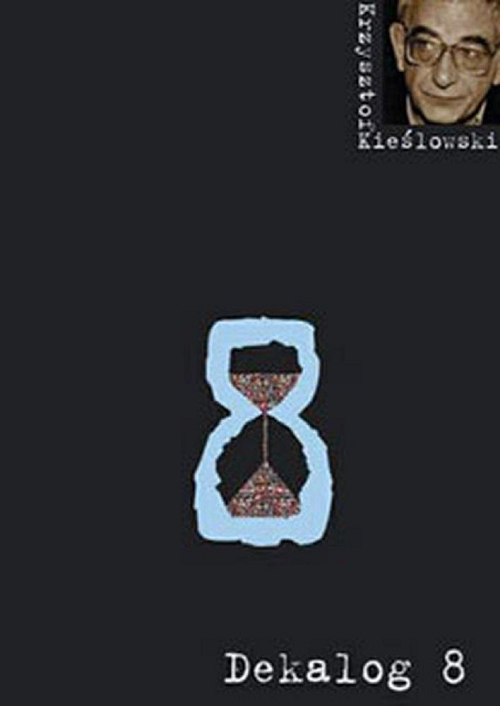
《第八诫》电影海报
索菲亚的负罪感依然是道德层面的事,但是通过背弃一个仪式而保护了地下组织,在她看来就变成了一种正义,而正义超越了道德和宗教,索菲亚告诉伊丽莎白,自己在课堂上对学生讲述的就是正义至上:“我没教学生什么,我只是帮助他们得到他们自己的结论。正义是最重要的,我相信它是真的存在,存在于人的内心之中。”她认为人是自由的,可以自由选择,“若他喜欢的话,可以背弃上帝。”伊丽莎白问她:“那么什么可以取代上帝?”索菲亚说:“遗世独立,然后,设法追到问题的核心,若最后什么都没,那就只有虚空。”信仰之缺失,是对上帝的背弃,是最后的虚空,但是却握着正义。当伊丽莎白听到了这个回答,内心的那个疑问才慢慢化解,但是她最后提出要求去渐渐那个保护自己的人,索菲亚便带她去见了那名裁缝,伊丽莎白说起了那段往事,“你们本来想救我的命,我是来道谢的。”但那人却只说自己当时22岁,并没有接受道谢,也不想回忆,最后索菲亚对伊丽莎白说的是:“他正遭遇大难题,或许这个难题太大了。”
裁缝救过伊丽莎白,他没有背负道德之罪,但是他却是盖世太保的眼线,他带着伊丽莎白去找索菲亚夫妇只是为了得到更多情报,所以他“救了”伊丽莎白的同时却可能害死更多的人;索菲亚没有给伊丽莎白提供虚假仪式,他们背弃了她将她置于危险之中,却解救了更多的人,无论是谁,做出决定其实都和道德无关,和信仰无关,只和正义有关,所以这个关于心灵之罪的故事涉及的是道德、宗教和正义问题,而“正义最重要”才成为最后的答案——当基耶斯洛夫斯基用这个故事来思考道德、宗教和正义三重问题,在一个细节上得到了诠释,那就是如何让墙上那张画摆正:索菲亚锻炼回来看到墙上的画歪掉了,于是将其摆正,但是一转身画又歪掉了;伊丽莎白来到索菲亚的家里,看到墙上的画歪了,她也伸出手将其摆正,但是后来还是歪了;只有最后,当两个人尽释前嫌看见里被历史尘埃覆盖的正义重新发出光芒,扶正的画终于没有再歪下来——正义超越道德和宗教,也只有正义才能扶“正”歪掉的墙画、被误解的历史和内心的疑问。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28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