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2-27《集外集》:躲进小楼成一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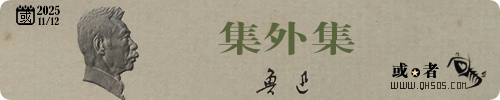
我虽然竭力想摸索人们的魂灵,但时时总自憾有些隔膜。在将来,围在高墙里面的一切人众,该会自己觉醒,走出,都来开口的罢,而现在还少见,所以我也只得依了自己的觉察,孤寂地姑且将这些写出,作为在我的眼里所经过的中国的人生。
——《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
一堵高墙是立在那里的,一边是被围在里面的“一切人众”,而且人人之间“各有一道高墙”,将每个人都分离,于是大家的心无从相印,还是有一天他们自己能够觉醒,能够走出,能够开口,但至少“现在还少见”;另一方面,则是高墙之外的自己,隔着墙是有隔膜的,但还是试做着,想要“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观察也罢,写出来也好,至少是用自己的眼睛看见“中国的人生”,至少也是在铁屋里“呐喊”了,虽然“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但是,“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
在俄文译本《阿Q正传》的序言里,鲁迅谈及了高墙之内外的两种状态,而这两种状态正显示了两种人生。于那些“各个分离”的人来说,他们活着便是国民性的体现,不仅没有感到肉体上的痛苦,又在“圣人和圣人之徒”补了造化之缺外,也不再感到精神上的痛苦——所以隔阂,所以枯萎,所以死去,“然而,许多人却不能借此说话了,加以古训所筑成的高墙,更使他们连想也不敢想。”这高墙已经筑起了四千年,“现在我们所能听到的不过是几个圣人之徒的意见和道理,为了他们自己;至于百姓,却就默默的生长,萎黄,枯死了,像压在大石底下的草一样,已经有四千年!”可怕的方块字被造了出来,像是那筑起高墙的砖石,阻隔了向外的目光,也压制了想要走出来的身体,而高墙外面的世界到底怎样呢?
在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上海暨南大学演讲的《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中,鲁迅讲到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讲到了十九世纪以后文艺的“不同”,其中就说到了中国高墙之外的“革命”,“十九世纪,可以说是一个革命的时代;所谓革命,那不安于现在,不满意于现状的都是。”十八世纪的英国小说,就是为太太小姐们消遣的,但是当十九世纪开始了革命,文艺就承担起革命的任务,只有旧的消灭,新的才能产生。这是一种进化的观点,但是文学家绝没有因为自己参加了革命而使命运发生了改变,他们一样还是“处处碰钉子”,这便又回到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上来:一方面,政治家认为文学家是社会扰乱的煽动者,“心想杀掉他,社会可就平安了”,但是在革命的时候,文艺家的话,政治革命家也是赞同的,但是不管是政治家杀了文学家,还是政治家和文学家一起进行了革命,文艺和政治的冲突似乎就没有终结,在鲁迅看来,这是一种必然的规律,“政治想维系现状使它统一,文艺催促社会进化使它渐渐分离;文艺虽使社会分裂,但是社会这样才进步起来。”
但是文艺家却总是逃不出一种宿命,那就是在革命的时候,他们都在做一个梦,以为革命的成功将会有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但是他们发现革命之后现实还是那么一回事,“照他们这样叫,啼,哭都不成功;向前不成功,向后也不成功,理想和现实不一致,这是注定的运命”——这一种文艺家的革命观和命运观在鲁迅看来是对革命文学本身的误解,“所以以革命文学自命的,一定不是革命文学,世间那有满意现状的革命文学?”甚至于那些文艺家是在用自己的皮肉在挨打,“文学家自己来做戏给人家看,或是绑出去砍头,或是在最近墙脚下枪毙,都可以热闹一下子。”想要被被人看戏的文艺家当然不是可以革命的文艺家,这和以革命文学之命的文艺家一样,只不过是口头革命,甚而至于还是在高墙里的那些处在隔阂中、既没有感到肉体痛苦也没有感到精神痛苦的众人一样,没有觉醒,没有走出,没有开口。
比如那些拿着屠城的笔扫荡文坛上的野草的人:一九二三年周灵均在《文学周刊》上发表《删诗》一文,把胡适《尝试集》、郭沫若《女神》、康白情《草儿》、俞平伯《冬夜》、徐玉诺《将来的花园》、朱自清、叶绍钧《雪朝》、汪静之《蕙的风》、陆志韦《渡河》八部新诗,都用“不佳”、“不是诗”、“未成熟的作品”等语加以否定,之后他在同年十二月十五日《晨报副刊》发表《寄语母亲》一诗,其中多是“写不出”一类语句:“我想写几句话,寄给我的母亲,刚拿起笔儿却又放下了,写不出爱,写不出母亲的爱呵。”扫荡了野草是快意的,但扫荡之后自己动手来创作只能喊出“我说不出”的无聊;比如以“神秘主义”作音乐的诗人: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一日的《语丝》发表了徐志摩翻译的波德莱尔《恶之花》中的《死尸》一诗,徐志摩在长篇议论中说:“诗的真妙处不在他的字义里,却在他的不可捉摸的音节里;他刺戟着也不是你的皮肤(那本来就太粗太厚!)却是你自己一样不可捉摸的魂灵”;比如“另找一个名字”写点文章去恭维的现象,北大学生欧阳兰写作了独幕剧《父亲的归来》,几乎就是抄袭了日本菊池宽的《父归》,被人指出后一个署名叫“琴心”的作者开始了辩护,后来又有人指出欧阳兰抄袭了郭沫若翻译的雪莱诗歌,“琴心”和另一个署名“雪纹女士”的人又开始为她辩护,而实际上这些人都是同一个人……
不仅不是革命的文艺家,甚至是可耻的文艺家,不仅不是麻木的文艺家,甚至是压制创作的文艺家——甚而至于连文艺家也不是,是“慈悲而残忍的金苍蝇”,是用了疯子做武器而且还是假的疯子的“杨树达”君,那些文人的丑态在鲁迅那里便成为了“烽话五则”:是冲突的父子“用神通”将他们的年纪变成略约相同而成为志同道合好友的荒诞,是受了儿子或姨太太的气才感叹“人心不古”的可笑,是“电报曰:天祸中国。天曰:委实冤枉!”的戏谑,是把灵魂之自在游行看成一钱不值而“率家眷移入东交民巷使馆界”自称是“精神文明人”的不齿,是睡在烽火边把烘烘地响的听觉看成是烽火的诗人,无为无不为、无味即至味的空谈……
“烽话”即“疯话”,不是革命者成了疯子,甚至是假疯子,这便是高墙之内的另一种魂灵,而高墙之外真正的革命文艺家是有的,那便是要放眼世界,而文艺家之革命,首先在于革命具有必然性,一九〇三年的《斯巴达之魂》和《说鈤》是鲁迅以世界眼光看见文艺之外的革命:“西历纪元前四百八十年,波斯王泽耳士大举侵希腊。斯巴达王黎河尼佗将市民三百,同盟军数千,扼温泉门。”只有三百斯巴达士兵,如何抵挡波斯十万之众?他们是大无畏的三百军,“结怒欲冲冠之长发,以示一瞑不视之决志。”不仅如此,还有挺身而出的女性隋烈娜,于是那场德摩比勒之役便成为展现“斯巴达之魂”的经典战役,在历史上成为矗立着的纪念碑;而新原质曰鈤(即镭)的发现,更是一种变革社会的必然成果,“由是而关于物质之观念,倏一震动,生大变象。”
战争状态的大无畏,科技时代的新发现,都体现着一种革命精神,而在文艺界,高墙外的革命烈焰也是在熊熊燃烧,作为《奔流》的编辑,鲁迅每次都要在编校之后也上后记,那十二则后记便是对域外革命文学发展的肯定,便是对照中国文艺的空白——一方面外国的书很少译介到中国,“单就文艺而言,我们实在还知道得太少,吸收得太少。”托尔斯泰这样的俄国巨人,在中国几乎为零,易卜生后来有了专号,但也是引起非议,所以,“从这记录中,可以看见在劳动阶级文学大本营的俄国的文学的理论和实际,于现在的中国,恐怕是不为无益的。”另一方面,中国的书译介到国外也是一个空白,“单是,忽然想起,在中国的外人,译经书,子书的是有的,但很少有认真地将现在的文化生活——无论高低,总还是文化生活——绍介给世界。”把《红楼梦》的宝玉变成了“少年威德”,《水浒传》里具有革命精神的反抗者都成了“涂面剪径的假李逵”,这只不过是“拉旧来帮新”的做法——而无论是引进外国著作,还是译介中国作品,重要的是和“现在的文化生活”结合在一起,而这便是鲁迅所强调的社会性,在为韦丛芜所译《穷人》而作的“小引”中,鲁迅就认为陀思妥夫斯基的小说显示着“灵魂的深”,“所以一读那作品,便令人发生精神的变化。”而陀思妥夫斯基写出这种灵魂的深,将灵魂显示于人,在鲁迅看来是“在高的意义上的写实主义者”。
陀思妥夫斯基“捉住了心中所实验的事实,使读者追求着自己思想的径路,从这心的法则中,自然显示出伦理的观念来”,是“穿掘着灵魂的深处”,是“使人受了精神底苦刑而得到创伤”,是“从这得伤和养伤和愈合中,得到苦的涤除,而上了苏生的路”,而这不正是鲁迅在《阿Q正传》以及《呐喊》中想要达到的目的?而这一次“竭力想摸索人们的魂灵”的鲁迅终于让《阿Q正传》被翻译成了俄文,绍介到了陀思妥夫斯基的祖国,或者也是一种开创性贡献,而这也是在高墙之外的这边,鲁迅以自己的实践,以基于自身的革命文学实践,用“写实主义”描绘了“眼里所经过的中国的人生”,同时也是作为一个痛苦的经历者摸索到了“人们的魂灵”。
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之后是鲁迅的《自叙传略》,在回到自我意义上,鲁迅回顾了自己初做小说的情形:“因了我的朋友钱玄同的劝告,做来登在《新青年》上的。这时才用“鲁迅”的笔名;也常用别的名字做一点短论。”而在之后的《自传》中,鲁迅则具体回忆了自己的曲折经历:“因为做评论,敌人就多起来,北京大学教授陈源开始发表这‘鲁迅’就是我,由此弄到段祺瑞将我撤职,并且还要逮捕我。”之后离开北京,到厦门大学座教授,半年之后因为冲突便去了广州,在中山大学做了教务长兼文科教授;之后半年,国民党北伐之后是“清党”,“我一生从未见过有这么杀人的,我就辞了职,回到上海,想以译作谋生。”后来国民党开始通缉,“我便躲了起来”;之后又加入了左联,但是,“到今年,我的一九二六年以后出版的译作,几乎全被国民党所禁止。”做评论多了敌人,被段祺瑞政府通缉,被国民党通缉,著作被禁止……这便是鲁迅经历的种种遭遇,当经历了这些,当鲁迅在一九三四年将此前未曾编入的诗文汇集成“集外集”的时候,是不是也是一种所谓不在以“革命文学”自命的“躲”?
一九三二年十月十二日“偷得半联”写成的“自嘲”是鲁迅自我审视的一首诗歌,“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交的是华盖运,身体已被碰上,“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中透露的是无奈,“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中却是一种决然,在无奈而决然中,“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反倒变成了不同流合污的态度,不管春夏秋冬的外在变化,躲进小楼便有一统的小天下,这小天下里是硬骨头的性格和勇敢坚毅的战斗精神,而这“集外集”也正是鲁迅的小楼。在《序言》中,鲁迅认为那些未曾收入文集的诗文,有些是因为没有留存底子漏落的,有些是故意删掉的,有些是抄译得年远而想不起来,“或者因为不过对于一人,一时的事,和大局无关,情随事迁,无须再录;或者因为本不过开些玩笑,或是出于暂时的误解,几天之后,便无意义,不必留存了。”
但是这些诗文却也构筑了鲁迅的一个向度,他认为这些“少作”,既是“少年之作”,是“乳犊不怕虎”,“出屁股,衔手指的照相,当然是惹人发笑的,但自有婴年的天真,决非少年以至老年所能有。”比如一九一八年的《梦》,是白话诗歌,“很多的梦,趁黄昏起哄。/前梦才挤却大前梦时,后梦又赶走了前梦。/去的前梦黑如墨,在的后梦墨一般黑;去的在的仿佛都说,‘我真好颜色。’”梦是颜色许好,暗里却不知,“而且不知道,说话的是谁?”这梦也如白话诗歌一样,虚无着,却又隐喻着。梦连接起黄昏和黎明,连接起前梦和后梦,是一种更迭?是一种革新?是新与旧的较量?是生与死的抉择?诗歌《爱之神》中用射箭的“小娃子”之口说出了这种人生观,“总之我的箭是放过了!/你要是爱谁,便没命的去爱他;你要是谁也不爱,也可以没命的去自己死掉。”一样在《人与时》中,有人说将来胜过现在,有人说现在不及从前,“从前好的,自己回去。/将来好的,跟我前去。”
诗歌里不只是少年的天真,也有着鲁迅的态度,梦之“好颜色”,爱神之箭,人对于时间的选择,无不是一种向前的坚毅和决绝,这是“少作”的态度。而另一方面,这“少作”也是“躲进小楼成一统”中坚持自己而成的文,既是精细的,也有着“不满自己之处”,“我佩服会用拖刀计的老将黄汉升,但我爱莽撞的不顾利害而终于被部下偷了头去的张翼德;我却又憎恶张翼德型的不问青红皂白,抡板斧‘排头砍去’的李逵,我因此喜欢张顺的将他诱进水里去,淹得他两眼翻白。”讲究策略,讲究方法,但对敌的方向是不变的,画出魂灵的目标是不变的,独自战斗的风范是不变的,既呐喊也在彷徨,“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题<彷徨>》)”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51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