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09-08《静静的顿河》:土地上种的是哥萨克的头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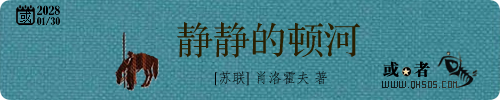
好啦,葛利高里在多少不眠之夜幻想的那点儿心愿终于实现了。他站在自家的大门口,手里抱着儿子……
——《卷八·十八章》
哥哥死了,妹妹死了,父亲死了,妻子娜塔莉亚死了,生命中那朵爱与欲的“迷人的野花”阿克西妮亚也死了,甚至朝着北面顿河的家也破败不堪,当战争破坏了这一切,当死神夺走了这一切,“他已经丧失了一切他最心爱的、最宝贵的东西。”不仅仅如此,他自己也不是一个自由人,顿河肃反委员会政治局等着他去自首,葛利高里的心愿为什么反而实现了?因为顿河还在,因为他还是一个哥萨克,更因为两个孩子还活着,他站立的地方是自家的大门口。在静静的顿河流淌中,死去的一切都已经发生,它像河水一样终归是一种流逝,而孩子、家已经自己还在,更重要的是,他自己却始终战战兢兢地紧抓住土地,“这就是他生活中剩下的一切,这就是暂时还使他和大地,和整个在太阳的寒光照耀下,光辉灿烂的大千世界相联系的一切。”
战争没有真正结束,死亡还会继续发生,活下来,面向顿河活下来,站在家门口活下来,紧抓住土地活下来,也许对于葛利高里来说,这就是可能的意义,也是肖洛霍夫在这篇史诗般的小说中对于命运真切地关注,“葛利高里的生活变得就像野火烧过的草原,漆黑一片。”他不是英雄,或者他也不会成为英雄,但是在被野火烧过的草原,还是那片不被毁灭的土地,土地就是生命,土地就是未来,土地就是希望,因为这是属于哥萨克人永远“光荣的土地”——葛利高里最后的命运铺陈在土地上,而肖洛霍夫从一开始就凸显出了和命运相关的土地情结。
“我们光荣的土地不是用犁来翻耕……/我们的土地用马蹄来翻耕,/光荣的土地上种的是哥萨克的头颅,/静静的顿河到处装点着年轻的寡妇,/我们的父亲,静静的顿河上到处是孤儿,/静静的顿河的滚滚的波涛是爹娘的眼泪……”用马蹄来翻耕的土地,种下的是哥萨克的头颅,顿河装点着年轻的寡妇,到处是孤儿,波涛是爹娘的眼泪,但是这依然是光荣的土地,只有土地在,像葛利高里一样的哥萨克人依然活着,依然在找寻着希望,依然可以面对未来。但是,也正是因为光荣的土地上承载了太多的苦难和不幸,见证了太多的死亡和毁灭,所以对于“静静的顿河”来说,它永远不是静静的,永远在咆哮着询问着人类命运的母题:“噢噫,静静的顿河,我们的父亲!/噢噫,静静的顿河,你的流水为什么这样浑?”为什么这样浑浊?是因为它必须这样浑浊,它流着的不是河水,而是血和泪,“寒泉从我静静的顿河的河底向外奔流,银白色的鱼儿把我静静的顿河搅浑。”
肖洛霍夫引用《哥萨克古歌》,就是为了揭示这片土地的苦难,就是在审视顿河的悲歌,而对于生活在其中的葛利高里,或者对于哥萨克民族来说,为什么必须面对用马蹄翻耕的土地,必须面对浑浊的顿河?这是一个和民族有关的主题,卷一的第一章讲述了葛利高里的“前历史”,却已经将哥萨克复杂的民族命运展现出来。第一句:“麦列霍夫家的院子在村子的尽头。”牲口圈的两扇小门面对的就是北面的顿河,在村子的尽头,一种边缘化的存在,而葛利高里的祖父麦列霍夫·普罗珂菲回到村子时,他也是一个边缘化的人物:一方面他是“参加倒数第二次土耳其战争”之后回来的,战争让他离开家园,回来其实让曾经的一切发生了改变,这就是最重要的另一方面:他带回了一个女人,被俘虏的土耳其女人。哥萨克和土耳其作战,土耳其女人也是麦列霍夫·普罗珂菲的敌人,但是她却成为了他带回来的女人,自然,这是一种对哥萨克人的某种亵渎,麦列霍夫·普罗珂菲被分了出去,父亲从此再也没有进过儿子的家门;麦列霍夫·普罗珂菲每次出去,总是抱着土耳其女人,然后坐在那块被风雨侵蚀地千疮百孔的巨石,两个人坐着,然后麦列霍夫·普罗珂菲又把她抱回家,他们和村子里其他哥萨克人的生活几乎隔绝;终于,人们开始把她叫做“母狗”,并在那天将她打死了。
土耳其女人终于无法在哥萨克的村子里活下去,但是早产的婴儿却被麦列霍夫·普罗珂菲救了下来,他就是葛利高里的父亲潘苔莱,就在一切毁灭之后葛利高里还有两个孩子,孩子就是希望,这个希望就是重新回到哥萨克生活的开始,麦列霍夫·普罗珂菲给潘苔莱娶了哥萨克姑娘,“从那时起,土耳其血统就和哥萨克血统交融了。”也从此还被人叫做“土耳其人”的麦列霍夫家族在村子里繁衍起来。这就是麦列霍夫的家族历史,也是葛利高里的“前历史”,它混合了战争和和平、哥萨克和土耳其血统,但是在这片土地上整个家族开始了繁衍,“高鼻子、带点野性、漂亮的哥萨克麦列霍夫家族”,它依然属于哥萨克。葛利高里的“前历史”是一种混杂的存在,而当葛利高里的人生被展开,他身上流着的血液里也有着哥萨克人复杂的情感。
这种复杂的情感在葛利高里身上首先就是关于爱情的混杂状态,他喜欢上了邻居阿克西妮亚,一个丰满、充满野性的女人,但是阿克西妮亚是邻居司捷潘的妻子,父亲潘苔莱一开始就警告他不要和阿克西妮亚来往,他称之为“造孽”,这是从道德立场出发的反对,但是对于葛利高里,对于阿克西妮亚来说,这种感情就是一种爱。阿克西妮亚把这种爱叫做“晚来的爱情”,因为她和司捷潘的婚姻里根本没有真正的爱,甚至司捷潘经常大骂她,暴力充斥着阿克西妮亚的生活,而追溯她的故事,她更是一个受害者,在她十七岁嫁给司捷潘之前,她被亲生父亲强奸了。被强奸,被毒打,这就是属于阿克西妮亚的人生,所以当她遇到对她投来暧昧目光的葛利高里,她认为自己找到了“晚来的爱情”,“每当葛利什卡的两只黑眼睛有力、疯狂而爱抚地盯着她的时候,她就觉得又温暖又愉快。”而葛利高里更是迷上了她,他把她看成是迷人的野花,浑身散发着女人的风骚魅力,对于葛利高里来说,这种爱本身就没有道德规则的约束,“我压根儿就不想娶亲。也许有那么个女人,不用娶她也会爱我。”和阿克西妮亚对这份情感的定义一样,“为了我过去受的那些罪,我要爱个够……哪怕将来你们把我打死也罢!葛利什卡是我的!我的!”
一个无视道德约束追求自己想要的女人,一个则痴迷地沉溺在晚来的苦恋中,和葛利高里的“前历史”一样,这是一种混杂的情感,“从河底冒出来的寒泉……热情的肉欲……像猛兽一样在心中……思恋和狂热的诱惑……用神圣的十字架……最纯洁的、最神圣的圣母……把上帝的奴隶葛利高里……”阿克西妮亚断断续续地听到的这些话语,便慢慢演化成了两个人的不羁命运,尤其对于葛利高里来说,也注解了之后作为一个哥萨克青年在动荡岁月里的多舛人生:它是肉欲的,也是神圣的;它是不受束缚的,也必受到惩罚;它是属于自我的,也必将被围观……就在葛利高里和阿克西妮亚越陷越深的时候,父亲潘苔莱为他物色了一个哥萨克女子娜塔莉亚,而被逼无奈的葛利高里也和娜塔莉亚走进了婚姻殿堂,“放荡够啦……放荡够啦!”这是葛利高里对自己讲的话,他进入了道德世界,进入了父亲的规则之中,这才是更大悲剧的开始,因为这不将是他和阿克西妮亚之间的纠葛,不再是和阿克西妮亚的丈夫司捷潘之间的冲突,而把无辜的娜塔莉亚卷入其中:葛利高里依然会和阿克西妮亚约会,上了战场之后又离娜塔莉亚远去,娜塔莉亚写信给他表达自己的苦闷和孤独,葛利高里的回信只有一句话:“一个人活下去吧。”当娜塔莉亚生下了两个孩子,葛利高里的心回到了她身上,但那只是一种习惯,他的冷漠,他的绝情,是六年婚姻生活的写照,最后娜塔莉亚在绝望中选择了“自杀”,那个在肚子里的孩子和她一样成为了这场婚姻的牺牲品。
| 编号:C38·2220618·1842 |
爱欲和婚姻,构成了葛利高里人生的一个侧面,如果没有战争,对于葛利高里来说,在阿克西妮亚和娜塔莉亚之间的选择依然是一种悲剧,“我很可怜你,这些日子,咱们好像亲近了一点儿,可是我心里依然空空的……空得很。就像这会儿的草原一样……”这是葛利高里曾经对娜塔莉亚说的话,在他看来,他无法爱着一个不爱的女人,他只是可怜他,只是为了完成一场婚姻,甚至只是为了传宗接代,但是在内心来说,他是空洞的,他只能在阿克西妮亚的身上找到那种爱的存在感,所以娜塔莉亚变成了悲剧,而阿克西妮亚呢?一个肉欲和神圣结合的产物,一个遭受暴力想要爱的女人,本身也带着矛盾性,为葛利高里生下的孩子死于猩红热,在庄园做工时和地主少爷叶甫盖尼暧昧,最后经受住了考验,在战争期间和葛利高里分分离离,最后他们没有去成南方,一颗子弹射进了她的身体,最后他亲手埋葬了阿克西妮亚,“他向她道了别,坚信,他们的离别是不会很长久的……”
葛利高里的婚姻和爱,都以悲剧的方式上演,两个女人,为他活着或者他为她活着,都无法演绎完美和幸福,而这也是葛利高里命运的一种写照,而以葛利高里个体的命运沉浮为线索,肖洛霍夫其实想要展现的是哥萨克民族的命运,当他将这种命运放置在战争年代的时候,这其实已经变成了历史的选择:历史和战争有关,战争区别了敌我,战争的出路是和平,战争制造了死亡,战争扭曲了灵魂,那么生活在其中的葛利高里,是不是历史悲剧的一个标本?“这该死的军役,拆散人家的魔鬼!”这是葛利高里对战争的第一次控诉,它改变了自己的生活,他逼迫自己和家人分离,但是战争远不止这些,当“要打仗啦”成为顿河地区哥萨克人必须面对的现实,一切都被改变了,就像在坟场听到猫头鹰叫的老人们所预言的那样:“灾祸临头啦。”
葛利高里服军役成为一名哥萨克战士,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付奥地利人的战斗,他和战争关系完全就写在那本哥萨克人的日记本中:起先认识了一个姑娘,后来坠入了情网,但发现两个人毫无共同之处,于是开始悲观,开始厌世,但是,战争来了,“有办法啦!上前线打仗去。荒唐吗?很荒唐。不感到害臊吗?”战争变成了一种救赎,是为了忘记现实的残酷,才在别无他路中走向战场,而进入战场,是不是更是别无他路的做法,上前线,要为“信仰、沙皇和祖国”而战,看见道路两旁的尸体,最后一天的日记写着:“马拴在系马桩上喂了一昼夜,现在我们又要开赴前线了。我已经疲惫不堪。号兵吹起上马号。此时此刻,向谁开枪,我都高兴!……”很高兴,因为可以开枪,但是同样可以开枪的是敌人——他死了,死在公路旁,那本日记本被葛利高里发现,和笔记本在一起的还有半截化学铅笔和一个钱包。
葛利高里发现了笔记本,葛利高里阅读了日记,葛利高里也成为了日记中的人物,和其他哥萨克一样,他被命运推进了战争的深渊。“被恐怖割掉了内容的思想,像个沉重的缠得紧紧的线团,在脑子里里乱滚。”但是走向战场就意味着杀敌,葛利高里完成了第一次杀人,那个身材高大的奥地利人“几乎对准葛利高里放了一枪”,葛利高里挥刀劈去,“奥地利人扎煞着手,像滑倒了似的,倒在地上,那半个头盖骨闷声落在马路的石头上。”第一次杀人,葛利高里经受住了考验,但是在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战场上,生或死都是一种偶然,而由此葛利高里的战争观开始慢慢形成:“他的脚步又乱又重,就像肩上压着不能胜任的重负似的;憎恶、惶惑在折磨他的心灵。他把马镫抓在手里,半天也抬不起那只沉重的脚。”他杀死了敌人,他的内心是憎恶,是惶惑,是折磨,没有一点害怕,却全部变成了内心的痛苦。他在遇见哥哥彼得罗的时候,说出了对战争的反感,“他们唆使人们到处互相杀戮!简直变得比狼还凶残。哪里都是仇恨。”当杀死了一个人,葛利高里说自己的良心受到了折磨,甚至在夜里也会梦见被自己杀死的人,彼得罗告诉他的是,“你不要冲到别人的前头去,不然的话,死神可是专门找急性人!多多保重!”
|
| 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永远在流淌 |
彼得罗对他说出的是逃避主义的战争观?而那个叫“锅圈儿”的战友对他说的是:“你的天职——就是砍杀,别的全不用问,打仗杀敌,这是神圣的功业。你每杀一个人,上帝就宽恕你的一桩罪过,就像杀死一条毒蛇一样。”战争让杀人合理化,而且被神圣化,上帝不会惩罚战争中的杀人者,反而在砍杀中完成神圣的功业。也就是在这种合理化甚至神圣化的杀人面前,“锅圈儿”毫无顾忌地杀死了匈牙利俘虏,在死亡面前葛利高里不解地问:“你无缘无故地把他砍啦!”也许第一次杀人给葛利高里带来的是憎恶,也许彼得罗的逃避主义是为了让自己活下去,也许“锅圈儿”大开杀戒是为了免除内心的罪恶感——对于葛利高里来说,一开始的种种不适和不解,也终于在沙场上麻木了,获得十字勋章,得到晋升,眼睛受伤,他已经再无法远离战场,对于死的疑问也不再是一个问题。
战争观在转变,但是对于葛利高里来说,对战争的思考已经不再只是生与死的问题,不再是杀人的合理化问题,而变成了战争的意义问题。这是葛利高里经历和思考的第二个问题,这个问题就像是利斯特尼茨基在谈话中抛出的一个关于哥萨克站位的问题:“他们跟谁走?”一九一六年战争已经进入到了白热化程度,本丘克少尉的说法是:“政府养活的哥萨克,就像系在木棍上的石头。紧要关头,政府就要用这块石头去打破革命的头盖骨。”作为一名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党员,一个布尔什维克,身上带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念着机关报《共产党员》中几段话的本丘克是要灌输布尔什维克思想;而任命为西南战线总司令的科尔尼洛夫是白军将领,当利斯特尼茨基问出关于哥萨克人抉择的问题“他们跟谁走?”的时候,其实就倾向于跟科尔尼洛夫走,“就让科尔尼洛夫做大独裁者吧,——他是哥萨克军队的救星。在他统治下,我们也许会比在沙皇当朝日子过得还要好些呢。”于是在《十二个哥萨克军区宣言》中,哥萨克军人联合会建立,而顿河地区,从此“撒下了一张像黑色的蜘蛛网一样的大阴谋网”。
二月革命,六月战役,以及武装政变,临时政府被推翻,之后的十月革命,消息不断传来,“许多人很高兴,盼着战争马上停止”,但是哥萨克人并没有看到命运的真正出口,而葛利高里心中始终有一个信念,那就是“忠实地维护着哥萨克的光荣”,但是哥萨克的光荣到底是什么?“他们跟谁走”变成了葛利高里的“我跟谁走”的问题,在十月革命后,他被任命为连长,认识的伊兹瓦林告诉他的是:“我们既不要布尔什维克,也不要君主政体。咱们需要自己的政权,首先是要摆脱一切监护人——不管是科尔尼洛夫,克伦斯基,还是列宁。不用他们我们在自己的土地上能搞得蛮好。上帝保佑,让我们摆脱这些朋友,至于敌人我们自己对付得了。”而波乔尔科夫对葛利高里说的是:“既然打倒了沙皇和反革命,就应当竭力使政权转移到人民手中来。你说的那是哄孩子玩的。古时候是沙皇压迫咱们,现在不是沙皇了,却又来了另外一些人要压迫咱们,咱们的日子会更难过!……”哥哥彼得罗对葛利高里说的则是:“你应该明白,哥萨克——过去是哥萨克,将来仍然是哥萨克。不能让臭俄罗斯人来统治咱们。你可知道,如今那些外来户怎样说吗?把所有的土地按人口平分。这怎么样?”
不仅仅是哥萨克人该选择跟谁,哥萨克人也出现了分化,有部队跟着红军走了,有部队则留在顿河地区,还选举产生了顿河军会议代表,当选为顿河军司令官的克拉斯诺夫少将对哥萨克说的是:“强大的顿河军会议将要统治顿河地区!我们将重建被革命瓦解了的哥萨克社会,恢复古代哥萨克美好的生活方式。”不管是红军还是白军,不管是苏维埃政权还是哥萨克政权,不管是哥萨克自洽军还是志愿军,在这片土地上,跟谁走的问题其实是关于制度的选择,但是对于葛利高里来说,每一次选择都是为了维护哥萨克的光荣,但是最后连他自己都不知道,哪一个派别,那一种制度,是哥萨克人的正确选择?甚至一切的问题都变成了一种好奇人,就像是当初参加战争时面对敌人时他的第一个想法是:“这是些什么人?是些什么样的人?”选择苏维埃政权又憎恨起苏维埃政权,渴望哥萨克建立自己的政权却又害怕回到独裁之路,无奈的选择,选择的无奈,到最后对于葛利高里来说,变成了一个更为本质的问题:每一种政权都是为了土地的利益,所以,“我们就像争夺情人一样,在为抢占土地厮杀。”伴随着对政权可能选择的否定,葛利高里更是在内心破解了哥萨克人苦难的根源:“不论共产党还是将军——全是枷锁。”
战争是对于土地的抢占,所以对于哥萨克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要有属于自己的土地,“土地不是抢来的,而是浴血奋战得来的!我们的祖宗用鲜血浇灌了这块土地,也许,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我们这块黑土地才这样肥沃。”这才是一种归属。的确,葛利高里目睹了不同政权的杀戮,而当哥哥彼得罗死于布尔什维克米什卡之手的时候,内心更是走向了崩溃,一个是哥哥,一个是曾经最要好的邻居,一个却是哥萨克士兵,一个是红军——战争变成了个体之间的生死。而当他最后和阿克西妮亚在一起,漂泊之中那一颗子弹也射进了她的身体……
从对战争的不同态度,到对制度的不同选择,无法避免的死亡总是在发生,当最心爱、最宝贵的东西都毁于战争,悲剧的源头便是那块饱经创伤的土地,但是这块土地也是生命最后的依靠,土地不死,命运不死,就像葛利高里呼唤着儿子米申卡的名字,就像还在流淌的静静的顿河,“光荣的土地上种的是哥萨克的头颅”,它是苦难成长凝结的精神,它是眼泪和鲜血浇灌的生命,野火烧过的草原还会有另一片绿色。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68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