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9-08 《信的影像》:喃喃自语说着未来之事

咳嗽声传来的时候,是如此清晰,它几乎覆盖了街垒战斗的枪击声,湮没了车行驶于路上的摩擦声,或者取代了影像交错时出现在音轨里的声音,咳嗽是老去的标记?是病态的停顿?还是戈达尔在阐释着一种必须标明的孤独立场?
2014年,戈达尔已经84岁了,他活着,却已经深居简出,把自己关在家里,其实是关在那些影像里,那是他的信仰,那是他的世界,那是他灵魂必须栖居的地方,“我在追随它们的栖居之所,在传道书的庇护下,喃喃自语说着未来之事,是的,我将行在原地。”当一切必须以庇护的方式活着,当一切只能喃喃自语,在面向“未来之事”的在场里,一定是有着必须的缺席,所以在这句话之前,戈达尔是给戛纳电影节的评委说出了自己的态度:“我亲爱的主席先生,导演同志:同志们邀请我走上庄严的24级台阶,我只是在人群中感到迷惑,每秒如是,我不再是这个群体中的一员。”
庄严的24级台阶,亲爱的主席,尊敬的导演,或者构筑了戈达尔向戛纳电影节致敬的理由,但是在这个典礼上,也必定有各式的人群,有各种的电影,当戈达尔开始寻找属于自己的影像,寻找自己的庇护所,其实意味着在大庭广众之下的沉默。但是,他为什么要沉默?他为什么会缺席?他为什么会让自己行在原地?那个他拒绝的世界并非只是戛纳电影节,并非只是电影工业化,而是关于影像的危机。
|
| 导演: 让-吕克·戈达尔 |
 |
黑白的世界里,出现的是莫桑比克解放阵线,是1975年执政至今的莫桑比克正当;影像的世界里,出现的是街垒上的战斗,是荷枪实弹的对立方……政治或者革命,1975年或者1968年,那些已经过去的事件,在电影世界里出现,是一种如实的记录,还是一种反讽?过去的历史总是通向现在,通向未来,当那个彩色镜头里的女孩从路上跑来的时候,她却叫着“柯雄先生”,但是被叫唤的人永远在镜头之外,奔跑是不是变成了一种无意义?或者说从过去奔向未来变成了一种未知?“悲哀如我,如此冬日,怎么可以找到花朵?”这是时间交代的无奈,苍白的冬天来了,那些鲜艳的、活在春天的花朵,已经像奔跑的女孩一样,找不到自己的那个“柯雄先生”。
找不到,其实是隐藏在镜头后面,它是将彩色世界变成黑白的力量,就像汉娜·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说的那样,“让卡瓦那死于极权主义。”汉娜·阿伦特的头像就在投影的上方,她注视着底下的世界,而戈达尔就这样走到屏幕前,然后侧着脸,一半的黑和一半的白,把世界分隔成两个部分:一个叫极权主义,一个叫个体主义,一种叫集权统治,一种叫孤独思考:“他们总是通过逻辑的力量,每每进行干涉,甚至强迫个体屈服。”那种逻辑的力量是“纯粹理性”?是允许不带任何看法的“自由”?而其实纯粹理性已经变形,个体自由已经丧失,而对于电影来说,真正的力量在于保持自己的声音,在于说出自己的话,所以在这一种现实里,孤独具有了丧失自己的风险,而哲学家也成为一种职业风险,“性而上学成了我们唯一的疑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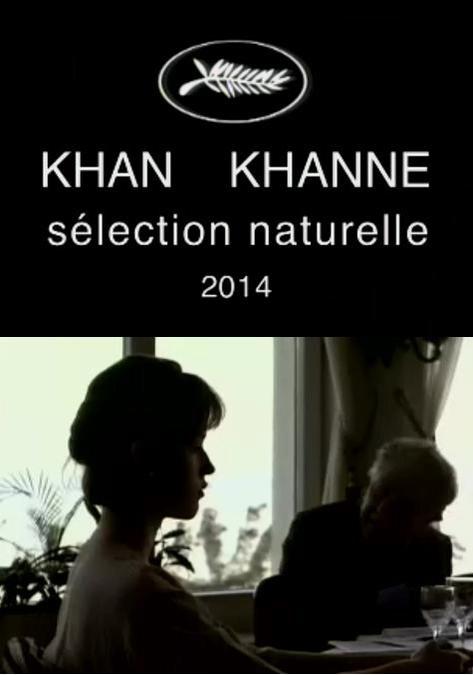 |
| 《信的影像》电影海报 |
戈达尔走下了台阶,离开了镜头,阿伦特的画像还在那里,对于极权主义的批评是不是依然像画像里一样,有着如炬的目光?实际上戈达尔的退出本身就是一种态度,那是沉默的开始,那是缺席的理由,影像里是李尔王的女儿考迪莉娅的一句台词:“但甚至更为频繁,但甚至更为频繁……”更为频繁的是什么?重复的台词是不是也是一种频繁?解构与建构的目的只有一个:用沉默来说话,用戏仿来讽刺。于是,“我与考迪莉娅共进午餐”成为一段新的影像:那人在大声地喝着汤,一勺一勺,一口一口,发出的声音无法掩盖,像是故意要制造噪音,而在旁边的对话起初就是在镜头之外,像是被忽视的一个场景:“我不会将我的心涌上我的嘴。”女子这样说,仿佛是考迪莉娅在表明自己的态度,在“更为频繁”地制造喝汤的声音时,也许这样的沉默才是最好的反抗,于是另一个声音便是:“我也乐享她的沉默。”
沉默的反面是“更为频繁”地制造噪音,沉默的背面是伪装地解释,“解释的可能性在于似乎一直都是演说之所以存在的托辞……”所以在这种解释的可能性里,前一个镜头还是男人和女人的相拥相吻,后一个镜头则是女子突然倒地,在后一个镜头则是男子从女子的背后拿出了那一把刀。爱情有着解疑释惑?情感需要甜言蜜语?一把刀子永远在身后,一种死亡永远成为密谋,所以解释是一种借口。而在“更为频繁”制造噪音之后,在解释的可能性变成永远闭嘴的影像之后,便是“我不会将我的心涌上我的嘴”的沉默,沉默是享受,沉默是拒绝,沉默也是反抗——沉默的世界里有雅克·蒂塔,有特吕弗,有新浪潮,当然也有戈达尔。
“这不是一部电影,尽管是我最好的一部。”雅克·塔蒂还是说话了,在否定和肯定之间,她表达的是自己,“不是一部电影”是在拒绝别处的电影,“最好的一部”是在保留着自己,那是自己的庇护所,那是自己的传道书,那是自己的时间和影像,那是自己的心和自己的嘴。于是戈达尔向世界发出了自己沉默的声音:“这个五月的21号,亲爱的同志们,我不可能与你们在一起……在你们下一场的宿命里,找到真正的从始至终的谬误。”落款是:“你们的朋友让-吕克·戈达尔”。
下一场成为宿命,通往未来的时间里,只剩下戈达尔的喃喃自语,而那声咳嗽响起的时候,正是特吕弗的那句话:“而今天,一如往常。”今天就是过去,今天也是未来,在没有被改变的信仰和理想中,在一如既往的自由和孤独里,世界总是缺席在“更为频繁”的声音里,总是沉默在拿着刀子的“解释的可能性”里。当黑白的影像变成彩色,是一只2013年1月31日拍摄的狗,它是安详的,但是最后那只狗却死了,在真实被记录的影像里成为无法反抗的宿命,而戈达尔用这只狗似乎就在说明自己想要用沉默来逃逸这种宿命的决心:四年前,他获得第84届奥斯卡金像奖终身成就奖,但是他没有前去领取;2014年,戈达尔在《信的影像》里“喃喃自语”,他在同年的戛纳电影节中,用《再见语言》里的那条狗为自己代言;而2018年,再次缺席的他用《影像之书》亮相戛纳电影节,表明自己的态度——无论是缺席还是沉默,戈达尔变成了“影像化的戈达尔”,而电影在沉默的世界里,只带着一声咳嗽说话:“我不会将我的心涌上我的嘴……”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34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