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09-08《尼采与哲学》:悲剧就是掷骰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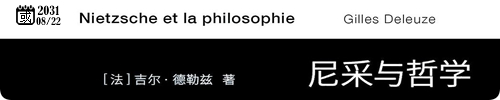
这“哪一个”的问题回荡在每一个事物中,为每一个事物鸣响:究竟是哪些力?是哪一种意志?这是一个悲剧性的问题。
——《批判》
问题和问题是不同的,当我们寻求关于本质的答案时,会提出“什么是”的问题,“什么是”作为不言而喻的问题,指向的就是最本质的存在,它揭开的也是关于本质的答案,但是尼采却否定了“什么是”的问题方式,他给出的是“哪一个”——哪一个指向个体?指向现象?甚至指向偶然和随意?它如何变成了对于本质的揭露?
尼采的提问方式在吉尔·德勒兹看来,就是一种批判的思维,批判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开始的形而上学:当我们问“什么是”的时候,就是落入了形而上学“最卑劣”的窠臼,因为它从来不指向真正的本;“什么是”实际上所问的还是“哪一个”的问题,但是看起来变得愚笨、盲目和令人困惑;因为当提出“什么是”的时候,它所寻求的还是由“哪一个”出发而揭示的答案,比如“什么是美”的问题,就是在寻求“从哪一个角度事物显示它的美”,或者是“从哪一个角度看似不美的事物显得不美”?或者“哪些力通过占有它使它变得美丽”?也就是说,尼采的提问方式面向的是具体的、多元的存在,它和每一个事物有关,和每一种力有关,和每一种意志有关,“哪一个”尽管是一种多元主义的表现,但是正是多元主义才不否定本质,“它使本质在每一种情况中都取决于现象与力的密切关系,取决于力与意志的默契配合。”
对“什么是”的提问方式的否定就是对形而上学的批判,而尼采的“哪一个”更是在本质意义上提出了悲剧性的问题,德勒兹说,“哪一个”的问题真正把我们领到本质问题上,因为,“本质永远是意义与价值。”而在德勒兹看来,正是尼采将意义和价值的概念引入哲学,他才建立起了关于本质的系谱学,而现代哲学也是从尼采对于本质揭示的“哪一个”中汲取营养,开始了一种真正批判的哲学。批判的问题就是本质的问题,本质就是意义和价值。首先在价值上,德勒兹认为,“批判的问题是关于价值的价值问题,是产生价值评价的问题,因而也是价值如何被创造的问题。”也就是说,批判真正实现,就是建立价值哲学,价值哲学是彻底的批判的可能实现的唯一途径,在这里,尼采的批判哲学是一个不可分割的二元运动,一方面让一切事物和起源返回到价值,另一方面让这些价值返回到其起源并确定其真正价值的事物,这样的二元运动就是尼采的“双重抗争”:他反对那些使价值逃避批判的人,他们就是康德和叔本华一类的“哲学工匠”;他也反对通过从简单的事实和所谓的客观事实中推导出价值来批判的人,他们则是功利主义者或所谓的“学者”。
价值是起源的价值,起源是价值的起源,这就是德勒兹所说尼采的“系谱学”,“系谱学意指价值从中获得自身价值的区分性因素。”在这里德勒兹强调的一个概念就是“区分性因素”,当系谱学关乎起源和出身,实际上就意味着本质意义上存在着“区分性因素”,也就是起源中的差距或距离,起源中有高贵和卑微的区别,有高贵与粗俗、高贵与堕落的区分,这就是区分性因素,它形成的就是系谱学中的差异和等级,也只有在区分性因素形成的差异和等级中,批判才成为可能,所以德勒兹认为,尼采的系谱学是对科学与哲学的重新组织,“是未来价值的确立者”。在价值中存在着区分性因素,在意义中同样存在,什么是意义?德勒兹认为,尼采是在现存的力中找到意义的症候的,他用意义与现象的关联取代了表象和本质的形而上学二元对立,取代了科学中的因果关系,也就是说,同一个事物、同一个现象,它的意义是根据占有它的力而变化的,事物的表现有时是这样有时是那样,这一切都取决于占有事物的力,而这就是尼采的多元主义观点,它是“这个,然后是那个”的具体体现,也是“哪一个”的具体回答,正是这种认为事物具有多重含义、认为存在很多事物的多元主义,才是哲学的最高成就:这就是力的哲学,是力产生的差异,是力连接为事物,而这就是本质,“从另一个角度看,本质又可以被界定为事物所有意义中与事物关系最为密切的力。”
为什么哲学的最高成就是尼采提出的力的哲学?力一样是区分性因素造成的差异,力的关系构成了一个身体,这个身体既是化学的、生物的,也是社会的、政治的,之所以构成身体,就在于不平衡的力形成了关系,而力构成身体在尼采看来是偶然的结果,“偶然不仅表现为力与力之间的关系,同时也是力的本质。”力的本质表现的身体于是也是一个多元的现象,但是这种多元现象却是一种“支配的统一”,这种统一表现为高等的支配力对低等的被支配力的统一,高等的支配力是一种能动力,低等的被支配力是一种反动力,能动力和反动力形成的力的关系看上去是一种质差,但实际上是通过量差形成的,而量差所反映的差异就是等级。什么是能动?尼采在《权力意志》中作出的解答是:“主动追求权力就是能动。”侵占、占有、征服和支配都是能动力的特征,能动力所体现的就是创造。无疑不管是能动力和反动力之间的关系,还是能动力的量的不同,都会形成差异,当这样的差异被消除之后,它就变成了科学的功利主义和平等主义——由此尼采建立了批判的三个层面:反对逻辑的等价,反对数学的等值,反对无力的平衡。
| 编号:B83·2240516·2120 |
这就是尼采消除差异的三种形式,反对消除差异意味着对力的差异的肯定,而肯定也是对“不同量的力的不期而遇”的偶然的肯定,这种肯定是对力的多元的肯定,是对力的关联的肯定,肯定的力作为一种创造,就是尼采的“权力意志”,“力的胜利概念——我们的物理学家用它来创造上帝和世界——仍然需要完善;必须把一种内在的意志赋予它,我把它称为权力意志。”权力意志归属于力,它既是力的补充也是某种内在于理的东西。权力意志体现的是力的关系,而力也是凭借权力意志才得以战胜、支配或指挥其他的力,这是尼采对哲学的另一贡献,在德勒兹看来,权力意志就是尼采系谱学最大的意义所在:权力意志是力的区分性因素,力意志把偶然置于它的中心,所以只有权力意志才能够肯定一切偶然,而系谱学就是意味着区分和起源;在力的关系中,力的量差和各自的性质都源于系谱学因素的权力意志;力的性质的原则是权力意志;权力意志不仅起着诠释的作用,而且起着评价的作用,一句话,“权力意志是系谱学的因素,正是从它那里,意义获得自身的含义,价值获得自身的价值。”所以关于价值和意义的本质就是权力意志。
尼采的批判提出了两个重要的概念,一个是超人,一个则是“价值重估”,在德勒兹看来,这两个概念所针对的就是辩证法,超人针对的是辩证法中人的概念,价值重估针对的则是辩证关系中的异化和压制作用。辩证法建立了同一、因果等概念,引入了否定、对立或矛盾的思辨因素,将辩证法变成了一种辛苦的劳作,而在尼采看来,辩证法具有一种当做奴隶的思维,“在此,矛盾的抽象思维战胜了肯定差异的具体情感,被动压制了主动,复仇与怨恨取代了进攻。”这在本质上就是对力的否定。尼采认为,力即使处于服从的地位,也不是一种否定,而是肯定自己与他者的差异,“甚至以此为乐”,所以辩证法的思辨因素被尼采代以差异的实用因素,它以肯定和快乐建立目标。所以尼采的“是”与辩证法的“否”相对,肯定和否定相对,差异和矛盾相对,快乐、享受和辩证法的艰苦工作相对,轻盈、曼舞与辩证的责任相对。
尼采对力的肯定也是对生命的肯定,而且在德勒兹看来,这种肯定就是尼采悲剧哲学的重要内容。尼采的悲剧观在《悲剧的诞生》中就提出了,但是那时的悲剧在德勒兹看来还未能摆脱基督教辩证法的阴影,这一悲剧完全是一种辩护、救赎与和解的思路,尼采后来评价《悲剧的诞生》时也说“它散发着令人讨厌的黑格尔气息”。尼采的悲剧观是发展的,《悲剧的诞生》中的悲剧体现的事酒神精神,酒神是悲剧的本质,狄奥尼索斯是唯一的悲剧人物,他是苦难的化身,他最终将其发展成戏剧,在尼采看来,这样的悲剧就是一种和解,酒神以日神的形式在日神的世界中表达悲剧也是一种客体化历程。而在《悲剧的诞生》之后,对立不再是狄奥尼索斯和阿波罗之间辩证的对立,而成为狄奥尼索斯对苏格拉底的反抗,这种反抗就是对生命否定的对抗,对救赎与和解的对抗,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站在基督教辩证的反面,就是对生命的肯定,它通过查拉特斯图拉得以表达:“那高于一切和解的”便是肯定;那高于一切展开、解决与抑制矛盾的便是价值重估。
狄奥尼索斯肯定一切存在的东西,“甚至包括最深重的苦难”,她的肯定就是对多样和多元的肯定,就是对生命的肯定,而这就成为了尼采所阐述的悲剧的本质,在德勒兹看来,尼采所攻击的就是没有认识到悲剧是一种美学现象的悲剧理论,悲剧是快乐的美学形式,而不是通过解除痛苦、恐惧和表示怜悯的道德手段——而这就是基督教的悲剧观,当基督教的辩证思想取消了对生命的肯定,尼采才发出了“上帝死了”的宣言,在他看来,上帝之所以死了,是因为怜悯而死,什么是怜悯?“就是这种对近乎乌有的生命状态的容忍。”怜悯是对生命的爱,但这样的生命是虚弱的、病态的、反动的生命,所以最后上帝会因怜悯而窒息,因为反动的生命而被阻断,“上帝死了”折射的是一种否定的、反动的和被动的虚无主义,在尼采看来,犹太教、基督教、宗教改革、自由思想、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都是这样一种虚无主义,而且都是“同一种历史”。而当“上帝死了”,上帝变成了人,人变成了上帝,但是在尼采看来,这依然是一种同语反复,因为人总是反动的存在,人总是虚弱的、被贬的生命代表,总是虚无主义的本体,和上帝一样是虚无一直的“对象”,是虚无主义的“属性”。真正超越了人的就是“超人”,“人类如何被超越?我只关注超人;他——而不是人——是我的首先而且是唯一的关注。——不是最邻近者,不是最可怜者,不是最受苦者,不是最良好者。”
超人取代人和上帝,就是一种价值重估,在德勒兹看来,尼采建立的超人哲学就是对虚无主义的超越,“超人与更高的人有着本质上的区别;这种差别既存在于产生他们的权威中,也存在于他们分别所达到的目标中。”而在本质上,超人体现的就是生命的肯定性意义,就是悲剧的本质,“悲剧的意义是由多样和多元的快乐界定的,这种快乐不是升华的结果,也不是净化、补偿、顺从或者和解的结果。”在这里尼采的悲剧哲学就体现为生命哲学,体现为一种系谱学:“多样性是对统一的肯定;生成是对存在的肯定。”生成的肯定本身即是存在,多样性的肯定本身即是统一。尼采对生命的肯定就是对生成和多样性的肯定,在这里,德勒兹阐述了肯定思想体现的“掷骰子”游戏。
掷骰子无疑有两部分组成,一是骰子掷出的一刻,另一部分则是骰子落回的一刻,尼采认为掷骰子的两个过程发生于大地和天空两张不同的桌子上,大地是投资掷出之地,天空是骰子落回之地。当骰子掷出的时候,它就表现为一种偶然,而当它落回的时候,就变成了必然,不管是偶然还是必然,都是一种肯定,而且必然性也是为偶然性所肯定,“恰如存在为生成所肯定,统一为多样性所肯定。”在这意义上,尼采就是将偶然性等同于多样性,多样性就体现为碎片、片段以及摇动并掷出骰子时的无序,当然最重要的是,尼采把偶然变成了肯定,这也就意味着尼采否弃了原因/结果、可能性/结果的配对关系,代之以狄奥尼索斯偶然/必然的关联和狄奥尼索斯偶然/命运的配对关系,投掷不是概率而是所有一次性的偶然,不是最终的、渴望的、期盼的组合,而是命定的、钟爱的组合,体现的是“命定之爱”。
掷出的骰子肯定了偶然,但是落回的骰子呢?它也必然是一种肯定,是对回落的点数和命运的肯定,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落回的第二个时刻就是掷出和落回两个时刻的融合,这个第二时刻就是永恒回归,“它是骰子掷出的结果,是对必然的肯定,是整合偶然各部分的数。但它同时又是第一个时刻的回归,是投掷的重复,是偶然本身的再生与再肯定。”不仅仅赋予了游戏肯定性意义,而且尼采还以象征主义命名的对多样性、偶然性、生命的肯定。骰子掷出时,大地“颤栗着崩裂了”,于是喷射出“火焰的河流”,它是生成,是多的生成,“掷骰子的过程中诞生的舞蹈之星,甚至可以说是灿烂的星群。”从混沌到火到星群,尼采在多样性中肯定,在偶然性中肯定,在生成中肯定,这种肯定就是尼采的诗歌和格言,“从形式上看,格言呈现为碎片,是多元主义思想的表现形式;从内容上看,它主张清晰地表述某种意义。一种存在,一次行动,一个事物的意义——这些都是格言的目标。”所以德勒兹认为,“一切格言必须读上两遍”:第一遍是骰子掷出时,第二遍则是骰子落回时,它们构成了对永恒回归的诠释,而永恒回归就是悲剧,“悲剧就是肯定:因为它肯定偶然以及偶然的必然性,肯定生成以及生成之在,肯定多样性以及多样性的统一。悲剧是掷骰子。”
尼采系谱学揭示的是价值和意义,在“哪一个”的提问中阐述了区分性因素造成的差异;尼采通过对力的关系的解读,在“这个”和“那一个”中提出了多元主义;尼采在悲剧中提出了肯定和快乐的经验主义,尼采在掷骰子中发现了永恒回归的游戏……在德勒兹看来,尼采的意义就在于“超越”形而上学,这就是尼采的批判:批判辩证法,批判基督教思想,批判虚无主义,批判科学平等主义。尼采的批判更在于建构,多样性、生成和偶然在他看来是纯粹肯定的对象,而这个掷骰子的游戏最后以永恒回归的方式完成了统一,这就是最高的权力,就是肯定之综合,“肯定之轻对抗否定之重;权力意志的游戏对抗辩证法的劳役;肯定之肯定对抗著名的否定之否定。”这就是权力意志,“肯定成为权力意志的唯一特性,行动成为力的唯一特性,能动的生成成为权力和意志的创造性认同。”
当尼采让能动的生成成为权力和意志的“创造性认同”,德勒兹也在尼采身上发现了这种认同,反辩证法、反同一性、反因果关系、反矛盾律不也正是德勒兹的态度?多元主义、偶然性、生成、肯定,这些概念不正是活用为德勒兹哲学的一部分?1962年德勒兹出版了这部作品,直到这时,尼采才真正受到法国知识界的重视,德勒兹对尼采的解读成为法国哲学史上的一个转折点。而更重要的是,德勒兹在尼采身上发现了丰富自己哲学的价值和意义,而这也是权力意志的本质所在,“权力意志是多重肯定的原则、捐赠的原则或赠贻的美德。”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57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