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10-22《天安门诗抄》:人民的海洋飞卷起诗歌的巨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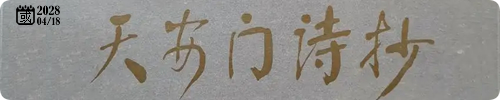
第一次去北京,经过天安门,应该是21世纪的事了,生命的前三十年,北京和“天安门”都是一种陌生的政治存在;即使是不从古旧书市中买来的这本诗集,从1997年购买到2022年翻开,摆放于书柜的某个角落,也是一种隐匿的存在。如果以世纪的起点为界,向前推22年是这本诗抄出版的时间,向后推22年则是打开书阅读的时间,前22年和后22年构成了事件和阅读长达44年的时间距离,当另一场政治盛会正在北京召开,当可以通过新媒体零距离观闻盛会的新闻,那个时代是不是就是一种历史?
甚至,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和作为整体的十年文革,也都在个体生命的感受之外,活着,却和被叙述的历史无关,历史似乎就是一种隔阂。而当距离44年后打开文本,历史以别样的方式被讲述:封面红色背景下的花圈、封二“本书承华主席题签”的说明,以及内文中工农兵、反修防修、四化、革命、新长征、八亿人民等词汇,勾勒出的就是一种历史的存在。历史的风格,历史的词汇,历史的说明,这无疑也是一部难以走进现实的历史文本——或曰之“档案”,正是对历史当下发生事件的一次记录,它以固化的形式保存着一段“愤怒出诗人”的记忆。
1976年4月5日,这是一个中国人在压抑之后情感爆发的日期,情感之所以爆发,首先的基调便是悼念。“大地春花发,江河分外妍。总理何处觅?八亿埋心间。”《浩气山河壮》传递的是思念;“清明时节泪纷纷,谁入广场不动情。抬头不见总理面,俯首碑前唤亲人。”《山呼海啸唤君回》表达的悲伤;“他没有遗产,他没有嗣息,他没有坟墓,他也没有留下骨灰。他似乎什么也没有给我们留下,但他永远活在我们心里。”现代诗《特殊的祭奠》在无和有之间叙说着人民的心声;“热血甘为党群洒,滴滴点点染晓霞。草木皆有立脚地,盖世栋梁竟无家。躯干化烬扬故土,忠魂成虹贯中华。千古人间传未死,遗灰落地已开花。”《忠魂成虹贯中华》表达的是对伟人的怀念。从周总理的逝世,也引出了对其他革命者的思念,组诗《悼陈老总》是对陈毅的悼念:“耿耿七旬遏陷害,妖邪误国歹徒心。”而《开慧烈士万载传》四首则是对杨开慧寄托哀思:“学习英雄有何罪,坐牢杀头大无畏。”——很明显,不只是哀悼和怀念,更是重申革命者的“革命”意义,而在挽联中,有一副对联更是指向了背后的阴谋:“谁反周总理,和他拚到底;迫害邓小平,永远难得逞。”
从革命者个体的逝世上升到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抒情,也是诗抄中的基本情感。“总理一生,灿烂壮丽。丰功伟绩,人民敬极。总理安息,人民念忆。巨星陨落,人民痛泣。”这是《一腔衷曲》中的“衷曲”;“总理英灵,民族之魂。流芳千古,与世长存。”一个人已是“民族之魂”的象征;“人民渐自迷中回,革命呼声似惊雷。同志你今须记取,为国为民血光辉。”《群众从来是英雄》诗歌传递的是一种信念;从信念出发,也表达了国家和民族的希望:“红旗飘,军号响,子弟兵,杀声亮。不怕流血不怕死,前赴后继除奸党。乌云遮天难持久,红日永远放光芒。革命一定要胜利,敌人终将被埋葬!”这首《永别周总理,迈步新长征》就指向了未来的新长征;“清明雨绵绵,母女碑前站。默悼总理魂,痛忆三月前。泣声摧肝肺,鬓旁白发染.泪洒长安道,众献花圈圆。梦见总理面,醒瞻总理颜。阴冷冻手足, 暖流浸心田。英灵死犹生,遗言留世间。勇携众儿女,革命代代传。”《革命代代传》就是一种赓续式的革命行动;而《除了战斗,还是战斗》表达的是不息的战斗激情:“通往那里的路只有一条,/除了战斗,还是战斗。”
在对伟人逝世的哀悼、对民族之魂的抒情,对革命信念的坚持之外,在那个特殊节点,在那种历史时间,必然有着更多的愤怒:《正告你们》里是对敌人的警告:“清明时节,痛悼英烈。千言万语,欲诉又噎。哀向总理,泪水纵横。怒恨国贼,又刮黑风。正告你们,小小一撮。人民威力,休要看轻。遥祝英灵,可慰红心。前赴后继,马列必胜。”《清明呐喊》当然是愤怒的爆发:“前番悼念,又哄又压。九十余日,百人遭抓。今朝扫墓,变本厉加。言称“破旧”,用心毒辣。《文汇》《参考》,舞爪张牙。人民愤怒,后台出马。颠倒黑白,诬人造假。遥桥无罪,总理有瑕?桩桩件件,有目共察。追根寻源,辽海两家。篡权野心,一如林家。若其得逞,必拥苏家。人民眼亮,尔辈眼瞎。民不畏死,何以惧怕。犹谢去者,唤起民心。革命新史,由此填发。呐喊呐喊,喊哪喊哪。浩荡洪流,冲毁厮家。”当然,真正的愤怒会转变为新的革命、新的战斗,“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扬眉剑出鞘》组诗就是吹响了战斗的号角。
愤怒转变为行动,这是压抑之后的爆发,当然在诗歌情绪的表达中,也大都是革命式的口号,也都是对战斗二元化的直接表达:他们是敌人,他们是妖魔,他们恶怪,所以唯一的办法便是用人民的力量,《擒妖甘献我头》《擒妖捉怪保红旗》《今日举剑斩魔妖》《神州清明大反击》,这些诗歌的题目就是一种愤怒的态度,就是一种革命的行动。敌我如此分明,战斗的目标也是十分明确和固定的,“我们要民主,不要法西斯;我们要繁荣富强,不要吹牛皮,我们要实事求是,不要野心家;我们要周总理,不要佛朗哥,更不要那拉氏。”《要和不要》就明确了人民的选择,而最终的结果当然就是敌人“灭亡”人民胜利,“红心永向领袖,擒妖甘献我头!”
| 编号:S29·1970615·0376 |
哀悼的情感是真挚的,愤怒的情绪也是直接的,这是历史呈现的风格,但是当用44年后的目光走进那一段并未亲历的历史,时代的隔阂感并不在于对于具体吟咏对象的陌生,而是历史叙事本身存在着的一种时代封闭性,这种封闭性在“天安门事件”中所呈现的就是匿名化。那么多人涌向广场,那么多人寄托哀思,那么多人表达愤懑,但是在那个高压的政治环境中,看不清历史走向的现实面前,匿名性既是对现实的一种投射,也是政治性抒情的必然。一方面,当抒情的个体汇聚于广场这个场域,便成为宏大主题的一部分,诗歌中代言他们的便是“人民”,个体的情感变成了“人民”的一部分:总理是人民的总理,“人民、总理,朝夕相处;总理、人民,相爱相亲。”总理和人民站在一起,“人民的总疆人民爱,人民的总理爱人民。总理和人民同甘苦,人民和总理心连心。(《总理和人民》)”所以人民的力量保卫着总理,“修正主义害怕您,阶级敌人攻击您。革命人民想念您,我们誓死保卫您。(《齐颂总理爱人民》)”所以人民的力量要斩魔除妖,“世界历史人民创,人民双眼赛金睛。妖魔恶怪休得意, 自有举旗打鬼人!(《神州清明大反击)”
哀伤成诗人,愤怒出诗人,诗人就是人民,人民都是诗人,这是情感和抒情主体同一化、整体化的象征,一九七六年四月四日上午朗诵于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的诗歌《今日在何方》很好地阐述了人民诗人的意义,“看:人民的海洋里,/今天飞卷起诗歌的巨浪,/这无数巨浪齐奔向英雄碑下,/汇聚在我们的总理身旁!”在其中也有“我”,也有“我贴出”的几首诗,一首诗,一个我,和英雄碑下“象利剑! 象钢盾!”的无数诗篇相比,有一种自惭形秽的味道。但是另一方面,这些诗正是由一个个诗人、一首首诗作汇聚而成,个体是人民的一部分,所以这些诗让“古老的,诗国焕发了青春”,而“亿万人民呵,全都是诗王!”,人民写诗,靠的不是“天才”和“灵感”,“是挚情的浪花,/汇聚成这诗歌的海洋,/它寄托了人民对总理的无限哀思。”
诗人就是人民,人民成为诗王,诗歌的巨浪,就是澎湃在人民的海洋里,人民、诗浪和广场,共同构筑了事件的政治隐喻,这种匿名化其实表达的是一种去个体化的政治抒情。而另外一种匿名化,则是对当时政治形势的一种注解。天安门事件之后被定性为反革命事件,本身就取消了其合法化,所以出现了“藏头诗”,或者是:“悼词花圈献碑前,周围广场尽肃然。总想恩人功和绩,理应哀痛泪连绵。”或者是:“周末清明思总理,恩情温暖八亿民。来人定睁金猴眼,好识翻案捣鬼人。”或者是:“横眉冷对千夫指,扫尽人间变色虫。文章千古颂总理,汇集全国八亿兵。妖风起自浦江畔,风展红旗战妖风!”另一方面,所有的诗作张贴在天安门广场各个地方,几乎没有一首诗有具体的署名,一方面作者可以都是“人民”,人民就是唯一的作者;另一方面,毕竟表达感情还有一个个性化存在的可能,所以作者成为了一种匿名的存在。
他们是“诗歌工农兵学员”,“收下吧,/请收下!/十个热爱您的孩子/献给您这束朴素的鲜花。”他们是《誓和野心家、阴谋家血战到底》的作者“革命接班人”,“当鲜血洒在战旗上,才看出我们的忠诚,当炮火炸开我们的胸膛,才看出我们的心象火一样红。如果只有用我们的生命,才能换来革命的胜利,那就让我们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用刺刀沾着我们的鲜血,为祖国:为人民,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彻底胜利,为着共产主义的实现而血战到底!”他们自称“我们是劳动人民的儿子”:“敬爱的周总理,您慈父般的微笑永远珍藏在我们的记忆里!您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的民主作风将永远是我们的榜样!您为人民鞠躬尽瘁的一生,将永远是我们力量的源泉!您光辉的名字,将使我们坚强起来!勇敢起来!团结起来!”他们是“中国共产党普通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普通一兵”,他在《这是为什么》中表达革命的激情,“革命不怕压,怕压不革命。抛头颅,洒热血,誓死不屈,谁反对周总理,就和他血战到底!”他们是为《文汇报》开出诊断书的“赤脚医生”,是“擒来妖怪庆胜利”的“钟馗帐前一小卒”……工农兵学员、革命接班人、劳动人民的儿子、普通一兵以及赤脚医生、钟馗自小卒,匿名化的背后其实也是一种命名,他们不是有名有姓的个体,却是人民海洋中具有自身力量的浪花。
作者的匿名化,可以视作人民化的一种表达,而对敌人的“匿名化”则成为了一种声讨,一种讽刺,有人自称“中共党员赵摇镜”,其实就是“照妖镜”:“反周必乱政,反周必反党。人民决不答应!!/反对周总理就是反革命!”署名继周、斩妖,就是表达双重的情感:“碑上总理显神灵,唤来无数驱妖人。”而在诗作中,利用谐音成为匿名化的一种手段,“揪出僵尸头,砸烂秀才殿”,这是《还我总理》中对“僵尸”的愤怒;“黄浦江上有座桥,/江桥腐朽已动摇。/江桥摇,/眼看要垮掉;/请指示,/是拆还是烧?”《向总理请示》中更是将两个人的姓名嵌入诗行,表达一种革命的信念;还有《斥“秃子”》中“来吧,/小心你头上那几根秃毛!”,“秃毛”是借代的修辞,更是一种讽刺。
作者的匿名化,敌人的匿名化,匿名化的作者是“人民”,匿名化的敌人则是“妖魔”,这就是人民和妖魔之间的斗争。而实际上,这场唯一的斗争形成的历史文本,即使那十年已经走向终结,这种深受政治影响的匿名化风格并未就此结束:1978年,汇集了515首旧体诗、40联挽联、59首新体诗、49篇散文的《天安门诗抄》出版,编者为“童怀周”,这是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汉语教研室16位老师的笔名,“童怀周”就是匿名化的命名:“同怀周”。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44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