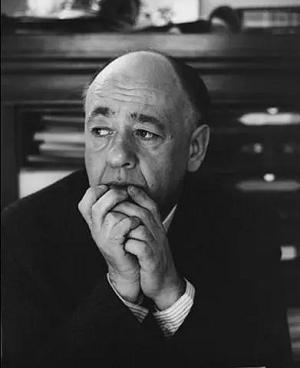2023-07-23《犀牛》:我有一只猫叫苏格拉底

贝朗热 确定性,确定性,我不知道的确定性。很确定的是这是一种确定性。
约瑟芬 好啦,既然这是一种不确定的、无限的确定性,那它就不是确定性。确定性是要以精确为其特点的。
——《空中行人》
确定性是精确,是秩序,是规则,甚至是知道确定性的能力,但是当“我不知道的确定性”构成了“很确定”的确定性,确定性是一种“不确定的、无限的确定性”,那么它就是不确定性——等式成立:确定性成为不确定性,于是悖论就这样建立了:精确自己解构了精确,秩序自己解构了秩序,规则也自己解构了规则,而当精确、秩序和规则在自行解构中变成了现实,那么现实就是一种可能性,就是荒诞,就是戏剧,就是欧仁·尤内斯库的荒诞戏剧。
《空中行人》就指向了这种能力带来的悖论,贝朗热说已经不能飞行了,不能飞行是忘记了飞行,忘记了走路,忘记了站立,忘记了坐着,一切的忘记就是丧失了所有的能力,而其原因就在于“身在祸中不知祸”,而这也是痛苦的根源——这就是人活着的“无能为力”状态,但是就痛苦本身而言,人又必须创造自己的能力,当大家都说“没法再重学飞行”,一句“太晚了”就注解了这种无能为力,但是贝朗热却说:“永远不会太晚。而且,凭记忆就足够了。”由记忆取代能力,不确定性能变成和精确、秩序和规则有关的确定性?如何证明?如何演绎?一出戏剧从两位英国老太太漫步开始:第一个英国老太太对女孩母亲说,“你们的小女儿很有教养。”第一个英国男人对第二个英国男人也说:“先生,你们的小女儿很有教养。”第二个英国男人的回答是:“你们的小男孩也一样,肯定。”“肯定”就是一种不容置疑的确定性,但是这种确定性只是一种推测,当小男孩扯下小女孩的发辫露出秃头,第二个英国女人说,小女儿就是小秃头歌女,扯下头发变成小秃头歌女再不是一种有教养的表现,它似乎就回到了尤内斯库“秃头歌女”的荒诞故事里。
殡仪馆的职工正在为约瑟夫父亲的死亡安排葬礼,他们还在报纸上发了讣告,但是约瑟芬却取消了葬礼,取消葬礼当然是取消了确定性;殡仪馆职工要将他们送上法庭,要走法律程序,法律也意味着一种秩序;但是当约瑟芬在法庭上的,她反问:“我被指控什么啦?我什么都没干”,女儿玛尔塔安慰她说,这是幻觉,这是噩梦,这不是真的,“你想是真的才是真的。你愿意是真的才是真的。别信它。”幻觉和梦境制造了真实,但是真实只是一种情愿,当然也不会建立永恒的规则;陪审员由那个巨型木偶约翰·布尔的演员扮演,他在法庭上说的是:“真正正义的道理,既不是良心的,也不是逻辑的。如果正义在您看来是不正义的,那是因为它是公正的。”正义被看成是不正义才是“公正”的,这又是一个悖论式的存在……
当然,种种的解构,种种的悖论,尤内斯库的设置就是为了让一种能力驾驭另一种无能为力,从而建立不确定性的确定性。约瑟芬的父亲死了,玛尔塔却唤醒了自己的父亲,这是父亲对“父亲”的某种替代,“我们现在有爸爸了。”一个丧身于飞行中,一个重新用“记忆”飞行,贝朗热说:“当我们梦见我们死去的亲属时,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多么惦记他们,我们多么惦记他们。”这是能力的替代和体现,按照记者的说法,贝朗热就是行动型的人,“他要世界服从于他。”这是一种用能力和行动战胜现实的方式,而现实如何呈现为一种不确定性?贝朗热说“我们大家都失去了我们的能力”,而专门追逐热点甚至制造谎言的记者说:“技术大大增加了这些能力。”贝朗热看到了“反世界”的人经过,他指出了“反世界”的本质,“无法证明它的存在,但可以想象,人们可以在自己的思想里找到它。”反世界,反脑袋、反四肢、反衣裳、反情感、反心脏,按照百姓的信仰,人死后要去“反世界”,而那个反世界的人出现是不是死亡的降临?反世界是一种死亡,面对反世界人们构建了虚无,“这是工作中的一种宇宙假说”,是虚无也是存在,“你看,这些为废墟所证明了的死去的宫殿统统都在下面,当然,也许,也许——希望就在那儿——穿过虚无之后,一切都将在那边重建、修复;当然,是反面,既然是在另一边。”
技术增加的能力取代了人自己的能力;反世界是一种死亡,用虚构构建了宇宙……所以这是一个没有能力、没有秩序、没有规则的世界,所以贝朗热要用记忆来恢复能力,用能力去除虚无:向空中跳,胳膊举高,挂在想象的树枝上,“从一根假设的树枝到另一根假设的树枝地爬。”用想象高跳,欲望决定想象,所以,“如果你愿意,这是无限的。如果你能,你可以永不停止。”贝朗热开始飞了,大家都看到他在飞,像飞机一样在飞,而飞行中看到了长着鹅头的人,看到没有头的断头台的柱子,看到干瘪的巨人、魔鬼、战败的大天使,看到了火光冲天、坟墓、刀子,“那里连接着空间和时间。”那是新的时空,新的宇宙,当然也是新的规则和秩序,在成千上万个世界消失之后,成千上万个人死亡之后,成千上万个星球爆炸之后……飞重新回来了,但又是新的开始,在这样一种新的规则和秩序中,世界就在每个人低头中看见城市,玛尔塔也在飞行,“也许除了爆竹声什么也没有……也许事情会好起来……也许火焰会熄灭……也许冰雪会融化……也许深渊会填埋……也许……花园……花园……”
这是尤内斯库对于能力的重建?是对于确定性被解构之后的再生?玛尔塔的“也许”依旧是一种推测,一种想象。如果说尤内斯库在《空中飞行》中用想象的欲望重构能力,这是对虚无的批判。电影脚本《怒气》和《空中飞行》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只不过它制造的是虚无之后的毁灭,所有人都沉浸在周日的喜悦当中,一碗汤里却发现了一只苍蝇,于是争吵开始,斗殴加剧,“怒气”成为人类的普遍情感,它宛如蝴蝶效应一般在人类世界蔓延,最后的景象便是“地球爆炸”——电影剧本后来变成了西尔万·多姆导演的《愤怒》,收录在《七宗罪》这部集锦片中,其中还有戈达尔的一部短片。一部舞剧的构思《学走路》最后变成了由德里克·孟代尔编舞和导演的《在路上》,这部舞剧也指向了荒诞的结局:男人被轮椅推进了病房,他是一个瘫痪者,于是女护士开始为他做康复动作,渐渐的,康复动作变成了舞蹈,男人学着她做出动作,慢慢的,他学会了舞蹈,之后成为了舞蹈奇才,当女护士也是女舞蹈家深处双臂,男人竟然独自旋转,在舞蹈中往上攀登,他最终消失在“可以看到的最后一级楼梯的高处”。
| 编号:X38·2230520·1963 |
从瘫痪的病人到舞蹈奇才,这是能力的重新构建?这种能力是欲望还是想象?当男人终于在独自旋转中从高处消失,能力制造了死亡?艺术也许在虚无中变成了另类艺术,而这另类艺术在高处的消失中似乎又让他变成了瘫痪者……重建变成了一种循环。如果《在路上》是艺术虚无的一种表现,电影脚本《煮鸡蛋》则是对所谓知识的一次解构:这是一个鸡蛋,一个呈现椭圆形的鸡蛋——椭圆形可以通过黑板上的几何法绘制出来;要煮鸡蛋,先要去乳品点买鸡蛋,乳品商给了她完好无损的鸡蛋,拿着鸡蛋过马路,警察叫停了所有车辆,只为不让完好无损的鸡蛋被撞破,结果导致了路上的汽车相撞,警察也被撞到,而被碰撞的汽车里掉下了一大筐鸡蛋,当然鸡蛋也没有碎;回到家里,年轻女子开始煮鸡蛋,锅子里要放水,锅子要放在炉子上,炉子要点火,当然开始煮鸡蛋要等候几分钟,然后将鸡蛋捞上来,用勺子可以避免烫伤手指,接着就可以剥掉蛋壳吃鸡蛋了;在一系列煮鸡蛋的知识普及之后,是关于鸡蛋的健康知识:如果吃下蛋壳会得阑尾炎,画面上的胖先生就因此被送上了手术台,女人吞下了鸡蛋打了一个嗝,脸开始红了神色还很尴尬,鸡蛋也会变质,在下蛋之前就可能被污染,“鸡蛋可能含有细菌:白色葡萄球菌、巴氏杆菌、大肠杆菌、绿脓杆菌、枯草芽孢杆菌、普通变形杆菌、萤光杆菌、灵杆菌。”
当然,尤内斯库“献给让·福兰 伟大诗人与美食家”的另一个剧本《准备煮鸡蛋》将《煮鸡蛋》的电影剧本变成了一种表演,也还是从乳品店买了完好无损的鸡蛋,还是用完整的过程煮鸡蛋,还是提到了鸡蛋的健康问题,“鸡蛋是营养丰富的健康食品。然而在某些情况下不能食用或不宜食用。请依照医嘱。”最后的“请依照医嘱”让买鸡蛋、煮鸡蛋、吃鸡蛋这样的日常行为变成了一种可能性,这是和知识有关的可能性,“不能食用或不宜食用”,与《在路上》的舞蹈一样,艺术也有成为舞蹈奇才或瘫痪者的可能性,可能性无疑是对确定性的解构,它在不确定性中成为了一种虚无,也许在想象中,在艺术构思中,在荒诞戏剧中,它会演绎可能性。
但是可能性的背后是不是也还是一种确定性?技术增加了能力这是确定性,没有葬礼、没有教养也是确定性,世界在反世界中更加虚无也是无可逃避的确定性,当然,《二人妄想症》看起来是他和她的一场臆想,一种虚构,但是它背后也是可能性中的确定性,它以必然的方式成为命运不可逃避的现实。她十七年前离开丈夫和情夫私奔,他后来成为了她的丈夫,但是生活没有得到改善,于是她骂他是个诱惑者,“蜗牛和乌龟,就是同一种动物。”同一种动物就是意指生活根本没有改变,而他却否定了,“不对,不是同一种动物。”或者说,“咱们原本就不是同类。”两个人争吵,就像乌龟和蜗牛,但是否认是同类就是在证明自己的价值:对于诱惑者的指责,他辩解说:“我不是个平庸的男人,我不是白痴。不像你所认识的那些白痴。”争吵是一场战争,而外面正响起爆炸声,还有子弹呼啸的声音,房子坍塌的声音,人群混乱的声音,甚至还有人死了。里面的争吵和外面的爆炸,构成了“同一种动物”的现实,这是无法避免的困境,而两个人在寻找可能,“ 跟你说,我并没有考虑出去的可能性,而是说,只有在这种可能性有可能的情况下,我才会做这种打算。”他这样说,而她却认为自己比他更有逻辑,“我这一生证明了这一点。”
出去的可能性其实根本没有,在确定性的命运中,一个人偶掉了下来,它是无头的躯体,也是无身子的头,但是可能性依然没有意义,因为这便是确定的惩罚,这便是死亡带来的和平,“他们在上面搭起了断头台。你该明白这就是和平。”无躯体的头就是无头的身子,可能性的逃离就是确定性的惩罚,死亡就是和平,还有什么区别?于是他骂她是“乌龟”,她骂他则是“鼻涕虫”,没有分别的动物互扇着耳光,“没有过渡便重又干起活来。”《二人妄想症》也是多人妄想症,私奔是妄想,不是懦弱是妄想,外面的战争是妄想,死亡是妄想,最后一切都变成了生活的妄想,而生活变成命运就是取消了妄想,因为乌龟和蜗牛、鼻涕虫就是“同一种动物”,确定性的命题,没有可能,没有意外。
|
| 尤内斯库:我是一个人。一个人类之人。 |
而乌龟和蜗牛、鼻涕虫和“犀牛”也是同一种动物吗?“某种既强壮又沉重的动物十分快速的疾驰声,近在咫尺;听得见它的喘息声”,这就是犀牛,当它突然出现在城市里,突然奔跑在街道上,突然制造了人群的恐慌,它一定是和人类不一样的动物。尤内斯库安排《犀牛》发生在外省小城的一座广场上,杂货店、教堂钟楼、咖啡馆都构成了人日常的、有秩序的生活,但这也是一种表象,当犀牛出现之前,贝朗热和让的谈话其实指向了这个城市、这个时代以及这个现实的问题。让穿着十分考究,而贝朗热则不修边幅,他昏昏欲睡,认为自己状态很糟,让说他可能患了肝硬化,他知道贝朗热很喜欢喝酒,而贝朗热喝酒是因为他讨厌这个城市,“日复一日,整天待在办公室里,每天八小时,只有三个星期的暑假!星期六晚上,我更多的是累,所以呢,您可以理解,为了放松……”
此时一头犀牛出现了,众人看见都发出了“这下子”的惊叹,犀牛的出现意味着世界发生改变,害怕当然也是对世界改变的态度,它和贝朗热的讨厌构成了现实的困境。而尤内库斯在这里安排了对全剧具有关键意义的人物:逻辑学家,他和老先生的对话、贝朗热和让的对话构成了舞台上的一种复调结构:贝朗热感觉城市里出现犀牛闻所未闻,“好哇………好哇……是不该允许这种事情发生的。”这是对可能性的一种阐述,所以他分析犀牛也许是从动物园里逃出来的,让告诉他,这个城市自从那场鼠疫之后再没有动物园了;贝朗热还推测可能来自马戏团,让也告诉他根本没有看到过有马戏团;贝朗热于是将这一切看做是一场梦,可能性就是梦中的事。在贝朗热不断向让阐述犀牛的可能性,穿插在他们对话中的则是逻辑学家和老先生的对话,他们的对话就是沿着逻辑构建的确定性。
“害怕是非理性的。理性应该战而胜之。”理性就是按照逻辑构建的确定性,不害怕的逻辑学家说刚才是一头犀牛,“速度飞快,就在对面的人行道上!”接着他说到了三段论,还举了例子,“猫有四条腿。伊兹道尔和费利科各有四条腿,因此,伊兹道尔和费利科是猫。”老先生说:“我家的狗也有四条腿啊。”逻辑学家于是说:“那它就是一只猫。”逻辑和理性构筑了确定性的事实,但是确定性制造了矛盾和错误,因为狗就是猫;再次讲到三段论的逻辑时,逻辑学家说:“所有的猫都会死。苏格拉底会死。所以,苏格拉底是一只猫。”老先生活学活用,“而且它有四条腿。确实,我有一只猫叫苏格拉底。”苏格拉底是一只猫,从三段论推断出的是一个荒诞的笑话,它取消了逻辑,取消了理性,或者说,所谓的理性和逻辑导致了非理性和非逻辑的出现,而这就是荒诞;另外,老先生家的一只猫叫苏格拉底,这不是逻辑也不是理性,这是生活本身,一种和命名有关的生活。
贝朗热对让说着可能性,逻辑学家在证明理性,他们同时发生,不断穿插,而这也成为尤内斯库的两种态度。接着,又传来犀牛奔跑过街道的声音,反方向,甚至它踩死了女佣的一只猫,但它不是苏格拉底,也不是叫苏格拉底的猫,它就是一只猫。犀牛一定是确定发生的存在,让也说到了确定性,“ 不对,不是同一头犀牛。刚才的那头鼻子上长着两只角,它是一头亚洲犀牛;而这一头只有一只角,它是一头非洲犀牛!”但是它在贝朗热那里依然是可能性:“您怎么能够辨认得出犀牛的角来!那野兽经过时速度之快,连看清它都不容易……”老先生也加入其中提出了疑问:“您怎么知道两种犀牛当中一种长着两只角,而另一种长着一只角呢?又是哪一种?”老板也开始讨论:“就当有过两种犀牛吧。哪一种长着一只角的呢,亚洲犀牛吗?”这里的一个关键点是,逻辑学家也变成了可能性的论者:“事实上,可能就从刚才开始犀牛就已经掉了一只角,而紧接着的那一头就是刚才的那一头。”也有可能,“两头长着两只角的犀牛各自都掉了一只角。”
在反逻辑的逻辑面前,在非理性的理性面前,可能性反而变成了生活本身,而这种可能性却以确定性的荒诞方式发生着,在办公室里,戴琪说自己亲眼看见了犀牛,杜达尔也将关于犀牛的报纸拿了出来,但是波塔尔却认为,这只是一个骗局,“作为一名小学老教师,我喜欢精确的事物,为科学所证明的事物,我的思维有条有理,准确可靠。”不相信确定性的事实,是要让自己重建确定性,这就变成了反逻辑的逻辑,非理性的理性,“你们的犀牛是一个神话!”他认为这是一次集体的癔症,就像宗教成为精神鸦片一样。但是荒诞的现实却打了波塔尔耳光,那天波夫没来上班,后来波夫太太来了,她告诉大家一个不幸的消息:波夫已经变成了一头犀牛,而且就在楼下,波夫太太于是从楼上跳到了丈夫的背上,看到这一幕,讲究精确性的波塔尔又改了自己的说法,“我不是简单地观察这种现象。我要理解它,还要解释它。至少,我要能够解释它,如果……”
有些东西也许的确发生了,而且根本不可解释,它是非理性的,它是反逻辑的,它就是意外,就是荒诞,就是无限的确定性变成的不确定性:贝朗热去看望让,他发现让的皮肤变绿头部的肿块变硬,这个认为自然超越了道德的人,这个信奉丛林法则的人变成了犀牛——失去了理智的犀牛反而成为了比人更高级的动物;“必须紧跟时代”的波塔尔变成了犀牛,戴着圆顶草帽的逻辑学家变成了犀牛,救人的消防队员变成了犀牛……这是逻辑彻底消失的标志,尽管它是一种反逻辑的逻辑,与此相随的,是心智,是意见,是看法,是精神,是科学思维,当然,还有爱情。戴琪找到贝朗热,面对越来越多的人变成犀牛,她想和贝朗热在一起,“我的爱情,我的欢乐!我的欢乐,我的爱情……把你的嘴唇给我凑过来吧,我还以为自己不会再有这样的激情了!”但是在这个世界病了的现实中,戴琪最终也离他而去,因为,“共同生活已经不再可能了。”
没有了逻辑,也没有了反逻辑的逻辑,没有了理性,也没有了非理性的理性,没有了确定性,也没有了不确定性的确定性,“我有一只猫叫苏格拉底”就是苏格拉底是一种猫,这个世界产生的命题是:所有人都是犀牛,按照三段论,所以人是非理性的。最后剩下的贝朗热却在可能性中建立了一种理性:“我不会追随你们,我理解不了你们!我要保持我自己。我是一个人。一个人类之人。”一个人,是一个理性的人,是一个战斗的人,但是在人人变成犀牛的时代,贝朗热的理性和战斗也成为了“怪物”,“面对全世界,我要自我防卫,面对全世界,我要自我防卫!我是最后的一个人,我要做人做到底!我不投降!”也许,“做人做到底”的逻辑最后也会成为反逻辑,也许,“我不投降”的理性也会成为非理性,最后一头犀牛叫贝朗热,最后一头犀牛就是贝朗热。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69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