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09-17《文化与帝国主义》:没有一个人是单纯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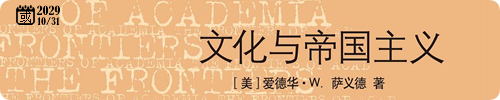
我想说明的最后一点是,这本书是一本流亡者的书。由于我不能控制的原因,我成长为一个受西式教育的阿拉伯人。
——《前言》
“流亡者”的界定,对于爱德华·W.萨义德来说,似乎有两层含义,一是本书的议题是关于文化的“流亡”状态,帝国主义带来的殖民,殖民带来文化的扩张和迁徙,虽然文化在萨义德的眼中是一个“使人美好、高尚的东西”,是“每个社会中被认为是最优秀的因素”,但是在帝国主义的争夺中,文化不再是一个文雅平静的领地,“它甚至成为一个战场”,各种力量的相互角逐制造了“流亡者”;第二,流亡者则是对作者的一种角色定位,或者说它就是萨义德对自我身份的界定,在他所说的“不能控制的原因”下,成长为一个受西式教育的阿拉伯人——西式教育和阿拉伯人可以看做是“文化与帝国主义”的具体写照,但是在这本最后要阐述在文化融合中形成新的权威的书里,萨义德所说的“不能控制的原因”到底是什么?为什么还要强调自己特殊的身份?
在《前言》中,萨义德开宗明义指出,写这本书是为了扩充《东方学》的观点,即“对现代西方宗主国与它在海外的领地的关系做出更具普遍性的描述”,他选择了两个论述视角:世界范围的帝国主义文化;历史上对帝国主义的反抗——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说,它并不仅仅是《东方学》的一次扩充。从“文化与帝国主义”的视角来论述宗主国与海外领地的关系,当然不是将它们割裂开来,即使其中有帝国主义的征服和扩张带来文化上的渗透,有殖民地国家对帝国主义的反抗带来的独立,但是在萨义德看来,文化和帝国主义形成了一个相互影响的统一体,文化既不是某种输出型的文化,帝国主义文化也不是单一的、分割的文化,在这本关于过去和现在、关于“我们”和“他们”的书里,萨义德所强调的是,文化与帝国主义都进入到了一个新阶段,这个阶段的标志就是:“跨越国界、跨越国家类型、民族和本质的新的组合正在形成”,而这个组合所挑战的就是帝国主义时代文化思想的核心——身份认同。
萨义德一方面把身份认同看做是过去“文化与帝国主义”的一种极端僵化的概念,把超越国界和民族的文化看成是新组合,他当然是对这种新组合持肯定并且欢迎的态度,但是另一方面却极力强调自我的身份,甚至将之归于“不能控制的原因”,从而将自己变成了一个“流亡者”。萨义德在《前言》中给出的观点看起来充满了自我矛盾,而如果撇开在客观上“不能控制的原因”造成文化上的流浪,在现实意义上,萨义德关于“文化与帝国主义”的理想化能否实现?这个理想能否实现关键就在于对文化的定位,萨义德认为文化具有双重意义,首先它是一种描述、交流和表达的艺术活动,它相对于经济、社会和政治而存在,它通常是以美学的形式表现出来,交织着人种学、历史编撰学、哲学、社会学和文学史等学科知识,在这个维度上,小说是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萨义德在本书中引用的例子就是小说,在他看来,小说和帝国主义的扩张之间是“一个有趣的美学课题”,所以在第一层含以上,文化是萨义德在叙述上的一种内容支撑,它具有两个意义:一是“故事是殖民探险者和小说家讲述遥远国度的核心内容”;二是“它也成为殖民地人民用来确认自己的身份和自己历史存在的方式”——在这里萨义德强调了“故事”带来的身份认同。其次文化是一种使人美好和高尚的东西,在帝国主义时代,文化就呈现为一种“相互角逐”的状态,像一个战场一样,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甚至相互取代。
文化在小说叙事中体现其内容的参照价值,在这里萨义德尤其强调了殖民探险者的“讲述”和殖民地人民的“身份认同”,很明显萨义德的“文化”在这里就具有了殖民主义的色彩,而殖民主义就体现了文化的内在差异性。在第一章《重叠的领土,交织的历史》中,萨义德就强调了这种差异性的表现,他当然在一开始就阐述了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差异,在他看来,帝国主义指的是“统治遥远土地的宗主中心的实践、理论和态度”,而殖民主义是伴随帝国主义而出现的,它“意味着向边远土地上移民”。殖民主义是伴随帝国主义而出现的,但是萨义德强调殖民主义只是一种移民行为,而帝国主义在具体的政治、意识形态、经济和社会活动中存在,当然也在文化领域中存在,所以和文化发生关系的是帝国主义而绝非是单纯的殖民主义,这个对概念的厘清实际上体现了萨义德对殖民主义的某种回避,帝国主义的存在必然导致殖民主义,殖民主义也是帝国主义的一部分,文化当然也体现在殖民主义中,它构成的是“殖民文化”——帝国主义对海外领地即殖民地的文化输出和渗透就是一种殖民文化,萨义德之所以回避,就在于从帝国主义这个复杂、多元的概念中考察复合的、混合的、不纯的文化,从而为他建立新的组合、新的融合创造条件。
但是,正因为萨义德将殖民主义简单化,所以在“文化与帝国主义”的阐述中,缺少了对海外领地土生土长“本土主义”文化的审视,当一切以“帝国主义”为中心看待文化的超越性和融合性,视角本身就是一种帝国主义中心说,即使其中有很大一部分论述海外领地对帝国主义的抵抗和敌对,也是从帝国主义中心说出发的一种观点,也就是说“抵抗和敌对”是对帝国主义殖民的一种回应,它的出发点依旧是帝国主义而不是海外领地的“本土主义”。在区分了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概念之后,萨义德几乎将全部的论述都放在了帝国主义中心说之下的文化差异和文化融合的可能性。首先他提出了文化和帝国主义两者之间的关系,“文化与帝国主义都不是静止不动的。因此,它们之间的历史联系是能动的、复杂的。”这是萨义德最基本的立足点;其次,如果帝国主义是一种相对稳定的概念,那么文化就有着更多的变化,更多的混杂性,文化不是自成一体的,它含有的“外来”成分、“异物”和差别比它们有意识排斥得要多,这种“外来”的、“异物”的东西往往是不容易发现的,它以不易察觉的方式发生着,而且对于第三世界来说,帝国主义给他们带来了奴役和痛苦,带来了屈辱,但是也带来了自由的思想、民族的自觉意识和高技术的商品,在这个意义上,尽管两个世界呈现了一种对立的危机,但是文化却在更激烈的交错中“相互影响”。
萨义德承认不同世界、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之间存在着文化差异和经验差异,但是这种差异不能单一被极权理论所囊括,不能以教条来划分,不能以民族来画线和限定,也不能绕过意识形态,萨义德强调差异其实为可能得跨越创造条件,或者说,差异也意味着“同时并存”,而这种并存就需要在人类总体上进行把握,所以萨义德说:“我们的讨论必须包括互相重叠的土地、男人与女人、白人与非白人、宗主国与边缘地带的居民所共有的历史、现在和将来。这些土地与历史只能从整个人类世俗历史的角度来看待。”将帝国主义和世俗观念联系起来,将文化置于人类的整体来看待,萨义德便从文化的具体表现之小说入手,探讨了“融合的观念”的可能性发展。
| 编号:B86·2230620·1974 |
“帝国主义”之所以成为萨义德论述的一个中心词,他对于“融合”的观念也是从帝国主义这个中心出发的:贯穿于奥斯汀的小说《曼斯菲尔德庄园》的是托马斯·伯特兰爵士字啊海外的领地,这些领地给他带来了财富,他的远行就界定了他在国内外的社会地位,这种地位构成了他的价值观。曼斯菲尔德庄园是一个横跨两个半球、两个大海和四块大陆之间的中心点,所以在19世纪的时候,帝国成为了一种参照系,它拥有的是一个合适的旅行、聚财和服务的背景,萨义德认为奥斯汀的小说就是表现了一种“可获得的生活质量”,它是文学杰作,不仅在文学本身上是一部经典,更在帝国主义文化的开拓上具有标志意义,“没有这种文化,英国后来就不可能获得它的殖民领地。”在这里,萨义德提出了“帝国的文化完整性”这一命题,他认为,文化与帝国主义的结合要完成一次命名,就需要体现其完整性,它主要表现在:西方和世界其他地方之间的本质差别是不可否认的;人种论的出现,使得差别的区分变成了进化论学说,“从原始的到附属的种族,最后到优越的、即文明的种族的衍进。”另外,西方的统治并非是静止不动的,它的一个主要表现就是传播宗主国的文化;帝国主义的海外扩张,还具有“巨大的创造力量”。
在这个“帝国的文化完整性”中,萨义德所强调的就是从帝国主义为中心出发的文化差异、文化进化以及文化创造,在这里萨义德选择了几个不同的文化样本作为“感觉与参照的体系”论述这种“帝国完整性”:威尔第著名的“埃及”歌剧《阿依达》,它的特征是“开罗欧洲面孔的一部分”,威尔第使之变成一部分离的美学作品,它的意义是作为一种帝国主义式的奢侈品,共埃及的一小撮人享用,“证实东方从根本上来说是异域的、遥远的、古老的地方。在那里欧洲人可以显示一下力量。”萨义德对这部作品是批判的,他认为,《阿依达》具有的象征意义就是一种欧洲的力量,“这些领土上的居民似乎注定永远无法逃脱,永远成为欧洲人的意志的产物。”这是“帝国的行动”取得的单一效果,它当然构不成“帝国的文化完整性”,而吉卜林的小说《吉姆》则提供了另外一种参照,吉卜林身为小说的作者也是“文化与帝国主义”身份认同最著名的一个例子,出生在印度对西方怀有一种母体思想,吉卜林本身就是一种历史的产物,而小说也并非是“混乱的、极端反动的帝国主义的种族主义想像力的产物”,在萨义德看来,吉卜林所创造的是“一个英国控制印度的手段”,吉姆所需要的是对他创伤的医治,“这种描写手法如果没有帝国主义的存在显然是不可能的。”所以吉卜林以及《吉姆》都是对“帝国的文化完整性”这一历史时刻的“伟大记录”。同样还有出生于阿尔及利亚的加缪,萨义德认为,加缪对于抵抗和生存冲突的论述是“文化与帝国主义争论的一部分”,这种争论一方面是加缪的小说作为“经过几代人精心打造的阿尔及利亚的政治地理的一部分”,是对于法国殖民地再现、占有和拥有政治解释权的有力说明,另一方面小说渗透着一种无能为力的殖民主义——但是不管争议如何,萨义德认为,小说中构建的话语体系是以法国帝国主义的立场和地理为参照物的,“我们必须把加缪的著作看作把殖民主义困境做了对应宗主国的美化:它们代表了法国殖民主义作品。它们是为法国读者而写的。”
《阿依达》体现着欧洲的意志,《吉姆》是对帝国历史时刻的伟大记录,加缪的小说是为法国读者而写的,萨义德解读“帝国的文化完整性”,站在西方与非西方、宗主国和海外领土、帝国文化和殖民地出生等看似对立维度上,其中心就是“文化与帝国主义”的西方视角,所强调的也是僵化的身份认同。而在“抵抗与敌对”中,萨义德面向了帝国主义和第三世界共同审视的“抵抗文化”,但是这种抵抗是对本土主义的一种捍卫?萨义德很明确指出,研究西方和“异类”的文化之间的关系,除了不平等对话之外,更是“研究西方文化实践本身的切入点”,也就是他的立足点还是在西方文化,还是体现了帝国主义的殖民文化:抵抗行为的发生,抵抗文化的形成,带着第三世界作家的历史印记,它们是屈辱留下的伤疤,是不同习俗的动因,是可能的对过去的改变,具有的悲剧性意义是,它还需要适应后殖民文化,需要重新解释重新体验的经验,“它必须在某种程度上恢复帝国文化已经确立的,或者至少影响过或渗透过的形式。”
当然,在抵抗文化中也出现了对帝国主义的完全反动,它形成了民族主义——对此,萨义德尽管称自己不是站在简单的“反民族主义立场”,但是他当然是反对分离的民族主义,文化对“国家主义”的贡献时常是分裂主义、沙文主义和集权主义,但是在他看来,民族主义应该“赞同各种文化、人民和社会间更阔大、更宽容的人类社会现实”,在这个意义上,抵抗文化走向的不是对立,不是分隔,而是走向超越民族主义的共融,所以抵抗的终极目标是解放,“反对与抵抗的文化在最大程度上,能够提出按照非帝国主义的条件重新构想人类经验在理论上的不同方式与实践的建议。”独立只是第一阶段的目标,而解放才是最终的主题,一方面对于非西方世界来说,“真正的民族主义反帝运动永远具备自我批评精神。”另一方面对于帝国主义来说,对于抵抗之后的解放,也需要用一种“勇敢和博大精神”来认识。
不管是从帝国主义的角度看来“文化的完整性”,还是从抵抗的维度来认识非西方世界的解放意义,萨义德的立足点只有一个:帝国主义,他的出发点也只有一个,那就是“文化与帝国主义”的现代出路。在解读英国、法国相关文学叙事作品背后的帝国主义之后,萨义德提出了美国问题,“本书写作的时代,可以说是冷战后美国作为最后的一个超级大国而崛起的时代。”美国问题似乎让“文化与帝国主义”变得更为复杂,一方面在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之后,美国成为了唯一一个超级大国,世界的格局发生 了改变,而美国的“帝国主义”更表现在将自己的法律和和平观念强加于世界,文化更是成为帝国主义霸权的一个特点——由于“不能控制的原因”,萨义德成为了美国公民,这是不是帝国主义文化输出和认同的一个结果?萨义德也强调自己是一个阿拉伯人,一方面他认为,“阿拉伯民族是十分重要的,它是被侵害的、未实观的民族主义,为阴谋与国内外敌人所困扰。”另一方面他强调在中东找不到真正的民主,“那里有的是享有特权的寡头政治家们或者享有特权的民族群体。广大人民被独裁制度或从不让步、无反应、不受欢迎的政府所压垮。”
是选择帝国主义还是选择独裁的民族主义?萨义德的选择对于身份认同依然是第一位的,但是他又希望完全抛弃这种狭隘的观念,“我们必须扩展我们的视野,以诘问并回答关于怎样和如何读与写的问题。”借用艾利克·奥尔巴赫的一个观点,“我们哲学的家园是世界,不是某个民族甚至作家个人……”文化同样具有这样的意义,它是生产力、多样化的组成部分,它具有批判性和互相矛盾的能量,更重要的是,“它丰富的实践意义及其与帝国主义统治和解放运动的联系。”所以在这个萨义德定义为“巨大的不确定的新时代”,他提出了文化的“运动和流动”的观点,“从一种固定、稳定和内化了的文化转变成了一种没有限制、没有中心的和流放的力量。”这种力量的化身是移民,是流放中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是处在边缘的人,在文化的流动中,身份和标签最终将消失,“当今,没有一个人是单纯的。”
很明显,萨义德将“文化与帝国主义”的出发点放在帝国主义中心论中,却将“运动和流动”力量主体变成了第三世界的边缘存在,以此形成一种文化上新的组合,“没有人能否认悠久的传统、习惯、民族语言和文化地理的延续性。”但是帝国主义并没有消失,民族主义也可能走向极端,萨义德的理想主义还是在“不能控制的原因”的中面临质疑:在写作此书的时候,伊拉克入侵并吞并科威特所引发的危机正处在高峰,数十万美军部属在沙特阿拉伯,伊拉克又向阿拉伯世界求援,而联合国在这一问题上意见不一,最终美国占了上风战争爆发了。“当下”的问题还在继续,帝国主义还在实施“侵略”,小国的人民遭受战争的伤害,萨义德似乎还没有完成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文化在何处?跨越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融合在哪里?我们与他们的对立何时被消除?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60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