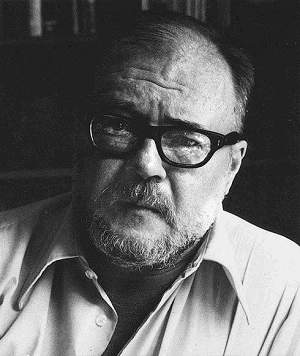2024-04-15《河流之上》:我已经死了这么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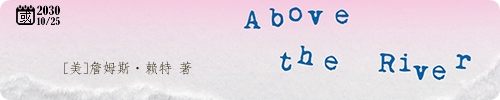
第383页,呈现为一种存在的有:有是一首诗的标题,是对于一匹马的纪念,是对于一首诗被吃掉的情绪,以及“戴维”作为马的名字,以及“吃掉”的动作,以及一种纪念的方式,都是有的显示。但是它以无的方式表现,这是一页纸的空白,是一首诗的缺失——是无的显现取消了有,还是有的存在命名了无?或者诗的标题就是对有中之无和无中之有的双重阐释:一首诗已经写成,但是被那匹名叫“戴维”的马吃掉了,所以即使吃掉了,诗也已经产生了,产生而存在,它是一种完成,即使不再又被看见的文字,它也无法被取消而成为无。
一首诗,在詹姆斯·赖特的这本诗集中成为最特殊的存在,仅仅以一个标题留存了被吃掉的诗歌本身,赖特似乎在进行着一种书写的实验,而这种实验在文本之内和文本之外构成了赖特的诗学观。言说而成为空白的言说,就是言说的一种方式,那么,这首诗是不是也意味着是赖特自己将它从诗集中抽身而去?他也变成了那匹名叫戴维的马,在自己书写和自我吞噬中完成了诗作,但是这种实验性的“吃掉”作为抽离而存在、作为缺失而拥有,为什么不是赖特更广泛意义上的书写?一部汇集了莱特毕生精力的诗作,一部收录了赖特诗歌、散文诗、抑扬格诗作在内的著作,一部厚度达到了816页的文本,,一首诗的抽离只是一页纸的空白,如果所有的作品只留存着标题,是不是它也会构成一部“诗全集”?
后一种的假设没有成为事实,所以缺失而存在只是赖特的一次有限实验,当抽离而存在、缺失而拥有、空白而言说,它似乎也成为了赖特在《河流之上》的一种探索——绝非是文本意义的实验,它是关于诗歌本身的一种精神命名。《纪念一匹名叫戴维的马,他吃掉了我的一首诗》收录在由诗集《诗集》选录的《新诗》之中,“新诗”一方面是对相对于格律诗在形式上体现为新的“新诗”,另一方面也是赖特想要突破某种约束进行探索的新。而那首放置在《新诗》诗集题辞上的《善的理型》就是赖特关于“新诗”的一种阐述。曾经是带着“一身刻骨的孤独”,曾经是“在黑色的岩石上行走”,而现在“再次踏上/旅途”,虽然还是“自己的旅途”,还是孤孤单单,还是看到了黑色的岩石,甚至还是知道在岩石关闭之后“我死去”,但是赖特在这一种重复的死亡中有所希冀,那就是希望“有只猫头鹰端坐在坟头”,希望“有双瘦骨嶙峋的脚/冷冷逼近碑石”,死亡抵达之后的希望,是向着新诗之“新生”开始的,那就是献给赖特诗歌中总是出现的抒情对象“珍妮”说的话:“珍妮,我给了你那本让人不快的/书,除了你我无人能懂的/那本书,所以,还给我/一息生命吧。”
诗人曾经给珍妮的书,是一本让人不快的书,是一本别人无法读懂的书,“让人不快”指向“新诗”之前,“无法读懂”指向他者,而向珍妮要回这本书,就是为了从让人不快和无人能懂中赋予新的言说方式,它是“一息生命”的象征,也只有诗人和“珍妮”能够将其激活,“我的宝贝秘密,他们/怎么会懂得/你和我?/忍耐。”取名《善的理型》,赖特就是要从理念之诗走向新生之诗,就是要从“无法读懂”走向对“宝贝秘密”的再次阅读——此为赖特的“新诗”,而《纪念一匹名叫戴维的马,他吃掉了我的一首诗》的实验就是要在抽离而存在、缺失而拥有、空白而言说中构建一种向死而生的诗歌人生。像是一个悖论,但是赖特明显在自己设置的矛盾和对立中寻找突破之法,即使痛苦万分,即使走向死亡,即使内心经历挣扎,或许也是走向“新诗”的必然。
这样抽离而存在、缺失而拥有、空白而言说的悖论是什么?是抽离和存有,是梦境和醒来,是怀疑和坚守,是孤独和富有,是肉身和精神,而出现在赖特诗歌中最常有的一对矛盾统一体便是死亡和复活——复活必然是死亡之后的复活,那么,在赖特的诗歌中,死亡又是什么?收录在诗集《两位公民》中的诗歌《她毫无睡意》似乎可以视作是对赖特死亡意向的一次解读,“求你了,快醒来吧,我到底会怎样死去?”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很简单。/我只需要删掉两个词:“孤独”和“影子”,/把扬抑抑六步格处理成抑扬抑格,//把你优美的生命汇入我的生命,/然后爱着你的生命。”前半部分可以看做是对死亡的解读,那就是“孤独”和“影子”,后面则是对复活的阐述,只有删掉了这两个词,只有改变了格律,只有把生命汇入其中,就是完成了一次新生。所以,“孤独”和“影子”就是赖特在死亡之中的“两位公民”,而死亡和新生构成了生命的“两位公民”。
什么是孤独?什么是影子?死亡的这“两位公民”在赖特这本诗集中也处在某种被“抽离”的位置上,在唐纳德·霍尔的《序言》之前,是两首诗的引用,一首是安东尼奥·马查多的《孤独的时刻》,诗的标题就切实地指向了“孤独”,但是这种孤独本身就带着影子,“你已没了影子,安睡吧;/愿你的尸骨永得安宁……/尘埃落定,/在你平静真实的梦中安睡吧。”影子在第二首被引用的诗歌里得到更具体的体现,那就是赖特的代表作《想起俄亥俄南部的一句俗语》:“我至今还会梦到自己像蛛网上虚弱的丝线般/摇摆,晶莹透亮,濒临消亡,奄奄一息,/悬在河流之上。”宛如蜘蛛不断的线,生命却已经奄奄一息,在“河流之上”摇摆和空悬中,必然会在河流中投下影子,河是俄亥俄的俄亥俄河,或者是任何一条让赖特想起家乡之河、希望远离的河,总之是投下了影子,而且这影子本身就是孤独的影子。
而在不属于其中任何一部诗集的两首诗,以更为抽离的方式体现着赖特的孤独和影子。一首是1954年10月22日首发于《纽约客》的诗歌《追》,“孤独,心如止水,任那/屋顶石子不停滚下,/死寂空气扬起灰尘。”当在高处迎接天空,把手伸向窝星,结果是:“那么高,我双手空空”,这就是追而不得的孤独,最后是一片死寂;另一首则是最早发表于《诗刊》1962年10月、11月合刊的《夏日午前,坐在小网屋中》,诗人一直在行走,独自上路的他就想变成了一匹马,即使在黑暗来临停下来的时候,枕着青露睡去的他,在梦中跋涉而来,“只为让我的影子/没入一匹马的影子。”孤独是诗人的孤独,影子是马的影子,像一匹马一样的孤独,保持着马孤独的影子——甚至那匹马也叫“戴维”,甚至也吃了一首诗,但是孤独和影子不变,抽离而存在、缺失而拥有、空白而言说,它最终通向的是死亡之中的新生,新生里的死亡。
| 编号:S55·2240205·2062 |
所以,孤独和影子就是通往赖特死亡王国的钥匙,他以将文本抽离的方式强化了这种从一开始就被预言也被体验的感受。孤独和影子构成的死亡,在赖特的一生中几乎就是一种同语反复,死亡是孤独的死亡,影子是死亡的影子,孤独又是影子的孤独,它们合而为一,它们无处不在也无处可逃。但是,赖特对于孤独和影子在死亡意义上的构建,也有着某种区分,孤独更像是一种对于自身的关照,它是生命之旅中的常态,无论是童年的记忆,还是家的故事,无论是旅行,还是回来,孤独总是伴随着诗人,在生命的意义上,这是一种更在肉体意义上的体验。“身体,请忍住液汁,/请远离诱人的树,/草地,这迷人夏日/召唤肉身坠降。(《反田园歌谣》)”在赖特的笔下,有父亲之死,“我在俄亥俄启程。/我还梦着家乡。//老头一身破旧蓝衣,一瘸一拐来到床前,/牵着一匹温顺的/瞎马。”有舅舅之死,“威利在这个世界没留下什么,/只有一把开裂的圆头锤子,一套西装,/包括裤子,被他儿子继承了,/花了点儿钱从赫斯洛普殡仪馆拿走了;/我母亲/气哭了,她害怕冬天,/她想到她的兄弟:/威利和约翰,他们的生活和艺术,如果有的话,/我一无所知。(《威利·莱昂斯》);有老师之死,“严寒中,我无法对雪哀哭,/雪在星空草地间盖着你。”这首名为《俄亥俄的冬日》就是纪念逝于1957年暮春的大学老师菲利普·廷伯莱克;有诗人之死,“如今我献上我的小蜡烛,/致敬这位大师。(《为W.H.奥登点一根蜡烛》)”
当然,对于赖特来说,最多的死亡来自于诗人自己,或者是“活着,却被当成死人埋了”的《惊惶》,或者是“梦里死的不是你,只有我”的唯一,或者是“出来吧,出来吧,我要死了”的呼喊——《藏在空酒瓶中的信,我在夜深入静时把它扔进枫林边的河沟》一首诗的题目其实就是一种被言说的死亡,对于赖特来说,“死神的阴影把我笼罩”真的是一种肉体上的痛苦折磨,像他的老师罗特克一样,赖特患有双相情感障碍,后期无法摆脱酒精的诱惑,因为酗酒他被送进过精神病院,为了治疗抑郁症接受了点击疗法,和第一任妻子利伯蒂分居之后,他看不见孩子,复合、分开让赖特的痛苦在一次加深,在1959年的时候他写信给朋友说他层想在西雅图附近溺水自尽。病痛、分居、精神折磨,一直让赖特活在死亡之中,而这样的幽暗人生就像被笼罩了影子的生活,在《宝藏》中,他写道:“我在风中站起身,/骨头变成墨绿宝石。”在《明尼苏达一面湖边》中,他说:“在那一块云朵的底岸,/我伫立着,等待/黑暗。”在《开始》中他把自己放进黑暗中:“麦子向后靠着自己的黑暗,/我靠着我的。”充满中国元素的诗作《冬末跨过水坑,想到中国古代一位地方官》,赖特引用了白居易819年的《《初入峡有感》“况吾时与命,蹇舛不足恃。”被贬的白居易后来在夷陵和元稹相遇,但是赖特在孤独中却只能看见自己的影子,“而今是1960年,眼看又是春天,/明尼阿波利斯巍峨的岩石/垒出我自己幽暗的黄昏,/这里也有竹缆和水。”
对于赖特来说,孤独和影子成为自我人生的一种写照,它在幽暗的世界里直接抵达了更容易到达的死亡,肉身之死,带来精神之死,而在个体的体验和感悟之外,那种孤独和影子带来的死亡更是赖特对俄亥俄为代表的“美国”的一种批判和思考。《绿墙》是赖特的第一辑诗歌,死亡气息弥漫期间,这里既有《墓地三访》中“皮包骨的老妇人/两棵树间/擦着石碑”的凄凉,也有《炉火旁的哀歌》中冻僵的鸟在死亡之前不远弯腰的偏执,但是赖特对死亡的关照更多是对现实的审视,《致失败的救人者》《死囚牢房里的乔治·多蒂之诗》《致逃犯》,赖特写了这些关于“罪人”的诗,从他们被惩罚的死亡中希望找到复活的可能,引用《约翰福音》第11章耶稣的话:“拉撒路,出来!”那首《出来》就是希望用一种神的救赎让死者复活,但是,“出来,它说。但这是谁在喊?/我早就已经脱离了人类,/我的肉身,被火吞噬的会堂。”
《圣犹大》更是对这种“被火吞噬”的救赎的一种书写,“圣”和“犹大”组成的正是信仰的悖反,诗集题辞引用的是《约翰福音》9:34的一段话:“他们回答说:你全然生在罪孽中,还要教训我们吗?于是把他赶出去了。”另一段则来自于梭罗的《河上一周:在康科德和梅里马克》,“消息传来:它很好……医生们,去拯救自己吧;我靠上帝活下去。”这里的“它”是it,即“古老的宇宙”,古老的宇宙不会消亡,因为它会自我拯救,这种自我拯救就是“我靠上帝活下去”——一种讽刺,不是对自我拯救的讽刺,而是对“上帝”的质疑,这种质疑也是对威权、规则的质疑,在《羞耻与屈辱》中,赖特以反讽的语气说道:“他们在挑剔中死去,精神/却逢生于绝处。/纯洁者,纯洁者!活不长久。”而在反向意义上,罪恶未必是罪恶,一首《拒绝》就是赖特的宣言:“神啊,我已经死了这么久,/我出生时,葬礼/就已开始,还将永远继续”。
|
| 詹姆斯·赖特:我说的是“一生” |
在赖特对现实的反思里出现了“美国”,出现了犯人,出现了死刑中,《1957,美国的黄昏》是一首“致卡里尔·切斯曼”的诗,1948年,切斯曼因17项罪名被判死刑。他的抗争曾引发全球性的轰动。1957年,美国高院下令复审此案,但最终仍维持原判,1960年,切斯曼在毒气室接受了死刑。对于死于死刑的切斯曼,赖特称之为“地狱英雄”,赖特要为他歌唱,“以纪念/人类不该忘的悲剧”,这不该有的悲剧就是死刑。另一首《在被处死的杀人犯墓前》则和被俄亥俄政府处死的乔治·多蒂有关,“大地是我无法面对的门。/让秩序见鬼吧,我不想死,/哪怕为了贝莱尔的安宁。”赖特在诗中多次引用《圣经》中的典故,就是表达对死刑的不满,而上帝从来不希望恶人死亡,因为恶人可以改过自新,从而得以存活,在“圣犹大”身上体现的正是这种救赎,“我想起我肉身吃过的食粮,?想起噬肉之吻。就算被剥,/我仍要徒劳地搂住那人。”
之后赖特的诗集里,俄亥俄和“美国”都成为了一道死亡的阴影,在《树枝不会断》诗集中,俄亥俄是赖特离开的家乡,是启程的起点,但是在孤独和影子中,梦里的故乡是死亡,而这也是属于“美国”的终点,“我在墓碑间躺下来。/在悬崖底部,/美国走到了尽头。/美国,/重新投入了大海/黑暗的犁沟。(《西行四章》)”俄亥俄有着滚滚的化学污水,俄亥俄的矿工撞开了坟墓的门锁,俄亥俄的寡妇们喃喃自语,俄亥俄脏着“哈定那个傻子”,从俄亥俄中部行驶的公交车向外望,也都是暴雨将至时的乌云密布。诗集《让我们相聚河边》中,赖特写到了“坐下来,变成瞎子,一声不吭扮死人”的《医药费恐慌》,在《我是苏族武士,他在明尼阿波利斯如是说》中写下了“死去的人一定很孤独吧”,在《在百货公司收银台前》是黑人的自述:“我是黑的。我天生/就是黑骨头。”《在内华达州斯泰特莱思赌博》《被芝加哥之冬裹挟的穷人》《打手电筒收网的偷渔人》《听到西弗吉尼亚州惠灵最老妓院被查封的传闻后》……这些诗作的标题就是一场场无可避免的美国式死亡,“老人沃尔特·惠特曼,我们的同胞,/如今已在我们的国家美国/死去。(《明尼阿波利斯之诗》)”在《新诗》中,赖特为“1862年明尼苏达苏族起义领袖小乌鸦”唱起了《百年颂歌》,因为小乌鸦反抗白人,因为反抗是制造死亡的死亡;赖特为十九世纪初纽约水牛死去的消防员写诗,“是谁掘的这些墓?/是谁任由自己的黑手在美丽的/榆树根中枯萎?/是谁把那些石碑抱起来,/埋进了土中?(《红衣人之墓》)”在《众河之诗:黑孩子变奏曲》中,赖特直接写出了美国的怜悯,“古老而孤独的悲悯,并非你我独有,/河流和孩子们的悲悯,弟兄们的悲悯,这片/国土的悲悯,这就是我们的人生。”
死了这么久,而且一直在死亡,赖特用梦着和醒来的两种状态描写孤独和影子的死亡,梦里的死亡是一种梦见,它已经发生,是“死了这么久”的一种无处可逃的结局,而醒来之后的死亡则以更残酷的方式让死亡不停地进行,“我曾在生命的中途/醒来,发现自己/就要死去(《再看一眼阿迪杰河:雨中的维罗纳》)”但是正是因为从梦中醒来,在死亡发生之后就要死去,所以不管是孤独也好,还是影子也罢,赖特给了死亡一种新生的机会,或者说,不断发生的死亡正是为迎接那一首首“新诗”而来,《树枝不会断》《让我们相聚河边》《致开花的梨树》这些诗集的名字本身就闪烁着一些生命暖色,甚至它们本身就是对生命的书写,虽然还有孤独和阴影,虽然还是死亡,但是“我知道死亡遥不可及”,在《恩典》中,是草地上的暮光,是小马驹的眼睛,“我心豁然开朗,/如果跨出身体,我将碎成/一片花海。”是《乳草》中对小动物的爱,“用手一碰,/来自另一个世界的美妙生灵/漫天飞舞。”是《葬礼之后》的再次出发,“我知道,门外的马已备好鞍,/正在吃草,/等我。”或者正如赖特擅长将诗意变成标题一样,新生就是“《因一本烂诗集而沮丧,我走向一片闲置的牧场,邀昆虫与我做伴》”。
实际上,从死亡到复活,赖特是在旅行意大利之后获得了更多感悟,面对那些古迹甚至废墟,他感受到了历史之死,但是废墟真的是一种毁灭?《致开花的梨树》引用了理查德·奥尔丁顿《献给圣吉米尼亚诺的花圈》一文,那些毁掉的画作、撞塌的教堂、粉碎的塔楼和宫廷,真的消失了,他的态度是:“如果它们消失了,就让它们消失吧;无须在此惹大家不开心,无须告诉人们美丽的东西已经永远逝去了。”废墟让一些东西消失了,但也留下了一些东西,就像理查德·奥尔丁顿认为自己死后才会离开欧洲,“没想到是欧洲死了,离我而去……”那么,赖特的俄亥俄和美国是不是也已经比自己更早死去?死去是新生的开始,所以俄亥俄成为了美丽的故乡,“我知道大部分时候/人们怎么称呼它。/但我会用自己的方式歌唱它,/直到今天,我还时不时/叫它美人。(《美丽的俄亥俄》)”而死后也是赖特新的《旅程》之开始,“在此痊愈”便是这部诗集的题辞,蝉“与我体内的音乐非常融洽”,午睡的萤火虫“睁开双眼,发光”,和“黑沙滩上充满喜乐的小野蟹”互动,还有《蝴蝶鱼》《进入海鳝王国》《雨中的羊》《忍耐风暴的雀鸟》……
它们构成了生命美的乐章,在赖特那里就是最美的诗,而所有诗歌,死去的诗歌,新生的诗歌,梦中的诗歌,醒来的诗歌,孤独的诗歌,影子般的诗歌,真正构成的是“一生”,“他们都下定决心过完这一生”,在诗集最后一篇收录的文章《宝贝》中,赖特记述了自己父亲和姐夫保罗之间的“战争”,他们怒目相向,他们争吵不断,但是,“他们无论如何都会活下去,哪怕水深火热。”而这活下去就构成了生命之“一生”,是抽离而存在、缺失而拥有、空白而言说的一生,是不断死去正在死去而活下去的一生,“我说的不是‘美好的一生’。我说的是‘一生’。”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69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