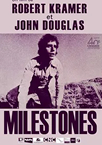2025-04-15《里程碑》:他们在世界之中

这是一部奇怪的电影,这是一部陌生的电影,这是一部发声却让人沉默的电影,这是一部纪实却需要虚构的电影,种种的组合是否也成为观影历史中的一个“里程碑”:当它被树立而成为一个时代的标志,一种事件的符号,甚至一种状态的重要阶段,它所意指的到底是什么?
约翰·道格拉斯和罗伯特·克拉莫以拒绝的方式回答这个问题——甚至是一种刻意的拒绝,没有中心,没有重点,在世界的拼贴中完成150分钟的记录。但是它有起点,有终点,起点是一声开始,重点是最后的落幕,既然将这个影像关闭在开始和结束的封闭世界,形成一种言说的独立状态,那么一定是将“无电影”排斥在外,一定是构建了一种内部,内部就是世界,就是主题,既然营造出一种散点结构,也一定可以寻找到某个可以透视进入的东西。比如约翰·道格拉斯和罗伯特·克拉莫为什么要拍摄这部电影?关于约翰·道格拉斯的信息很少,但是罗伯特·克拉莫则相对较为丰富:出生于纽约的他是“反帝国主义、反资本主义、反种族主义和反好莱坞”的电影导演,可以说他是反美国主流文化的斗士,这个左派导演不仅在对社会进行审视,也在对自我身份进行批判,在商业电影被拒绝之后,在政治立场引起争议之后,1979年他搬到了欧洲,据说,他是被认为仅次于让-吕克·戈达尔的政治现代主义者。在他35年的职业生涯中共参与创作了40多部突破边界的电影,除了这部《里程碑》,1989年的《美国一号公路》也是他的代表作。
《美国一号公路》被称为美国式的挽歌,而比它早14年的《里程碑》克拉莫似乎注入了某种更积极的反叛思想,或者说这部电影其实就是在他去往欧洲之前给美国社会写下的一篇檄文,同时他用影像记录和虚构相结合的方式表达了对新的生活、思考和存在方式的一种态度。同年的《纳什维尔》和这部电影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只不过罗伯特·奥特曼更多是用剧情片的类型对美国社会进行散点透视,《里程碑》使用的是散点,但透视却被隐藏了,约翰·道格拉斯和罗伯特·克拉莫似乎用一种去中心化的方式让电影成为一种纯粹的记录:六个故事线索连接的是五十多个人物和角色,彼此有穿插,有关联,但又在自己的故事里独立存在,就像他们和社会的关系,既是一种排斥和拒绝共存的边缘状态,又是在不断试探、不断接近中介入——甚至是融入,而这个社会也呈现出某种既开放又关闭的矛盾状态,不管是社会整体还是个体,不正是上世纪70年代的美国乃至世界格局的一种写照?
| 导演: 约翰·道格拉斯 / 罗伯特·克拉莫 |
当然电影提供了对时代的背景解读,那就是越战,越战当然已经结束,但是后越战时代对人们思想上、精神上以及世界观、人生观上的影响正逐步显露,剧中直接和越战有关的是一个叫海伦的女人,她喜欢拍摄电影和照片,那些影像就是她在越南拍摄的,但是很明显,她的素材不是战争本身,不是越战的显明影像,而是越南乡村景象,那些人在锯木,在生活。海伦的影像呈现的是一个自然、淳朴以及和平的越南,或者这也是她所说“痴迷电影”的原因,但是约翰·道格拉斯和罗伯特·克拉莫将海伦作为一个越战的参照点,是不是在反其道而行之?在海伦影像之后,电影画面中出现的则是胡志明的照片,这是一种越战被重新归位的提醒,似乎这才是被美国人所认识的越南,这就是一个和战争有关的政治越南,而最后插入的黑白影像是一名叫朗布尔的中尉,在越南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自己作为一名美国空军飞行员被俘,但是受到了越南人民的友好对待,“这增加了我对越南的情感……”
海伦的越南电影和最后朗布尔对越南态度的影像,构成了另一个越南,和照片中的战争越南是不是形成了一种对立?但是对立或者也是互补,甚至是对话:越南所呈现的多样化存在,正是对越战窄化的一种消解,在这个意义上讲,后越战时代的生活是不是也必须去除那种左和右在观念上的樊笼?所以约翰·道格拉斯和罗伯特·克拉莫在拍摄这部电影时,对立而对话是明显的,电影就是在松散的世界里制造紧张,在不确定的生活中寻找支点,在拼贴的叙事中构建同一的状态——或者是形式上的一种实验,所传达的也正是如何在世界的纷乱中寻找自己可能的轨道,在时代转型中如何书写自己可以纳入的当下?或者说,看起来处在边缘的他们如何成为世界之中的存在?
“不论高远,既不是帝王也并非国王的宝座,你只是路边的一粒微尘。”这一句被打出来的字幕就像是约翰·道格拉斯和罗伯特·克拉莫的影像宣言,微尘的存在,在世界的洪流中随波主流,但也必定是自己。可能就是当下,选择就是现实,表达就是自由,这里有刚从监狱里出来还不知道何去何从的人,曾经住过的地方一片散乱,也许记忆也支离破碎了,在朋友的陶瓷工坊制作陶瓷,朋友从11岁开始就失明,但是制作陶瓷让他有一种看见的感觉,“我在监狱里的时候也有这样的感觉,呼吸着从外面世界进来的空气。”简曾经也因为运输危险物品的罪名入狱两年半,她现在在打字机上写关于狱中生活的文字,那次在电视台里做访谈节目,问及为什么会被入狱,简的回答是:“反抗压迫是我们所有人的政治力量。”这里有在加油站寻找工作的年轻人,也有生活在原始社区赤身裸体的人,他们拒绝现代文明,他们在最原始的状态中感受乐趣;这里有和孩子在海边的雪地里玩耍、烤火的父亲,也有和孩子关系紧张分离的人,“我才是他的父亲”,吉米这样对女人说;这里有怀孕后通过针灸希望流产的女人,也有正怀着孕对生活充满了期待的人,凯伦是海伦的女儿,曾经他们母女关系紧张,凯伦甚至一直希望拜托母亲的束缚,但是因为怀孕,她和母亲建立了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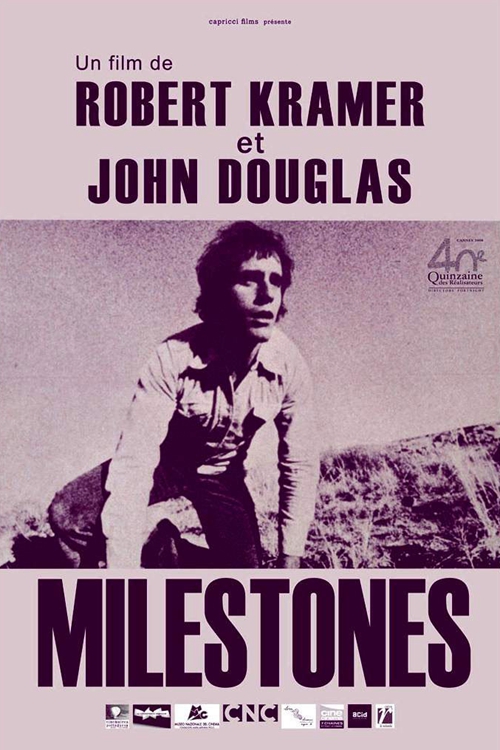
《里程碑》电影海报
他,他,她,她,这是他们的世界,独立而结合的世界,联结而分开的世界,矛盾无处不在,对立到处呈现:避孕与生产、族群与个体、自然与文明、游离与融入、战争与和平、父亲与孩子、母亲与女儿、自由和规则……在这些不同关系体系里,他们的生活触及到了印第安纳瓦霍人,说到了在古巴哈瓦那和卡斯特罗的往事,谈论着黑豹党、奴隶船、印第安保护区,表达着“革命存在于我们每个人之中”的观点。而在影像呈现上,约翰·道格拉斯和罗伯特·克拉莫在纪实中插入了虚构,尤其是警察追捕最后欠债的特里被打死的镜头,让这部纪录片变成了剧情片,而在被导演的世界里,“里程碑”是不是也必然成为每个人人为设置的一个目标,对自然化现实的某种积极改变?
“我出生于1891年12月……”电影就是通过撑着雨伞行走的老妇人的旁白揭开了序幕,生于19世纪末的老妇人,经历了父亲去世、高中辍学、工厂上班、三个孩子流产的人生之后,在70年代的影像里还在积极工作,甚至还是工厂的主要负责人,每天要核查账单。而到了电影最后,老妇人再次现身,她讲述了自己母亲生命最后一刻的场景,“经历各种各样的疼痛,还有一切渗透到身体里的东西,坚持住!”而下一个镜头,便是凯伦最后的生产,在约翰·道格拉斯和罗伯特·克拉莫镜头的实拍中,经历了生产阵痛的凯伦终于听到了孩子的哭泣声,在场的每个人都欢呼:从出生于19世纪末的老妇人认真工作开场,到结尾是以讲述母亲去世作为回应,经历就是人生宝贵的经验,从回忆中母亲去世而喊出“坚持住”,到孩子从母体中降生,构成的人生回环不是从生到死,而是从老死到新生:它是新的起点,新的时代,新的自由。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30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