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04-19《最后的言者》:从死亡的语言内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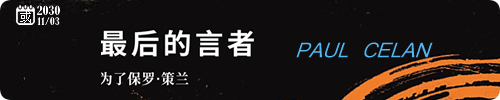
保罗失踪期间吉赛尔对我说:——保罗一直把手表戴在手腕上。他说过:哪天我摘下手表,我就下定决心去死了。
——埃德蒙·雅贝斯《回忆保罗·策兰》
54周年,从54年前的夜晚到54年后的夜晚,如此整齐地划出生与死、读者和作者的距离:2024年4月19日晚,终于将“为了保罗·策兰”的这本书合上,也是整整齐齐,没有被溢出的任何边缘,它只属于一个叫保罗·策兰的诗人;而在1970年4月19日晚——或者20日晚,保罗·策兰摘下了他手上的手表,将它放在一件家具显眼的位置上,然后从埃米尔·左拉大道6号的3楼住处走出,然后在十几米远的米拉波桥上,纵深跳入了塞纳河,并不平静的塞纳河在保罗·策兰跳入后溅起了一个身体的水花,然后又慢慢合拢,恢复了它在夜晚一以贯之的状态——也是整整齐齐,似乎没有惊扰到任何人。直到几天后被发现,一个身体在沉入后被捞起,一个诗人成了一具尸体,保罗·策兰死了。
死亡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但是对于保罗·策兰来说,取下手表的时候,似乎已经注定了他向死的决心,因为他最后的举动就是取消了时间,“哪天我摘下手表,我就下定决心去死了。”埃德蒙·雅贝斯在保罗·策兰死后回忆起了他曾说过的这句话,而在保罗·策兰失踪后他的妻子吉赛尔就打电话告诉了雅贝斯这个重要信息。这块手表,是他从13岁开始戴在手上的,这是保罗·策兰的父母送给他的成人礼,是他在此后的37年里一直让时间活着的标记——保罗·策兰的父母在二战时死于奥斯维辛集中营,这块手表更是成为了死亡的一种证明,甚至,保罗·策兰一直戴着手表的方式也在记录着人生的缺失。马塞尔·科昂在《保罗·策兰的手表》中说,这块手表的时针其实已经坏了,表盘也受损了,但是直到战争结束,保罗才对它进行了修补,这说明,“手表的零部件,无论如何过于昂贵,处于匮缺状态。”即使修补了,这块手表依然成为了一块旧的手表,但是它一直戴在保罗·策兰的手上,直到做出生命结束的选择时,它被静静地躺在了家具上。手表对于保罗·策兰来说,是不是具有特殊的指向意义?陈旧的旋钮,破碎的表盘,开裂的表镜,以及不匹配的时针,“种种令人目眩的迹象,是为了让这个如此清醒且留心日期的人,在所有地方和所有环境下,仅凭一瞥,就能掌握当前的时辰和过去的灾难吗?它们因此指示着他眼中永远确切的唯一时辰吗?”
过去的灾难和当前的时辰都保留在保罗·策兰的时间里,而当他摘下手表,纵深跃入塞纳河,这一时间就搁置在了保罗·策兰的肉身之外,让·戴夫把这种时间的搁置称为“不见了”,在保罗·策兰逝世29年的时候,让·戴夫在《保罗·策兰不见了》一文中回忆了他和保罗·策兰交往的点点滴滴:当保罗·策兰从伦敦回来的时候,他告诉戴夫,“我旅店房间里的一束光。”就像他看见了上帝在门下面;五月风暴的时候,保罗·策兰走在乌尔姆街上,他对戴夫说:“昨晚我隐约听到了炮击一样的声音。”他再次说到上帝,引用的是卡夫卡,“有时是,有时不。”当吉赛尔打电话告诉戴夫,说保罗的遗体被发现了,戴夫想象夜晚的塞纳河和米拉波桥,想象着戴在手腕上的手表被摘掉,“他不见了。”但是这种不见似乎又是一个见的开始,保罗·策兰似乎用他的死完成了另一种成人礼,“正因天空不再向人敞开,人才跳入水中,刨开土地。这里也有构成一次蒸发的不同方法。”他想到了和保罗·策兰有关的人,争吵着的妻子吉赛尔也“不见了”,英格褒·巴赫曼三年后被发现死于床上,他想到了这些“疲倦”的人, “保罗在四面围墙之间追逐天空。”
让·戴夫把保罗·策兰的“不见”看做是传达了一个跨越门槛的想法,而埃德蒙·雅贝斯则在回忆和保罗·策兰最后一次见面之后,想到了他的沉默,“我听到的,不是他的声音,而是沉默。我看到的,不是他,而是空无,或许是因为,那一天,我们彼此,不知不觉地,围着我们自己,残酷地绕圈。”上帝的光在门下面,保罗·策兰的声音是沉默,它们都被某种东西搁置了,如同死亡本身,阿尔贝·霍桑德尔·弗里德兰德则把保罗·策兰在法国巴黎的22年看做是“为了求死”的活着,“巴黎没有一处是策兰的家。没有任何地方可以作为家。”在跃入塞纳河之前,他就谈起过离开,离开巴黎去往瑞士或者其他地方,但一定是除德国之外的任何地方。没有家成为保罗·策兰的一种命运写照,作为一个犹太人,作为一个诗人,“他的命运是犹太式的”,这种对身份的强化就是回到没有家的终点,所以,弗里德兰德认为保罗·策兰的死就是一种斗争,就是一种抗争,“他的童年被遮蔽了,他的大部分学识也被遮蔽了。”所以,保罗·策兰应该被哀悼,所以,保罗·策兰更应当被阅读。
如何阅读保罗·策兰?在这本书里,每个人都在阅读保罗·策兰,阅读保罗·策兰的诗,阅读保罗·策兰身为犹太人的身份,“摆渡阅读的创痛”,题辞引用的就是保罗·策兰的这句话——我们如何阅读?如何摆脱创痛?如何在“不见”中重新看见遮蔽的童年和学识?不见而看见,是一种回溯,是一种揭开,当保罗·策兰跳入水中刨开土地,恰好可以从巴黎的死回到最初的生:生于犹太人家庭,生于切尔诺维茨——回到让·戴夫的思绪,他在“保罗·策兰参观荷尔德林塔楼三十年后的那天”发表的演讲《切尔诺维茨的子午线》,其中说到了保罗·策兰的出生地切尔诺维茨,这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地理意义上,语言意义上,以及民族意义上,所以切尔诺维茨成为了保罗·策兰写作生命中的一条子午线,“正是在切尔诺维茨,保罗·策兰放置了《子午线》,他将在那里永久地试演整个生命,并将不休不止地专注于此。”这条子午线对于保罗·策兰到底意味这什么?首先是一种失去,“它将会缺失,必定缺失,已然缺失,不是因为过错或疏忽,而是因为对其中一个来说,阳光太足,或是因为对另一个来说,语言过度。”然后是被驱逐,“言说将人驱逐出境。写作将人驱逐出境。”最后是行走的方向,“一个肯定的方向,一个返回的方向,一个迂回的方向,一个相遇的方向:诗。”
从语言的缺失,到家园的被逐,再到诗的相遇,一个圆便是保罗·策兰对子午线的“拓扑学探索”:像子午线一样命令,像子午线一样展开,像子午线一样呈弧形,像子午线一样的流动音调,想子午线一样的波浪,“诗是对沿子午线返回出生地的揭示。”所以让·戴夫在保罗·策兰的“切尔诺维茨的子午线”中看见了流放之后的开始,看见了缺席后的存在,看见了没有他者的他异性,看见了乌托邦的两大强力——或者也是症状的来源,那就是德国性和犹太性,正如那句“太阳的文明始于边境”,“与乌托邦一起,它们决定了每首诗的音调;与乌托邦一起,它们编织了每首诗”。同样埃莱娜·西苏对流亡诗人进行考察后认为,“所有诗人都是犹太人”,在她看来,犹太人的标记就是仪式中被赋予其身体的那个切口,这就是“割礼”的仪式,“这个切口辨别、分离并设置了象征性的排斥。被驱逐出城的诗人体验到的正是这个切口。”它是辨别的符号,是分离象征,是被驱逐的铭刻,“在犹太人看来,这个圆环把世界分割成结盟与非结盟的两半。”而对于保罗·策兰来说,“子午线”是一个奇异的圆外,它描摹了宇宙两端的离析。
| 编号:S38·2231204·2033 |
从一种生开始,无论是地理的、民族的,还是语言的,保罗·策兰毫无选择地标记着那个切口,当遮蔽的切尔诺维茨被揭开,是不是意味着他最终通向的是没有家的终点?而在这个作为犹太诗人的漫长抗争中,保罗·策兰又如何构建着他的“子午线”?犹太人这一身份对于保罗·策兰来说,必然牵出一个关键词:奥斯维辛,它是战争,它是屠杀,它是死亡,它是受难——1942年他的父母死于集中营,整个战争期间600万犹太人死去。当阿多诺说“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残忍的”,为什么保罗·策兰成为一个犹太诗人?为什么他还要用德语写作?将自己真名“安切尔”Ancel转变字母顺序后得来的笔名Celan,这是保罗·策兰对自己的命名,他构建了关于诗人的自我,而德语也成为了他“述说奥斯维辛碎片的词”。
恩佐·特拉维索在《保罗·策兰与毁灭的诗学》中认为,保罗·策兰不是德国人,也从不把自己视为德国人,他的德国性是“由一些严格的语言界限划定的”,这就是他对于所谓“不可传达性”或“不可言说性”各类命题的反对,因为成为一名德语诗人就意味着成为流亡诗人,而这是保罗·策兰的另一种自我命名,特拉维索称其为“从死亡的语言内部”寻找词——因为在奥斯维辛之后,德语对于保罗·策兰来说,就是一种流亡的语言,“流亡从此离不开哀悼,因为它不再指示一个因同化而遭离弃或遗忘的世界,而是指示一个遭到灭绝、摧毁的世界,一个消失、化作灰烬的世界。”保罗·策兰“从死亡的语言内部”作诗,与其说是在寻找语言,不如说是一种“反语言”:一种缺席的证言,“穿过纳粹的阴影后,语言仍是唯一没有在废墟中遗失的价值。”同样,意大利的安德烈·赞佐托在《为了保罗·策兰》一文中认为,保罗·策兰代表了看似不可能之举的视线:他不只是在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更是在那些灰烬之中通过平息“绝对的灭绝”,同时又以某种方式驻留于其中,“成功地抵达另一种诗学”。他称保罗·策兰的那种表达系统为“暗哑”,不同于沉默,它是一种实现的形式,“坠入缄默并伴随这同样的话语发觉自己不得不为种种发现而陷入一种至高的迷醉,这就是策兰身上流露出的悖论。”
伊曼努尔·列维纳斯则认为,诗对于保罗·策兰来说,“一下子跨到了它认为可以赶上、可以释放,也许还未被占用的那个他者前面”,这个他者是被释放的、未被占用的他者,只有在跨到他者面前,“我们已经远远在外”,已经“处在乌托邦的光芒中”“诗歌在我们之前,燃烧着我们落脚的地方。”用策兰的话说,诗人“从其生存的倾斜角度言说,从造物得以陈述的倾斜角度言说……写它(诗)的人,献身于它。”在他者面前,自我开始去实体化,自我变成了一个“示意”,也正是在这种乌托邦的光芒中,人才得以展示:一种作为本真性的无国籍状态——甚至是荷尔德林“人诗意地栖居于大地”的变种,绝对的诗言说一切维度的缺陷,它沿着“不可能者的不可能的道路”,走向了乌托邦。莫里斯·布朗肖则在《最后的言者》中试图回答“要从何处寻找无人为之作证的证人?”在他看来,我们需要寻找一个“为我们之内、我们之外”的某个东西,它是匮乏中的抵达,是丧失中的占据,保罗·策兰自己就是“最后的言者”:通过物的形式的书写而被阅读,通过剥夺自身的目睹来目睹,“当我们这样对万物说话时, 我们总在追问它们的途中了,欲知它们从何处来,往何处去,一个始终开放的、无止无尽的追问,指示着敞开,空无,自由——我们远远地在外之处。诗歌追寻的也正是这个位置。”
无论是恩佐·特拉维索所说“从死亡的语言内部”寻找词,还是安德烈·赞佐托的“暗哑”,无论是伊曼努尔·列维纳斯的“他者”,还是布朗肖的“言者”,都关涉到保罗·策兰的诗和语言,雅克·德里达和艾芙琳娜·格罗斯芒的对话则直接以“语言”为题:《语言,永不为人所有》。格罗斯芒通过德里达在《示播列》中对保罗·策兰的作品分析,问及了“在习语中栖居”的“签名”方式:德语是其唯一的财产?还是一种语言在语言自身之中的移居?德里达认为,策兰不是德国人,德语也不是他童年唯一的语言,他只是用德语写作,这是一层对语言的使用问题,但是对于策兰来说,更重要的是,“而是为了与之肉搏”。策兰的每一首都是一种崭新的习语,在这个意义上,他传递着德语的遗产,但是,作为一名并非出于国籍或母语而成为德国人的诗人,他用一种“反签名”的方式让语言不成为被占有之物,甚至让它脱离民族主义的诱惑,脱离民族和国家、国家权力连接的纽带。所以,策兰对语言的继承不是被动接受某个已然在此的东西,而是意味着变形、改动和移置,“他必须尽可能地接近语言的残余、语言的遗骸。”它所召唤的正是新的阐释,新的复活和新的空气。
“创造一件作品就是赋予语言一具新的身体,就是给语言以身体,使得语言的真理能够如是地从中出现,从中出现并消失,在省略的回撤中出现。我想,策兰,从这点看,是诗人的典范。”德里达如是说,他给出了策兰在德语写作中具有的“语言经验”。而这样的经验在菲利普·拉库-拉巴特《论保罗·策兰的两首诗》中则变成了对具体文本的分析:一首是《图宾根,一月》,另一首则是《托特瑙堡》——图宾根关涉的是荷尔德林,而托特瑙堡则和海德格尔有关,都和德语有关,和诗歌有关,也和“我们这个时代”有关。拉巴特认为,《图宾根,一月》是一首写给孤独和痛苦的诗,它从人们认为可能的对话中被抛出,但陷于退却,陷于“蜷缩”——当海德格尔谈论荷尔德林时用的就是这个词,“再也不能言说,只能结结巴巴,被私人用语吞没,或者沉默。”这种沉默是“没什么要说”?还是言说一种从诗中挣脱出来的东西?拉巴特所谈的两首诗,其实指向的是一首诗,一首和海德格尔有关的诗,一首关于“诗人何为”的诗,甚至就是一首对于海德格尔所言“思的任务”的诗。这首《托特瑙堡》首先是文本意义的,它被书写,却又在不可言说中建立“语言经验”,这就是一首诗的“无所欲言”,诗欲有所言,纯粹的欲有所言,却什么也不说,它所欲言的,是无,是虚无。
《托特瑙堡》更是一首现实意义的诗,1967年的夏天,保罗·策兰和海德格尔在托特瑙堡的小屋里见面,在会面还没有发生的1961年,保罗·策兰就在《话语栅栏》中写下了“献给马丁·海德格尔”的题词,“荨麻路上传来的声音:/来到我们手上。/谁独自与灯一起,/
只有手,用以阅读。”在题辞中,策兰怀着“由衷敬意”,对海德格尔“致以我的心与我诚挚的问候,致以我真诚的衷心”;而海德格尔在托特瑙堡会面之后也写下了献给保罗·策兰的题词:“献给保罗·策兰,纪念对木屋的访问”。保罗·策兰在会面6年前就下下了献辞,对于海德格尔似乎充满了期待,一个是被德国纳粹迫害过的犹太诗人,一个是和纳粹撇不开关系的哲学家,两人的会面颇受关注,也备受争议,在恩佐·特拉维索看来,这次会面也成为保罗·策兰毁灭诗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它让人惊讶甚至错愕,只能从策兰对于信仰或仪式的尊重来解释他对海德格尔的敬意,而策兰就曾说起自己和语言的关系是一种“海德格尔通道”,它结合了动词“去往”和名词“异教徒”,而这正是一种流亡的语言,所以策兰主动接近海德格尔是在表明,“上帝也许没有离弃祂的子民,而是随子民一起在特雷布林卡、奥斯维辛和马伊达内克被消灭了。”
“它就像一道意外的光线,撕破了笼罩在策兰诗歌上的厚重阴霾。”无疑特拉维索也是惊讶和错愕的,但是拉巴特却认为会面本身关涉的就是海德格尔所言“思的任务”,思要开启历史,打开世界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也就是诗的“无所欲言”,“策兰的诗整体上就是一场与海德格尔之思的对话。”一个是诗人,一个是哲学家,一个是诗,一个是思,甚至拉巴特认为那首《托特瑙堡》也是一首被辜负的诗,一首失望的诗,也正因为被辜负、失望,所以“无所欲言”的《托特瑙堡》所说的东西是:“一种宣布了奥斯维辛的语言,让奥斯维辛在其中得以宣布的语言。”或者说,策兰就是“在死亡的语言内部”写诗。但是,当死亡的语言内部变成语言的内部死亡,保罗·策兰是不是彻底走向了“无所欲言”的空无?对于犹太人、德国、奥斯维辛以及德语,都是在保罗·策兰出生这个维度谈论的,他的诗歌写作也是一次出生,深深刻印这这些标记,但是在策兰来到巴黎,一住22年,在法语的世界里用德语写作,是不是真的让他成为了他者?是不是将他带向了死的维度?
弗里德兰德把保罗·策兰在巴黎的生活看做是“为了求死”的活着,巴黎真的没有一处是策兰的家?真的没有任何地方可以作为家?伊夫·博纳富瓦在《保罗·策兰之所惧》中说,策兰移居法国并没有使他获得他人的认可,“在一个不懂他诗歌所用语言的社会里,他走到悲剧终点的这段生活,确实值得我们作出迄今还没人作出的反思。”博纳富瓦的反思回到了诗歌之外的世俗世界,回到了人赖以存在的肉身,在他看来,保罗·策兰作为诗人,有着诗人的烦恼,“在如今的社会里,诗歌,如此的诗歌,穿越了多少世纪的诗歌,只能被寥寥无几的人所感知、所体验。”而同时,他的身上已经集聚了战争时期的不幸和残酷的回忆,这些让他不安,作为犹太斗士,他的全部存在都是由欲望所支撑,“他期待权力,也能够梦想权力,因为他拥有诗歌,这通向自我的道路也可通向其他的人。”克莱尔·戈尔的污蔑,或者是保罗·策兰所受的最大打击,“虽然一切都如此突然、难以预料,但他最严峻的考验,并非在这场滋扰开始的1953年8月,而是在诽谤者可耻地再度提起控诉的1960年。”
实际上,博纳富瓦已经将策兰放在了一个存在者生存的维度,在他看来,正是因为保罗·策兰经历了这些,所以他在某些方面的惊恐情绪和他的暴力构成了一种征兆,“意味着他的烦恼已无法在交流中化作可以诠释或掌握的形式,并对他持续施加着影响——虽然他认为,他所经历的事情关乎众生。”妮娜·卡西安在1965年从罗马尼亚来到巴黎,他和策兰一样是“流亡”者,但是她却见到了“不快乐”的策兰,“一种悲哀的神情不知怎的加厚了他高贵的容貌。”埃米尔·齐奥朗在《邂逅保罗·策兰》中也提到了翻译合作的事,他也认为,“无力超然物外或愤世嫉俗让他的生活变成了一场噩梦。”他开始厌恶巴黎人,无论是不是作家,他以普遍持有的态度对待这个世界,齐奥朗认为,策兰是一个“悲剧的存在”,“这个富有魅力的不可能之人,凶猛又带有一丝温柔的亲近,我爱他,但也躲着他,怕伤到他,因为一切都伤到他。每次遇见他,我都小心翼翼,时刻留心,以至于过了半个小时,我就精疲力尽了。”
一个犹太人,一个诗人,一个必须写作的犹太人,一个必须被阅读的诗人,保罗·策兰已经成为诗学的符号,已经成为诗歌的象征,但是从生到死,从切尔诺维茨到奥斯维辛再到巴黎,那个摘掉手表,从米拉波桥上纵深跳入了塞纳河的保罗·策兰也只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而死亡或者也是一个肉身存在无法避免的结局,正像妮娜·卡西安所说,在死亡之前的同一个夏天,“保罗统治着一个海水与爱情的王国”:他那时离开了一个叫丽娅的女人,迷上了“像黑色丝绒一样”的神秘女人邱奇;后来,丽娅死了,传到了保罗那里,他给朋友写信时说:“丽娅在地中海的水域里溺亡了,这离仍未忘却的一切是那么远——离我的心又是那么近。”在1967年他还写到:“丽娅,溺毙,溺毙……”三年后,保罗·策兰也以溺毙的方式走向了死亡——故事或者只是一种巧合,但这不正是一个比诗歌更为真实、具体的肉身存在?埃米尔·齐奥朗说:“对词语的爱,没错;但不是执迷。第一次激情产生了诗;第二次,诗的戏仿。”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75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