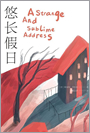2024-08-10《悠长假日》:他在阴影中游荡

明天一大早……就这样,这两朵花躺在一堆鱼骨头、鸡蛋壳、面包碎屑、茶叶渣和残羹冷饭上面过了一夜。
——《新来的女佣》
鱼骨头、鸡蛋壳、面包碎屑、茶叶渣和残羹冷饭,是生活产生的垃圾,它们的命运就是被舍弃,当两朵花躺在这些垃圾上面过了一夜,当第二天垃圾被舍弃,两朵花的命运又如何?阿米特·乔杜里用这句话结尾,似乎并不想回答这个问题,当两朵花的命运留下了悬念,是不是在开放中保留了一种不被生活击碎的希望?
两朵花“躺在”垃圾上过了一夜,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意向,它们仿佛独立着,迎接属于它们的明天,而这也象征了“新来的女佣”米拉和另一个佣人雷蒙的可能生活。米拉是新来的女佣,当她按响了门铃,带来的是一首乐曲,很短暂但悦耳动听,而当里面的雷曼为她开门,仿佛也感染了这一种快乐的情绪。米拉来到新主人这里,干起各种杂活,“仿佛在她眼里,只有灰尘才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她总是对雷曼保持着微笑,而且她的微笑和小嘴非常契合,这也许就是属于她的快乐;实际上,雷曼在那首铃声之外也和米拉在屋子里感受到了快了,两个佣人一起为主人干活,在保持着某种距离又友好的相处中,彼此认识了自己,“你在家乡吃过辣的食物吗?”米拉这样问他。
佣人和主人,无疑是两个阶层的人,当米拉第一次整理衣柜的时候,女主人指着“床罩”说的是英语,这也许是女主人常用的语言,但是在米拉面前被说出,就是拉大了彼此之间的距离,所谓隔阂。而喜欢吃辣的雷曼是一个来自比哈尔村子里的男人,他离开了家乡来到这里,妻子、孩子和七十二岁的老父亲还生活在比哈尔的村庄里,雷曼离开村子当然是为了赚钱,为了生计,这就是他和米拉一样、与主人不同的生活。但是,男主人和女主人之间也存在着隔阂:男人总是相信自己就是小说中的人物,他不习惯真实生活,每天沿着规定的路线反复行走半小时;和有气无力的男主人相比,女主人虽然在晚上会习惯性失眠,但一到天亮心情就豁然开朗,她会出门,回来就变得容光焕发、生机勃勃。
乔杜里没有详述主人之间的隔阂,他甚至只是用几句话带过,但是明显让人感觉到一种不和谐,但是回到佣人的生活里,他们一起为主人干活,始终保持着友好的态度,而且还互相帮助。当雷曼想到明天要和米拉说起两朵花的故事,“这个夜晚到第二天早上的这段时间似乎变得无比漫长,充满希望,给人心灵慰藉,让人觉得前景光明。”似乎乔杜里完成了一次置换:佣人的生活本来就像那些被丢弃的垃圾一样,主人才是躺在上面的两朵花,但是当它变成了希望,躺在狼藉般的命运上面的两朵花却正是米拉和雷曼,在困顿的生活中他们感受到了一种温暖,这种温暖是属于他们的美好,是和明天有关的希望。
《新来的女佣》是短篇集《那些故事》中的一篇,“那些故事”是淡淡的故事,是平凡的故事,是遭遇了困顿之人的故事,“那些”对于乔杜里来说,指向的就是容易被忽略的“他们”。在《三月底的路》中,他写到了加尔各答地铁施工带来的变化,道路被临时挖断,碎石堆积如山,灰尘到处飞扬,通过建设是为了提升生活品质,但是这样的城市却制造了新的问题,在修建现场,道路两旁的商店都关门了,留下的是那些流浪者,他们是身无分文的穷人,是无家可归的家人,是印巴战争的难民,废弃电车轨道旁就是他们的家,“所谓的家,不过是用塑料板搭起来的、里面只有一些烧焦的炊具、勉强能安身的地方。”乔杜里写到的是“临时挖断”的道路,但是这个工程却建设了十年,当十年后完工,道路恢复了通行,商店也重新开业,但是流浪者却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当然包括他们安身的家。
流浪者的到来和离去,都和城市建设有关,所以他们的生活就像《新来的女佣》里的残羹冷炙一般,明天就是他们被舍弃的日子;但是在地铁完工之后,流浪者不见了,并不是生活被改善了,而是因为他们淹没在人群中成了更容易被忽略的存在。乔杜里写到了男人和女人的对话,女人伸出她的手,男人握着她的手,然后盯着手心看,发现了“手心如薄玻璃般泛着难以捉摸的光泽”,而女人似乎也是第一次看见自己的这双手,之后女人问男人:“那你的手相呢?”男人回答说:“哦,很平常,无非是工作、退休、死亡。”平常的手相,意味着平常的生活,工作、退休和死亡的三部曲就是属于他们不曾改变的命运,而这也是这个城市芸芸众生的命运,它和大动干戈既制造了繁荣又带来了灰尘的大工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那里,正常的生活向人们展示着自动循环的秘密,他们加入到人行道上的散步者行列,淹没在人群中。”
| 编号:C42·2240418·2096 |
还有《世界上最快乐的人》中的那个“他”,第三人称单数,就是一种容易被淹没的存在,但是他不在加尔各答,也不再孟买,身为印度人,他却住在伦敦,而且一住就是三十年,“他一无所有,没有家庭,没有房子,也没有车子,但他假装对这些东西不屑一顾。”这个不被命名的“他”在乔杜里的故事里,是一个被“我”观察的对象,我的父亲和他曾经是好朋友,他们在这里读书时认识,现在他和我的舅舅也有来往,舅舅带着我再次认识了他,他会来我的出租屋,“坐在电视机前面,拿着遥控器狂躁地换频道,幸好那台电视机的频道不超过四个。”在这里,我和他之间的关系被赋予了不同的意义:我来自印度,他却不再回印度;我来到伦敦为这里的美景征服,他生活在这里却一无所有;他会和我聊半个小时的天,他会每天举行小小的仪式,不仅将壁炉上的灰尘擦除,还会在神明面前摆放圣食或供品,他把公寓桌子上那盏大象形状的灯称作“甘尼许”,这是印度教中代表成功的鼻头神的名字……
在伦敦住了三十年却一无所有,是在逃避印度?为什么还保持着曾经的仪式?所以“我”成为观察者是为了解答“他”矛盾的生活,而他竟然问我的是“你回到印度后会教英语吗?”这更是一个和他的选择有关的矛盾问题,于是作为观察者的我问他的是:为什么不回印度?他的回答是:“我受不了印度人,一群愚不可及的生物。”因为他的印度亲戚向他借钱一借就是二十年,还有一个巴基斯坦邻居,失业在家也时常向他借钱。所以他认为,自己不是“抵触回去”,而是“不能回去”,因为那里不再是他以前的故乡,不再有他曾经的生活,一切都改变了,一切都不复存在了:
如果大家都能生活在一起,到了晚上住在同一个房间里,就像我们以前在西隆(印度东北部城市)那样,我是愿意回去的。如果每个人都衣食无忧,不富也不穷,起码有足够的钱维持舒适的生活;晚上,大家一起坐在房间里聊天,每个人都在——赛迪、美达、杜库、兰吉、卡库、布迪、摩吉……这样的话,我是愿意回去的。
过去已经变成了虚无,所以不愿意回去,所以“不能回去”,那么对于他来说,是想回到从前才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还是彻底告别回不去的印度才成为“世界上最快乐的人”?无疑乔杜里的回答是第一种,因为记忆之中的美好才是快乐的源泉,不仅是他还包括舅舅,“舅舅第一个愉快的故事是在他七岁时”,那时家里有七兄弟、两姐妹和一个守寡的母亲,十口人住在锡尔赫特县,但是,“他向我讲述如何独自闲逛,如何穿过一条住着一群行为古怪、留着大胡子的穆斯林男人的街道,走到小镇尽头去看山。”记忆是仅存的快乐源泉,它容易被现实湮没,而《那些故事》里的佣人、看手相的男女,其实都在内心里保留着这样一种微小的快乐,这种快乐就是躺着的两朵花,指向明天的希望。
乔杜里在短篇小说中营造了淡淡的忧伤和淡淡的希望,而中篇《加尔各答的假日时光》也有这样的忧伤和希望,但是中篇的故事却写得极为碎片化,这种碎片化带来的琐碎感甚至取消了希望,就像在“悠长假日”站在陌生加尔各答的桑迪普,无法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加尔各答还是那个尘土飞扬的城市,这座“扬灰之城”似乎要将一切都覆盖了一般,所以对于这里的人来说,是回归传统还是走向现代?这就是站在十字路口的矛盾选择,“此时的加尔各答如同一个现代艺术作品,既不合理,又不实用,只是为了某种奇特的审美价值而存在。”一方面墙面剥落、铁门生锈、天花板掉落,就是传统文化不断被解构的现实隐喻,当人们每天打扫和擦拭,不让灰尘污染,就是为了去除这种奇特的存在方式,对于他们来说,这就是“奉献”:“在这里,奉献的含义是:遵循远古的传统,涂上眼影相番红花粉,用上其他古老的化妆品或化妆术,如檀香膏、手绘文身等。”
在月底的时候,这里的人忙着庆祝萨拉斯瓦蒂女神节,他们一丝不苟准备供品,学生在纸上写一百零八遍“女神萨拉斯瓦蒂”,画家为他们的画作默默祈祷,音乐家为自己的音乐祈祷,作家请求女神保佑他们的新书热卖……这是对传统的态度?小舅却说到了印度独立前的历史,他认为国父甘地是一个厌食症患者,而大舅怀念被英国统治之前的生活,“在我们的父亲去世后,我们就搬到西隆。西隆境内有绵延的群山和飞流的瀑布。”对过去的态度并非只是维系那些传统仪式,仪式的背后更是他们朝向未来的寄托,但是对于未来,传统是不是也会逐渐湮没?也会异化?在桑迪普看来,大人们都疯了,因为他们把简单的事情搞复杂了,甚至在他看来,他们的生活不是贫穷而是苦行,“贫穷意味着物资匱乏,流离失所;而苦行意味着在物质稀缺的传统和文化里面,以根深蒂固的方式保持贫穷状态,甚至把物资匮乏的生活当成一种存在方式。”
苦行变成了一种刻意的生活,宗教仪式当然也失去了信仰意义,那么在这样面临“现代化”之路上,是不是舍弃一切传统?连清洁工加内什都有了自己的选择,她会把孩子送到一所说英语的学校,说着话的时候她的眼神里流露出坚定的责任感和油然的热情。但是和加内什完全不同的是舅妈,她从来不重视英语,像其他印度妇女一样,维护着所谓的高贵尊严。而这种所谓的高贵就像苦行的生活、女神节的仪式一样,越来越变成了一种存在于执念中的宿命,那次小舅心脏病发作发出呻吟声,还拼命撕扯了自己的衬衫,他被送到了医院的重症监护室,最后的结果是大难不死,人们都认为这是一种奇迹,但是这种奇迹观就像苦行一样,其实脱离了生活的真实状态,“这个奇迹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想象力丰富的人更容易相信这些并不存在的东西是存在的。他们相信神灵、天使或魔鬼是存在的,而不愿相信一个真实存在的人可能会停止存在。”就像收音机播报的新闻,永远是一个政治清明、政府有为的美好世界。
在这样的虚幻面前,桑迪普当然相信自己是真实的,他的理想是成为作家,他反对愚昧,他用英语写诗歌和小说,他希望自己像鱼儿那样自由,像鸟儿张开翅膀。但是他的这种真实却陷在传统和现代难以融合的夹缝中。从孟买而来到加尔各答,他不适应这里的生活,身为独生子,他没有自己的兄弟可以分享一切,“他在阴影中游荡,忘记这只是暂时的阴影。”他学英语,希望帮助舅妈,但是他也不会用孟加拉语,“在现代印度有无效像他这样的孩子,从小脱离家乡的语言环境,如同语言上的孤儿。”他不信神灵只是喜欢拜神,因为可以闻到檀香,可以听到舅妈的喃喃声,甚至他喜欢这样一个事实:“庄严的祷告结束后,神灵通常并不会显灵。”
桑迪普是一个孤独者、无信仰者,但是这会让他毫无顾忌地走向现代?当然一样是茫然,“悠长假日”就像桑迪普面对的漫长人生一样,充满了太多的不确定性,而乔杜里将这种不确定性变成了字里行间的散漫,始终没有一个让人有所感悟的中心点,甚至这种“悠长假日”拉长到两个假日,当桑迪普一年半之后再次来到这里,一切似乎都没有改变,他依然茫然。乔杜里在这里给了桑迪普一种诗意的发现,那个坐在土豆中间的女孩,因为真实触动了他,“他经常幻想有一天会娶她,所以悄悄用眼角的余光观察这个衣衫褴楼的小女孩生龙活虎、一脸欢快地跑下楼的样子,倾听她召唤弟弟妹妹跟上自己时那略带沙哑又缺乏教养的嗓音。”
他感觉自己爱上了她,甚至在一年后回来,桑迪普看见了女神节上的女神,“女神看起来善良仁慈、娴静自若又宽容大度,她端坐房间一头,像个羞答答的新娘,胆怯得不敢跟家人说话。”这是桑迪普对传统之美的一次回发现?而他分明想起来认识一个女孩,安静、羞涩,这让桑迪普感到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快乐。但其实一切还是虚幻,那只不过是转瞬即逝的感觉,阴影还在,忧伤还在,却连两朵花的希望都被取代了,就像最后那只飞走的噪鹃,“实际上不是飞走了,而是消失在有形的世界里。当他们看它时,发现它有点羞涩,还遮掩着自己的眼睛。”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5002]
顾后:问津·鹊桥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