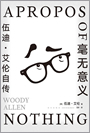2024-09-02《毫无意义》:我的灵魂是多云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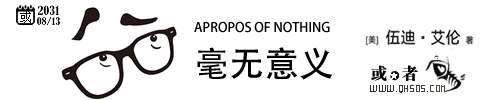
我已经八十四岁了;我的生命几乎已经过半。在我这个年龄,就像在用从赌场赢来的钱继续赌。我不相信有来世,所以我真的看不出人们记得我是一个电影导演、一个恋童癖或根本不记得我之间有什么实际区别。我只要求将我的骨灰撒在药店附近。
那时的伍迪·艾伦84岁,那时的伍迪·艾伦拍摄了《纽约的一个雨天》,当然,那时他的骨灰还没有撒在药店附近——五年过去了,伍迪·艾伦已经89岁了,也许生命还只是过半,而电影人生却还在不断的拉长,在《纽约的一个雨天》之后,他在2020年推出了《里夫金的电影节》,2023年推出了《天降幸运》,还未命名的一部电影已经计划2025年推出。虽然对于年仅9旬的艾伦来说,推出电影的周期被拉长了,但不可否认,他依然是好莱坞拍摄电影最多的导演之一。
但是激情依然的艾伦为什么说自己是在“续赌”?为什么在电影界取得了声誉的他并不把“电影导演”看做是一种莫大的荣誉?为什么把84岁只看成是生命过半的年龄却悲观地不相信来世?在电影导演和恋童癖之间画等号而且只希望骨灰撒在药店附近,艾伦如何会发出这样的声音?一切似乎都来源于他刻在骨子里的那句“毫无意义”,在回顾自己84年走过的路时,艾伦说:“我可以把生命看成悲剧或喜剧,这取决于我的血糖水平,但我一直认为它毫无意义。”不管生命是悲剧还是喜剧,都是一种“毫无意义”的存在,而实际上艾伦并不只是在这里提到了“毫无意义”,在这本不分章节的“自传”中,艾伦几次都提到了这个核心词:在五岁的时候意识到了死亡,艾伦认为作为人类,出生就是为了抗拒死亡,在这样的逻辑中,苟活是生命的样子,但是有时候大脑会让你做一些事,“生命是一场毫无意义的、苦难和眼泪的噩梦,但如果有个人突然进入房间,拿着刀要杀死我们,我们会立刻做出反应。”在十岁时因为一篇作文,一丁点儿知识转换成了好笑的段子让观众觉得自己知道很多,他却悲观地认为,“人类在一个毫无意义的、残暴的宇宙中寻找上帝。”而对于拍电影,对于电影带来的荣誉,艾伦说:“赞扬毫无意义。即使得到很高的赞誉,你还是会得关节炎和带状疱疹。”
因为对闯入者做出反应只是苟活中的一种态度,所以生命毫无意义;因为人们只是从笑话中得到了知识,所以宇宙是毫无意义的存在;因为被赞扬依旧会有疾病和不开心的事,所以名声也毫无意义;因为悲剧或喜剧只取决于自己的血糖水平,所以生命再次毫无意义——“毫无意义”是一种否定,对生命的否定,对知识的否定,对信仰的否定和对人生意义的否定,当艾伦在保持着电影创作的那份激情却一次又一次说到“毫无意义”,在这种否定甚至彻底否定意义的人生中,他是不是就是活在永远的矛盾中?而矛盾对于生命作为不可更高的属性,它的背后是不是一种宿命论?在84岁拍摄《纽约的一个雨天》时,艾伦说他喜欢雨天,喜欢雨天的故事,“当我早上醒来,打开百叶窗,看到下雨或灰蒙蒙的小雨,或至少是阴天时,我就会感觉良好。”但是雨天只是一种他想要的理想状态,而现实对他来说则是另一种天气:“我的灵魂是多云的。”不是灰蒙蒙的雨天,不是万里无云的晴天,现实是内心状态的客观对应物,那种“多云”的天气对于艾伦来说,是“毫无意义”中的意义,或者是意义中的“毫无意义”。
宿命论在艾伦的自传中,强调的第一层含义就是出生的偶然。他从祖父、父亲、母亲等家人说起,就是从出生开始自己的故事,尤其是父亲在他生命中扮演者特殊的角色:出生于布鲁克林,父亲作为一个犹太硬汉,当过桌球老千、赌徒、和道奇队的球童,16岁加入了海军,在法国行刑队里时处决过一名强奸了当地女孩的美国水兵,一战期间,他所在的船在欧洲冰冷的海水中被炮弹击中,船沉了,除了三个人游上了岸其余人都溺死了,于是父亲就成了“那三个能搞定大西洋的人之一”,搞定大西洋的父亲,却走在死亡的边缘,这也意味着“我就那样差一点永远没能出生”。这只是出生的偶然性之一,它带着巨大的巧合,而艾伦讲到关于出生的偶然还有两次,于是,“有三次我险些没能出生。”生命的降生成了一个最大的偶然事件,对于这样充满偶然性的命运,艾伦总是从自我的叙事中退出来,然后站在远处,像观察自己电影中的主人公一样来形容自己的出生:他说到了父母,说到了妹妹,然后说:“然后,我会重新回来并出生,这样故事才能真正开始。”在记叙了一段故事之后,又调转头来说:“所以我说到哪儿了?哦,我出生了。”或者完成了一系列铺垫后说:“但现在,我已经准备好要出生了。终于,我进入了这个世界。”
准备出生,以及出生了,就像是艾伦看到不是自己的邻家小孩降生,带着完全是客观主义的视角。而出生之后呢?艾伦说自己热爱关于魔术的一切,自己喜欢“任何需要独处的事”,因为这样就不必和其他人类打交道,“出于无法解释的理由,我不喜欢也不信任人类。”这是艾伦内心的真实表达,它形成和外界的错位,正是这种错位使他的人生充满了太多的矛盾,而矛盾是“毫无意义”宿命的第二层含义:他成长中翻阅的第一本书是父亲的《纽约的黑帮》,这使他对黑帮、罪犯和犯罪产生了迷恋,所以他把自己称为“热爱黑帮的反人类文盲”,“一个没有教养的孤独的人,他坐在三面镜前,练习一副纸牌,这样就可以藏掉黑桃A,从任何角度都无法被看到,然后骗取一些赌注。”自己不喜欢读书,在学校里逃学而且在父母面前撒谎,“掩人耳目,躲躲闪闪,伪造通知,罪加一等,父母气愤。”这无疑也是对他人所作艾伦人设的一种否定,而这又成为艾伦对自己电影的某种注解:“你看我的电影就能明白;有些很有娱乐性,但我没有一个想法能创立新的宗教。”出生进入到这个世界,在艾伦看来,这是一个“我永远不会感到舒服、永远不会理解、永远不会赞同或原谅的世界”,甚至是和自我形成了一种对立,比如在别人看来自己是一个健康、有运动天赋、团队合作的首选,但实际上是一个紧张、恐惧的情绪废人,甚至冷血、厌世、幽闭恐惧、孤立、怨愤,以及“绝对悲观”……
| 编号:Z21·2240519·2126 |
从宿命到矛盾,艾伦对人生的态度永远是“毫无意义”,所以他选择了改名,1935年12月1日出生时他的名字是艾伦·斯图尔特·康尼斯伯格,他把自己叫做伍迪·艾伦,这是一次“随便改”的经历,在保留了艾伦这个姓之后,考虑过J.C.艾伦、梅尔·艾伦,但最后随机地想到了伍迪·艾伦,“这名字短,和艾伦很搭,而且有一种轻盈而模糊的喜感,不像佐尔坦或路德维西奥之类的。”改名就是对人生命名的一次抗拒,而改名的随意性是不是又变成了另一种偶然?这其实和艾伦对于“毫无意义”的阐述一样,当他在讲笑话、写作以及拍电影中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否定式的“毫无意义”是艾伦故意对自己的贬低,但是,它的潜台词其实是:意义,是从偶然性的毫无意义中发现了必然的意义,是从宿命论的毫无意义中看到了对命运抗拒的意义,是从矛盾的毫无意义中探寻到了消弭冲突的意义。无疑对一切的否定是艾伦的手段,在否定变成肯定、在毫无意义中找到意义,带成为艾伦对于自我生命的注解——反其道而用之的策略似乎正是艾伦在电影中的叙事手段,甚至在毫无意义的彻底否定和意义的重构中,被人为拉大的距离反而装入了比预想更多的东西:他的天才性创作、他对传统的革新、他独特的魅力……
比如谈到自己的成长,他说自己从小喜欢生病,只有这样才能不去学校尽情享受收音机、漫画书和鸡汤;他说自己是天真的笨蛋,不知道自己具有音乐的天分,认为自己只能成为音乐界的无名小卒,而人们也是因为容忍才听自己演奏;在纽约大学里学的是电影专业,选择这个专业知识因为看电影既愉快又舒适,但是这个在老师眼中不知道人生目标的人、不具有良知的人、心理有问题而被建议去看心理医生的人,最后被学校开除,对此艾伦的说法是:“一个很大的好处是有利于自我欺骗。”自我欺骗中找到了自己在做的事,于是开始成为一个喜剧作家,为广播节目写作。对于写作,艾伦也全然采取了否定式的叙述,写作之前是阅读,但是直到一年级才学会阅读,后来是因为在女孩子面前不懂的东西太多,所以开始读福克纳、卡夫卡、艾略特、乔伊斯、海明威、加缪的书,但是还是搞不懂亨利·詹姆斯;而身为一个导演、作家,艾伦说自己从未看过《哈姆雷特》的现场表演,没有看过任何版本的《我们的小镇》,从未读过《尤利西斯》《堂吉诃德》《洛丽塔》《第二十二条军规》《一九八四》,当然也没有读过弗吉尼亚·伍尔夫、福斯特、劳伦斯、勃朗特、狄更斯——却读过约瑟夫·戈培尔的东西……
同样,在电影之路上艾伦也有诸多的未看过:没有看过卓别林的《从军记》或《马戏团》,没有看过基顿的《航海家》,没有看过《一个明星的诞生》的任何版本,也从未看过《青山翠谷》《呼啸山庄》《茶花女》《扬帆》《宾虚》或其他许多电影,还没有看过《迪兹先生进城》和《史密斯先生到华盛顿》……如此多的没看过,却依然不能阻止他成为好莱坞最成功的导演,而即使如此,艾伦也依然把改名后的“伍迪·艾伦时代”称为“一个将臭名昭著的时代”,否定不是为了否定本身,而是在否定中找到肯定,艾伦说:“我不是贬低这些作品;我在说我的无知,以及为什么戴眼镜并不会让人特别有文化,更别说成为知识分子了。”肯定他的无师自通,肯定他对“知识分子”标签的反抗,肯定他在博学漏洞中开辟了属于自己的领地。
自己的领地是从笑话的写作开始的,“嘿,你上了尼克·肯尼的专栏。”朋友的这个电话是艾伦新的起点,他坐飞机去洛杉矶为《高露洁喜剧时间》写夏季剧场的喜剧,回到纽约后写了很多短剧,二十二岁时被任命为《帕特·布恩电视秀》的首席编剧,后来又成了《加里·摩尔秀》,加入了NBC的编剧发展计划中。之后艾伦又从编剧变成了电影导演,开始执导电影,从在欧洲完成第一部电影剧本《风流绅士》开始,艾伦的电影人生正式开启。对于自己执导的电影,艾伦也有肯定和否定、赞扬和贬低的评价,他认为《性爱宝典》是第一部商业上取得巨大成功的电影,《爱与死》是具有俄罗斯文学氛围的直白喜剧,是早期搞笑电影中最搞笑的,最糟糕和最垃圾的胶片电影是《皇家赌场》,《星辰往事》是一部有点被误解的电影,《西力传》为纪录片风格的喜剧积累的经验,《仲夏夜性喜剧》是非常美丽和魔幻的作品,《子弹横飞百老汇》是最好的电影之一,最令人失望的电影是《好莱坞式结局》,当然,《安妮·霍尔》因为获得了四项奥斯卡奖,在艾伦执导的电影中一定是最引人注目的,“我的反应就像读到了肯尼迪遇刺的新闻。”但是就像他认为赞誉毫无意义一样,在得到了这个消息之后,“我思索了一分钟,然后吃完我那碗麦圈,走到打字机前,开始工作。”
而对于世界著名导演,艾伦也开出了长长的单子,叙述和他们的关系:喜欢卓别林胜过基顿,他也比哈罗德·劳埃德有趣;喜欢希区柯克,唯一一次见到希区柯克是在后台闲聊,之后希区柯克走上舞台,和包括林登·约翰逊一家在内的众人说:“我警告过你们,《群鸟》要来了。”狂迷刘别谦,但从来不觉得《倪涛我也逃》好笑;与伯格曼共进过晚餐,还有几次长时间的电话交谈,“我觉得他是我一生中遇到的最好的导演,而他和我有一样的恐惧。”在休·门格斯家里曾和特吕弗一起学过语言课,艾伦学的是法语特吕弗学的是英语;曾与戈达尔短暂合作,与雷乃会面并共进晚餐,和安东尼奥尼相处了很长时间,见到过雅克·塔蒂,但是从未见过费里尼,只是打过一次“美好而漫长的电话”……当艾伦84岁的时候,他说特吕弗、雷乃、安东尼奥尼、德西卡、卡赞都走了,戈达尔还活着,对于这些逝去的记忆,艾伦不免忧伤,“整个影坛已经改变,所有我年轻时想打动的人,都已经消逝在深渊中,而深渊似乎就在不远处等着我。”依然弥漫着悲观主义的情绪,依然表现出多云的灵魂。
对生命偶然性的感触,都充满矛盾人生的怀疑,以及悲观厌世的情绪,这些组成了艾伦“毫无意义”的叙事,但是对于他来说,最具争议也让他感觉到毫无意义的或许是感情的经历。艾伦的第一任妻子是哈林,那时他刚加入NBC编剧发展计划时,哈林还在亨特大学念哲学,两个人在社交俱乐部认识,于是约会于是结婚,对于这一段婚姻,艾伦就像他形容自己的出生一样,“还有什么可做呢?所以我们订了婚。”但是结婚之后两个人的观念出现了矛盾,开始渐行渐远,“她对我的情绪、我的阴郁、我让人讨厌的个性变得不耐烦,这是可以理解的。”艾伦强调两个人的矛盾,但是其中却是另一个女人的介入:露易丝·拉塞尔,起初三个人在一起聊天,后来艾伦被这个“名字中的L要用舌头发音”的女孩所吸引,“直到我在半夜醒来,有一种强烈的欲望,想要娶她并住在月球上。”和哈琳分手之后,艾伦开始了和露易丝的恋情,“我清楚地记得,我是在哪里第一次意识到什么是爱,爱究竟是什么感觉,我也终于明白了那些诗人、抒情诗人在表达什么。”
艾伦对每段恋情的开始都有了肯定的语气,但是随着交往和生活,他便把对女人和爱情的肯定变成了否定。在和露易丝结婚前的八年时间里,这个在艾伦眼中曾经让他知道了爱的感觉的女人,却变成了“不忠、节食、进出医院、抽大麻、嗑药”的女人,虽然对自己的事业有过帮助,虽然自己感觉过有趣,但是露易丝最终变成了艾伦眼中狂躁、不诚实、极度贬低自己的女人,终于这个一直是艾伦“十四行诗里的金发女郎”终于和他分道扬镳,甚至在刚刚结婚的时候,艾伦还评价说:“但从本质上讲,这是她与其他男人乱搞的黄金机会。”之后走进艾伦生活中的女人是黛安·基顿,“她如此迷人,如此可爱,如此漂亮,如此闪耀,以至于我坐在那里想,为什么我明天晚上要去和那另一个女人约会?”但是好景不长,艾伦发现了她的暴食症,发现了她厌倦曼哈顿,于是和基顿的妹妹罗宾、多莉约会,“我们纵乐一时。”
在获得了奥斯卡奖之后,另一个女人进入了艾伦的生活,它就是米亚·法罗,这个和艾伦交往十三年的女人就像电影中的“戏剧性”一样,它曾经是艾伦所追求的东西,但是当它发生,艾伦才知道“我失败了”。“她非常出色,我喜欢她,但这是一件漫不经心的事;我们没有相爱,没有对彼此承诺。”这是艾伦保持理性的一个评价,和这个“有七个孩子的女人”建立恋爱关系艾伦认为是一件“好笑”的事,因为他说自己应该看到“示警红旗”:米亚和第三任丈夫安德烈·普列文生有三个儿子,在这段婚姻期间收养了两名越南裔婴儿和一名韩裔孩童——她就是之后成为艾伦妻子的宋宜,与安德烈离婚之后她又收养了有脑瘫的韩裔孤儿摩西·法罗,和伍迪·艾伦恋爱期间收养了迪伦·法罗,之后和伍迪·艾伦生下了罗南·法罗,之后米亚又收养了无名孩子。对于艾伦犯的错,他自己将其看成是自己的无知,“回想起来,示警红旗每隔几英尺就有一面,但大自然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否认机制,否则日子就不能过下去了,正如弗洛伊德教给我们的,正如尼采教给我们的,正如奥尼尔教给我们的,正如T.S.艾略特教给我们的。不幸的是,我从来不是一个好学生。”
米亚也曾说起过结婚,但是艾伦认为婚姻之事不必要的仪式,两个人在13年的时间里从未结婚,按照艾伦的说法,甚至从来没有住在一起。虽然13年里“我没有在她的纽约公寓里睡过一次”,但是两个人最后却走上了法庭,在对薄公堂中,艾伦都是被告,关于抚养权,关于恋童癖等等,但是在艾伦看来,自己无疑是受害者,“我并不害怕真相,也不打算购买沉默。我根本不在乎名誉。我已经准备好上法庭,完全诚实地宣布我一生中从未侵犯过任何人,我也准备好公开捍卫这一声明。让耶鲁去调查吧。让纽约州去调查吧。我欢迎专业人土仔细调查。”他认为米亚布下了“毒狼”,利用自己的怀孕向他讨价还价;他说米亚是黑寡妇,“她杀死并吃掉了我。”他指责米亚对收养的孩子没有尽到抚养的责任,“两个被她收养的孩子最终自杀身亡,这并不出人意料。还有个孩子也计划过自杀,另有一个可爱的女儿,三十多岁时与HIV阳性作抗争,却被米亚抛弃在医院,在一个圣诞节早晨独自死于艾滋病。”而对于外界认为双方都是疯子、精神错乱的说法,艾伦认为“他说——她说——”式各执一词并不是真相,而是“她说”之后的“他说”,是“他说”背后的真相。
也许正因为艾伦和米亚之间的爱恨情仇,最后走进艾伦生活的是宋宜:因为宋宜是唯一挑战米亚权威的人,她认为米亚收养孩子并不是为了抚养他们,而是喜欢圣人的名声,陶醉与充满赞美的报道;更因为艾伦在失意甚至被公众误解的时候,宋宜站出来帮助他给予他精神的陪伴——在拍摄《丈夫、太太与情人》时,两个人真正走到了一起,也是在舆论对艾伦形成重压的时候,他们于1997年躲开了公众的目光在“一间隐蔽的房间”举行了婚礼,对于这段婚姻,艾伦的评价是:“我生平第一次享受到真正的婚姻,真正的爱情关系。”而这本距离他们结婚已经过去20年的自传,也是艾伦献给这段“真正的婚姻”的礼物,“献给最亲爱的,宋宜”,而题辞的下半句则是:“我把她置于股掌之上,随后发现我的胳膊没了”……
依然幽默,依然多情,“胳膊没了”是否定,“置于股掌之上”则是肯定,在这肯定式的否定和否定式的肯定中,经历了这一切的艾伦是不是找到了“毫无意义”背后的意义?只不过灵魂多云的艾伦似乎总是想要证明什么,对于几段婚姻,对于女性的态度,它们发生了就是发生了,就是人们会议论的事件,就是一定会被看见的真相,但是艾伦却以画蛇添足的方式自证了清白,而这是不是就是真正的“毫无意义”:
我的媒体代表莱斯利·达特曾向我指出,在五十年的电影制作中,我与数百名女演员合作,提供了一百零六个女主角的角色,获得了六十二个女演员奖项提名,从未与其中任何一位有过不正当行为。或与任何一位临时演员。或与任何一位替身。此外,自从独立于电影公司以来,我已经雇用了两百三十名女性作为摄影背后的主要工作人员,更不用说女性剪辑师、女性制片人,而且每一位在我的电影里总是与男性同工同酬。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7197]